Ⅰ、同气连枝
不管在幻想还是现实世界,到处都有老鼠。
我们熟悉的许多科幻故事都为我们勾勒出了鼠类一步一步向着智能生物演化的奇观:陈楸帆的《鼠年》中,拥有智能的新鼠与没能就业的大学生灭鼠队周旋战斗,它们不仅拥有集体观念,甚至还能够通过操控幻觉来诱使人类自相残杀;在迟卉的“拉比特人系列”里,鼠类成了人类灭绝后新崛起的智慧种族,鼠族姑娘也为“催婚”而苦恼;至于贵志祐介原作、丁丁虫翻译的日本科幻名作《来自新世界》,更是大胆描写了由人类与裸滨鼠基因融合产生的种族——“化鼠”,战争策略既有不亚于人类的机智又非常系统化。类似的还有意大利恐怖电影《人肉鼠餐》,更是描绘了智鼠崛起后的重口味世界……而到了奇幻与童话的世界里,鼠类的形象就更丰富了,从“战锤”系列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斯卡文鼠人”,到可爱的米老鼠、杰瑞以及舒克贝塔,人类对鼠从爱到恨的各种情感全都能找到对应的拟人投射。
而在现实的地球上,作为最成功的哺乳动物类群之一,啮齿目凭借着超强的繁殖力与适应性,将血脉扩散到了几乎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之中,并在环境选择压力下演化出了形态迥异的种群,彼此之间一眼看上去甚至都不像是一家人了。
如此一来,“鼠”家的门槛到底在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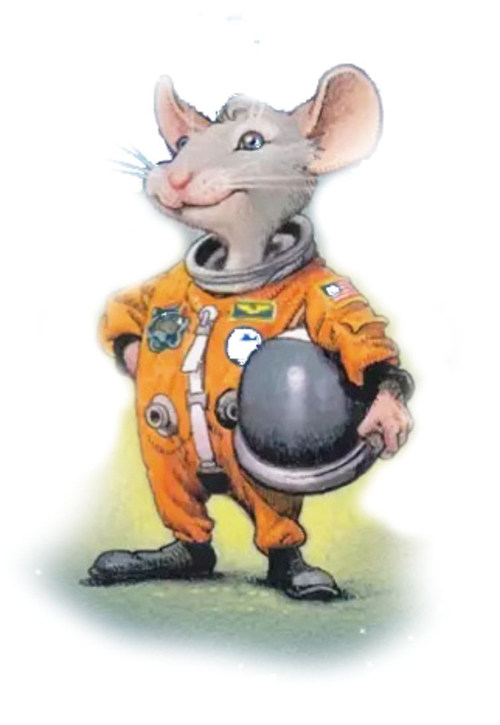
啮齿动物最重要的鉴别特征,就是嘴上把门儿的“大板牙”。这四颗没有牙根的大型凿状门齿会终生持续生长,必须不断地通过啮咬硬物来打磨,稍有懈怠就会疯长。人类为它们定下的“啮齿”之名,就是在描述“耗子啃桌角”这一最典型的啮齿动物行为。而这样一副甚至有点“威力过剩”的好牙口,也让啮齿动物在占领大地的适应辐射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顺利解决掉了不少“难啃”的问题。
虽然有了如此给力的门齿,但啮齿目的“虎牙”——也就是犬齿却在演化中缺位了。不过,这种缺位并非啮齿动物独有,我们熟悉的马(奇蹄目)以及牛、羊(均为偶蹄目),就分别出现了类似的“趋同演化”,同样在门齿和臼齿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档。但更有趣的是,和牛羊同属偶蹄目的猪形亚目“二师兄”们,却又以发达犬齿形成的“獠牙”而著称。
说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嘴里同样有“大板牙”把门儿的兔形目,为什么和啮齿目分成两家了呢?
难道仅仅是萌萌的“小兔几”嫌弃“耗子”了吗?
作为与啮齿目最为接近——或者说得学术一点儿,“有着最近共同祖先”的群体,兔子们确实也有着从形态到功能皆与啮齿动物非常类似的门齿。但是,啮齿动物的门齿数量在演化过程中被削减到只剩两上两下的最后四颗,而兔子们则有两对上门齿——在显眼的大板牙之后,还有一对几乎没有功能的小门牙。虽然这个差异看似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恰恰是这类“有没有都一样”的痕迹器官,往往更容易在风向说变就变的自然选择压力下保持原本的形态,最终反而成了演化分类研究中的关键特征。
生命演化分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不要盲目把“看起来差不多”的物种堆到一起。因为外在的特征与形态,往往最容易被环境所左右,产生“趋同演化”:相似的环境、相似的选择压力,会将源自不同家族的物种,最终塑造成外貌非常类似的模样。
因此,诸如“负鼠”“袋鼠”“鼹鼠”等等名字里有“鼠”字的群体,以及鼩鼱和树鼩这样看似小老鼠或小松鼠的家伙,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鼠”。它们与“耗子”们在形态特征、行为习性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能让彼此攀上更近的亲缘关系。
不过,既然啮齿目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假亲戚”,也就同样有可能存在着失散多年的“亲兄弟”。随着研究者在古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域的深入推进,人们惊讶地发现,啮齿动物确实还有一大批之前没想到的亲戚。
那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灵长目动物。
是的,老鼠真的是我们的“精灵鼠小弟”。

目前的研究表明,啮齿目、兔形目、灵长目以及规模比较小的树鼩目、皮翼目共同构成了古老而庞大的“灵长总目”。这个家族最早的演化证据,甚至可以追溯到恐龙依旧统治大地的白垩纪。
也就是说,从踏上月球的人类,到满地乱窜的各种耗子再到撑着翼膜滑翔在林间的鼯猴,所有这些看似天差地别的物种,都曾经有同一个共同祖先,各自基因库里的内容也高度重叠。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层亲缘关系,让人类与“鼠辈”之间的故事,变得更加辛酸。
Ⅱ、相煎何急
老鼠,既是人类的兄弟,也是人类的影子。
与繁殖策略上选择“少生精养(K对策)”的人类不同,啮齿动物几乎全都践行著“多生糙养”的“R对策”,因此面对自然环境突变更容易迅速“迭代升级”。正是凭借着无孔不入的超强适应性,褐家鼠(大鼠)、小家鼠(小鼠)以及黑家鼠等几种“鼠辈”,成功适应了发展速度相对自然演化来说日新月异的人类文明,从此搭上了人类崛起的顺风车,成了极少数日子反而因为人类活动而越来越好的动物。作为鼠的重要演化中心之一,目前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褐家鼠就源自我国西南地区,其化石证据在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中就已经屡见不鲜。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交流,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物随着人类的迁徙与贸易,在全世界扩散开来。3000年前,褐家鼠已经出现在中亚,之后在公元元年前后到达非洲,并进一步顺着罗马帝国的交通网,从北非窜入了地中海对岸的欧洲。
当然,这些如影随形的小东西给人类带来的麻烦可远不止“无票乘车”这么简单。
首先,它们也要吃饭。
虽然老鼠是“什么都吃”的杂食主义者,体型硕大的褐家鼠甚至会捕食自己的“小兄弟”——小家鼠来打牙祭(因此这两种耗子的分布区域一般来说不会太重叠),但人类种植并储存的农作物显然是最为唾手可得的“免费自助餐”。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等华夏大地的炎黄子孙当然早就吃足了这些啮齿动物的苦头,甚至把它们和威风凛凛的“老虎”“老鹰”等顶级捕食者一起划入“老”字辈行列。先秦时代的古人,更是借着描述贪食谷物的“硕鼠”,来讽刺压迫百姓的封建贵族。
也正因为鼠患猖獗,对于收成就是一切的农耕时代人类来说,那些能够帮助自己大量消灭、震慑各路鼠辈的小型食肉目猛兽,就成为需要奉若上宾的救星了。
最早驯养家猫的埃及人,对“喵星人”的崇拜就达到了让现代“铲屎官”们都自叹弗如的地步,不但创造了猫首人身的女神“贝斯特”顶礼膜拜,还把死去的猫制成木乃伊加以厚葬。无独有偶,在“黑猫警长”们扩散到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前,欧洲人就和萌萌的蒙眼貂达成了战略合作;而在亚洲最东方的日本,同样善于捕鼠的狐狸更是“位列仙班”,成了神道教大力膜拜的“稻荷神”之一;甚至从汉代起就一直主张“君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善于捕鼠的狐狸和黄鼠狼也都被劳苦大众私下当作“胡黄二仙”加以敬畏。
這些如今看来有点儿可笑的崇拜,恰恰反映着先人对鼠患的苦恼。
此外,啮齿动物的门牙,也让它们绝不可能在偷点儿粮食后就收手。老鼠们磨牙、打洞的习性,经过日积月累,足以对人类建造的各种土木工程产生致命的威胁。甚至在现代都市中,被它们啃断的网线与电缆,也一样会让我们回忆起先祖苦于鼠患的烦恼。
但所有这些破坏加在一起,都不及传染病来得可怕。

作为同属灵长总目的亲戚,人和鼠有着大量共患疾病,这其中不乏斑疹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以及鼠疫这样杀人无数的死神。
作为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之一,鼠疫至今依然和霍乱共同平分了《传染病防治法》中甲类传染病的“光荣榜”,把人们谈之色变的“非典”、艾滋病、禽流感等乙类传染病统统踩在脚下。在14世纪的欧洲,席卷而来的“黑死病(一般认为是鼠疫)”创造了5000万人级别的毁灭性屠杀,在短时间内沉重地打击了欧洲中世纪后期的高速恢复进程。当时身披黑色长袍、头戴鸟嘴面具的“瘟疫医生”还未掌握现代医学知识,面对这些远在其认知能力之外的病原微生物,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更不用说去阻止疫情的蔓延了。而作为瘟疫的化身,身披黑袍、手持大镰无情收割生命的“死神(reaper,本意收割者)”形象,也成了欧洲人遭此劫难后深深镌刻于群体记忆深处的文化印记。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作为更早就与鼠疫打交道的“过来人”,华夏文明也没少被它折腾。不管哪朝哪代,只要瘟疫一来,上至王室贵胄、下至黎民百姓,无一幸免。直到“大清要完”的1910年,都在清朝曾经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爆发过一次规模不小的鼠疫。幸好这次疫情暴发时,中国已经有了第一批属于自己的现代医学家。后来主力创办协和医院的伍连德先生,顶着俄、日等多方列强和国内各方势力的压力与质疑,亲自带领团队奔赴东北,以严谨求实的现代流行病学知识为指导,在4个月内迅速平息了这次原本可能进一步爆发恶化的灾难,堪称真正的“国士无双”。
时至今日,在高速崛起的现代医学面前,鼠疫已被逼到了文明社会的边缘,一般情况下只有牧区牧民偶尔被零星感染。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某些号称“返璞归真”的流行文化影响,在草原、高原景区近距离接触旱獭(土拨鼠)的无知游客成了黑色死神重返现代社会的“代理人”。至于现代空前便捷的交通,更是可以让疫病携带者在短短半天之内就穿州过省、甚至远赴地球另一端,极大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

幸好,现代医学对这些曾经屠杀人类的疾病都有着效果不错的控制手段。因此,尽管全世界的现代大都会各个都有不输地面人类社会的地下鼠王国,但如今啮齿目动物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却降低到了文明诞生以来的最低点。甚至于原本用于捕鼠的家猫和蒙眼貂,也都“解甲归田”,成了在居室内打滚嬉戏的软萌毛球。
但人与鼠持续近万年的“战争”,却也谈不上孰是孰非。这些让我们气恼甚至憎恨的鼠类,也不过是在顺应自己的生存本能、努力地活过下一天而已。
就如同它们的人类兄弟一样。
Ⅲ、共赴前程
不管怎么说,鼠终归是我们的兄弟。
这种相似性,可以让很多在鼠身上做出的实验结果,直接或间接地推广到人类身上。不过,人们一开始选择大鼠和小鼠作为实验动物的原因,则更加简单直接:
因为它们能生。
拜其祖先选择的“R对策”所赐,啮齿动物普遍具有高效的繁殖能力。以实验室常用的小家鼠(小鼠)为例,母鼠受孕后只需要三周就可以产下一窝粉嫩的鼠宝宝,平均下来大概一次能生7只;而鼠宝宝诞生后三周就可以断奶、开始满地乱窜;到了它们两个月大的时候,这些新生一代就可以让自己的母亲当奶奶或者外婆了。
因此,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大鼠和小鼠的繁殖能力会让其种群规模以爆炸一般的速度指数级扩大。这样可怕的繁殖潜力,对于巴不得将耗子斩尽杀绝的古人(以及依然饱受鼠患困扰的部分现代人)来说确实是一大麻烦;但在实验动物学家眼里,这样的高速繁殖,却让人类可以对它们的种群进行快速、大范围的近交筛选,从而培育出各种有着稳定遗传性状的品系,用于对应的科学研究。

因此,不同于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小白鼠”,現实中的生物学和医学实验,所用到的小鼠外观随品系不同而有着各自不同的变化。
我国常用的“昆明鼠”,就是一种患有白化病的典型“小白鼠”。不过,这个品系内部的基因差异还不够小,杂合率比较高、个体差异也相对比较大,只是一个“远交系”。因此,这些“小白鼠”只能用于教学操作训练以及一些对实验动物不那么“讲究”的实验。
而到了对实验动物个体差异管控更加严格的研究中,研究者最常用的小鼠就换成了黑褐色的C57BL/6系小鼠。这个源自至少几十代同胞兄妹“近亲繁殖”的“近交系”,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已经极其微小,绝大部分基因都高度纯合,甚至于任意两只C57BL/6小鼠之间,都可以随意移植器官而不用担心出现免疫排斥反应。
这样一支近乎“克隆人军团”的近交系,为各种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将个体差异压到极低水平的实验动物平台。现在大量的前沿尖端研究,都会优先拿C57BL/6系小鼠“开刀”。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品系的小鼠遗传背景“纯净”、品系稳定且易于饲养繁殖,因此非常适于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一步构建各种转基因小鼠品系。这些乍看之下平平无奇的转基因“小黑鼠”,对于很多生物学或医学研究来说,可是必不可少的无价之宝。
除此之外,经过人类多年的大规模育种筛选,其他品种的近交系小鼠也在科学研究中大展身手。比如BALB/c系小白鼠的一个分支——俗称为“裸鼠”的BALB/c-Nude就因为缺少胸腺而有先天性T细胞免疫缺陷,因而一生都必须生存于严格无菌的人造封闭环境中,却也因此在肿瘤与免疫研究领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此外,作为最早被驯化的实验动物,各种品系的大鼠也是世界各地实验室里的铁杆常客。而属于豪猪亚目豚鼠科的呆萌豚鼠,也是被各种医学和药物试验大量消耗的重要“被试者”。至于来自非洲、长相极为“任性”的裸鼢鼠,也因其惊人的身体特质与社会行为而成了科学研究的“新星”。
在遥远的过去,人与鼠从共同的远祖相互揖别。在文明时代,鼠曾经给人类造成了刻骨铭心的惨痛破坏;如今,鼠却又以自己难以计数的牺牲,替人类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科学贡献。

在可能的未来,驶向无尽寰宇的太空飞船依然会如大航海时代的卡拉克帆船一样有着鼠类的身影;只不过这一次,鼠类将不再是藏身货舱与甲板下的偷渡客,而是在实验室中与人类一起并肩共赴星海的伙伴。
鼠与人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责任编辑:艾 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