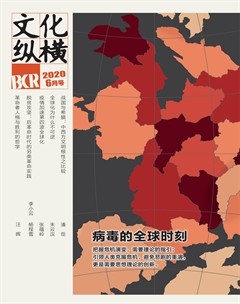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震动着中国与世界。全球思想界在此危急时刻也共同聚焦着疫情之下的困境与挑战。对于西方知识界来说,此次疫情暴露出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而面对率先走出疫情的中国,欧美从最开始的同情逐渐转向关注中西治理模式背后潜藏的“文明冲突”,并对此愈发警觉。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了对下一阶段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思考。
美国国家能力的危机
疫情在美国的全面暴发激起了学者对美国国家能力的质疑与责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史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撰文直指“美国国家能力之死”。无可否认,特朗普治下反建制派与传统技术官僚的对立在激烈的政党斗争背景下不断恶化,两党之间、联邦与各州之间在应对疫情中的冲突与推诿,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宪法原则下的总统制、选举制和联邦制。
在过去,几乎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拥有最具能力的官员、运转最好的企业、最先进的金融公司和最贤达的领导人。然而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威廉姆·戴维斯在《我们为什么不再信任精英》一文中指出,过去十年西方精英阶层已日益陷入信任危机之中,更多的民众将政治看作是一场骗局,不再相信专业政客,转而信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
现实政治中,反建制派不遗余力地攻击着“不接地气”的职业官僚對民众利益的背叛,精英们则不断指责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专业精神、独立文职部门等传统准则的破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达隆·阿西莫格鲁在《新冠疫情暴露美国的威权转向》中指出,我们的宪法无力约束总统,特朗普不仅将党派的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知识之上,还削减国家的关键卫生基础设施,更迫使许多有能力和经验的文职官员辞职,以至于疾控中心这样的联邦卫生机构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得含糊而低效,整个联邦官僚系统像一只“纸利维坦”(Paper Leviathan),毫无决策能力。在阿西莫格鲁看来,这样的现状不得不令人反思当下的总统制和民主制。当宪法和文职官员都无法有效地制约“超级总统”,当所有政客和媒体都疲于应对无休止的选举政治,美国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用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疫情到来之际,本就适逢选举年而愈发激烈的政党斗争裹挟在反建制派与职业官僚的矛盾之中日益恶化。《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罗纳德·布朗斯撰文指出,两党在国内议题上长期持有不同主张,病毒的传播更加剧了双方在基本问题上的哲学分歧,其中最为关键的争议在于“社会中最健康的人到底亏欠最脆弱的人多少?”这一问题也正是特朗普在2017年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CA)时所面对的核心争论。时任总统奥巴马以及民主党议员偏向于把医疗和财务风险更为平均地分摊在健康需求较高者和较低者之间,而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则谴责该法案会导致年轻人和健康人为降低老年人和病人风险牺牲得太多。
在疫情暴发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之下,两党类似的分歧再次产生。特朗普、部分共和党议员以及保守派经济学家声称,管控措施使得太多人遭受经济痛苦,这类措施所拯救的人数甚至无法为措施本身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的发言是这一观点的最极端版本。他认为,如果能使得经济和社会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开放,老年美国人就应当接受可能死于病毒的更大风险。而民主党官员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无论是否会给多数人带来压力,广泛的社会群体都有责任拯救尽量多的弱势群体。
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传统与病毒传播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区域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两党的冲突和对立,而这种分裂也使得整个国家对统一的疫情防控政策施政乏力。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和波士顿等地是目前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城市,而各州的城市选民恰恰构成了民主党的选票基础。与此相反,小城镇和乡村社区受到疫情的影响明显更小,这些地方的选票又是共和党的坚实支柱。在最大的几个偏共和党州,这一冲突展现得尤其明显。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几个偏民主党城市(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圣路易斯)的当地官员开始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这些市长抱怨他们的努力正因共和党州长拒绝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控制措施而受损,而这些共和党州长又主要受到乡村地区的广泛支持。乔治城大学医疗保险改革中心研究教授萨布丽娜·柯莱特认为:“我对我们是否会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限制活动)持悲观态度……或许在一些地方仍会采取限制措施,但保持全国范围的限制是几乎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不是履行社会契约的模范生。”
除此之外,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思考,但基本上都聚焦于左翼思想中老生常谈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总体上乏善可陈。不论是大卫·哈维、迈克·戴维斯还是朱迪斯·巴特勒,均对这场公共健康危机进一步凸显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撕裂表达出深切的同情。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制度僵局的同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词也频繁地出现在几位学者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斯拉沃热·齐泽克表示,一旦身陷危机,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连特朗普也不例外。巴特勒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则更加明确。作为伯尼·桑德斯和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支持者,巴特勒认为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主张在美国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而“我们必须等待这一想象在这个国家成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承诺”。
中西危机治理模式的差异与文明冲突的反思
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表现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西不同治理模式、文化差异乃至文明冲突层面的观察与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习惯于在威权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下理解中国与世界。在既有理论中,威权政体被认为是一种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政府权威、极大限制个人自由、公权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状态。例如在《金融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北京是如何包装抗疫故事的》中,英国记者吉迪恩·拉赫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全世界地缘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更多国家或对中国的领导寄予更大的期望,更加认同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在《新冠疫情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一文中也指出,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抑或是公共卫生政策观点而得以保全的国家,将会对其余那些经历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宣告胜利。“对一些国家来说,这将清楚地展现果断的威权主义统治的好处。”
这种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下“威权主义”的判断,正如马丁·雅克所述,本就是一种过度简化,其背后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长期偏见与有意归责。在马吕斯·迈因霍夫看来,将病毒置于“自由主义/威权主义”或“现代的/落后的”的框架之下,其实是西方人思维中挥之不去的东方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时间观。在疫情之下,这种判断更带有了文明冲突的含义。
葡萄牙政治学者布鲁诺·马孔斯在《新冠病毒与文明冲突》一文指出,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疫情为新一轮的文明冲突充当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过去几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慢慢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国坚定地致力于另一种模式,而且实际上正试图将这种模式输出至世界各地。马孔斯指出,在所有关于西方价值观的讨论中,意大利借鉴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大部分措施。这让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底蕴:都试图将社会稳定置于一切之上。而美国似乎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特朗普正在进行一场豪赌,他假设美国人在应对高风险时是与众不同的。他的计划是控制疫情,而不是阻止疫情。在马孔斯看来,当代文明的冲突,就像过去的类似冲突一样,从来都不是一场知识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思想的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术并对自然力量更高层次的掌控的人。同样,冲突发生的背景也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稳定的。从最初的新技术发展,到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侵蚀现存权力体系,再到如今出现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一系列的发展变化都标志着这场冲突将在诸多领域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各国不同的疫情治理现状,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明確拒绝了或者说回避了唯体制论的二分法,而是回到了“国家能力”的议题上。福山认为,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事实上,在疫情治理的行动中,评价政府绩效的关键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疫情之下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在欧美对中国充满警惕的目光中,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化的一场“大考”。传统观点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且蓬勃的国际市场,世界各地的制造商们组建起了灵活的供应链,劳动分工也因全球化优势尽显,但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复杂且相互依赖的系统。在全球经济编织形成的生产网络中,一旦其中一环出现断裂,各国将被迫承担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与经济风险。总体而言,疫情在短期内导致不可避免的逆全球化已成为各界共识,但全球化是就此终结,还是在发生权力转移或内部变革后继续发展下去,成为学者争论的主要焦点。
无可否认,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和“英国脱欧”本就使得全球化达到了它的最大界限,疫情的“大流行”更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大国对抗和战略脱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撰文指出,疫情之下的公民会更期待本国政府能够保护自己,世界各国在采取紧急措施以管控危机的同时,也会在战略上倾向于寻求降低自身风险和对他国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在疫情中看到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
在关于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持更为悲观的态度。在《正如我们所知的经济全球化终点》一文中,尼布莱特直指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作者看来,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激起了美国两党与其斗争的决心,意图强行推动中国与美国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脱钩,并试图迫使盟国仿效。而当前的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而是只会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学教授亨利·法雷尔、乔治城大学外事学院教授亚伯拉罕·纽曼指出,新冠病毒引发的教训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失败,但这次危机极可能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转变。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在全球应对疫情的行动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而是把部分角色让给了中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凯硕认为,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经失去信心,不管有没有特朗普,人们都逐渐接受了自由贸易协定是有害的这一观念。相比之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也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竞争力。时任奥巴马政府时期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M.坎贝尔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拉什·多西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而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伊恩·布雷默对此则更为谨慎。在布雷默看来,今天人们面对的挑战的确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解体,但目前尚缺乏新的全球领导力量介入并取而代之。尽管中国并不满足于在一个战后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发展,而是希望重塑世界,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崛起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影响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還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在未来或将以大国竞争为主要特点。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D. 卡普兰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全球化1.0是从冷战结束一直持续到最近,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的团结和互信。而全球化2.0是一个全球大分歧的故事。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两国对抗的危险性不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但随着美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更加亲美的其他地区,新冠病毒的传播也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因此两国不久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南海和东海开展更具侵略性的军事活动。卡普兰认为,人类或将见证一场多维度的大国竞争,这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截然不同。全球化2.0将不断深化,并伴随我们多年。(文/刘天骄 复旦大学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Stephen Walt,“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Foreign Policy,March 23,2020.
Daron Acemoglu,“The Coronavirus Exposed America’s Authoritarian Turn,”Foreign Affairs,March 23,2020.
Ronald Brownstein,“The COVID-19 Crisis Reveals an Old Divide Between the Parties,”The Atlantic,March 26,2020.
Gideon Rachman,“How Beijing Reframed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narrative,”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20.
John Allen,“The History of COVID-19 Will Be Written by the Victors,”Foreign Policy,March 16,2020.
Bruno Maçães,“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Hudson Institute,March 10,2020.
Francis Fukuyama,“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The Atlantic,March 30,2020.
Stephen M. Walt,“A World Less Open,Prosperous,and Free,”Foreign Policy,March 20,2020.
Robin Niblett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Foreign Policy,March 20,2020.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Will the Coronavirus End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Affairs,March 16,2020.
Kishore Mahbubani,“A More China-Centric Globalization,”Foreign Policy,March 20,2020.
Ian Bremmer,“We Are in a Geopolitical Recession,”Time,March 13,2020.
Robert D. Kaplan,“Coronavirus Ushers in the Globalization We Were Afraid Of,” Bloomberg,March 2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