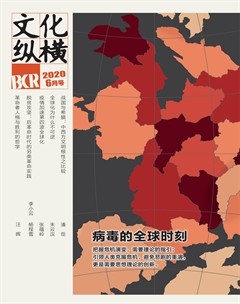突然的无处幸免
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迅速使病毒时刻成为政治时刻、社会时刻、经济时刻和历史时刻,甚至被认为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如T.弗里德曼认为历史可被分为“新冠前”和“新冠后”,[1]见惯兴衰的基辛格也认为病毒“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永远改变世界秩序”[2]。此类预测流露了一种真实心情的预感,即世界要变天。罗伯特·席勒的看法另有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我将疫情视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播”,“叙事也会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如果一个故事主导舆论场好几年,就会像一场流行病一样改变许多东西”。[3]
但病毒时刻还尚未见分晓,仍在不确定性中演化,因为病毒时刻是否真的成为划时代的时刻,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答案一半在病毒手里,另一半在人类手里,而病毒和人类行动都是难以预定的“无理数”。在这里暂且不追问答案,也无能力预知答案,还是先来分析病毒时刻提出的问题。
认为病毒时刻是“史诗级的”巨变或“历史分水岭”,这些文学形容需要明确的参照系才能够明辨。假如以最少争议的划时代事件作为参考尺度,或可进行量级比较。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无过于改变生活、生产或思想能力的发明,比如文字、车轮、农业、工业、逻辑、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力学、疫苗、抗生素、互联网、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或者精神的发明,比如大型宗教、希腊哲学、先秦思想等;或者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或者大规模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经济巨变,如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和美元体系。按照这个粗略的参照系来比较,除非后续出现始料未及的政治或精神巨变,否则新冠病毒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如此巨变的能量,但据经济学家的估计,或许足以造成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
我们还可以换个分析框架或历史标准来看病毒时刻。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标准是一个有说明力的选项。“事件”有着暂时性,相当于历史时间之流的短时段波浪,那么,什么样的波涛能够波及在历史时间中足以形成“大势”的中时段,甚至触及稳定“结构”的长时段深水层?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力超过了短时段的事件,或有可能形成某种中时段的大势。如果真的能够决定数十年的大势,那就很惊悚了。假如新冠病毒大流行只是造成经济大萧条级别的后果,似乎仍然属于事件的范畴,尽管是特大事件,但还不足以形成大势;假如它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那就是大势了。这个大势的可能性虽然风雷隐隐,但尚未形成充分必然的理由,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来自长时段既定“结构”的阻力。文明、社会和思想的深层结构具有抵抗变化的稳定惰性。
从历史经验上看,意外事件冲击过后往往出现反弹,大多数事情会寻根式地恢复其路径依赖而恢复原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种反弹不仅是心理性的,也是理性的,特别是在成本计算上是理性的。长时期形成的“结构”凝聚了大量成本,不仅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技术成本,也是文化、思想和心理成本,这些成本的叠加形成了不值得改变的稳定性。破坏“结构”等于釜底抽薪,是危及存在条件的冒险,所以革命是极高成本的变革。成功的革命总是发生在旧结构已经完全失灵的时候,即旧结构失去精神活力、无法保证社会安全和秩序、无法维持经济水平。可以注意到,1968年以来的世界发生了大量连续的“解构”运动,但主要是拆解了文明的一些表层结构,比如艺术的概念、性别的概念、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之类,尚未动摇经济、政治制度和思维方法论等深层结构。那些最激进的“解构”几乎只存在于文本里,难以化为现实。解构运动的历史力度相当于对结构的“装修”:既然没有能力建造新房子,就只能以多种方式来装修。如果尚无能力在新维度上生成新结构的设想,尚无具备“建构力”的理念、原则和社会能量,“解构”就终究不可能化为革命,解构的行为反倒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吸收进旧的体制,反而成为旧结构的老树新花。
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解,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或精神结构这些属于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难以改变。正因如此,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一旦发生,比如现代性的形成,或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成了二百年来被不断反思的大问题,而百思未解的现代性却已在等待结构的“时代升维”了。不过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能够触发一种新的结构,仍是个未定问题。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果,有一个颇有人气的最严重预测是全球化的终结。如果出现这个结果,就无疑达到了中时段的大勢变局,甚至触及长时段的结构。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就很难拒绝全球市场的诱惑。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只是初级全球化,就经济层面而言,是“分工的全球化”。在分工链条中,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分工的全球化”有可能被终结,但各地仍然需要全球市场来保证经济增长,而技术化和信息化的经济更需要最大程度的扩张,因此,就经济而言,全球化的终结在经济上、技术上和信息上都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理性激励。当然不排除出现政治性的全球化终结,政治自有政治的动力。无论如何,追求自主安全和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确实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有可能出现全球化的转型,由“分工的全球化”转向“竞争的全球化”。如此的话,那就至少形成了中时段的大变局。
“竞争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市场继续存在,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化继续进行,但全球化的游戏性质发生了改变,原先全球化中的“合作博弈”比例大大减少,而“不合作博弈”的比例大大增加,甚至可能会形成“不合作博弈”明显压倒“合作博弈”的局面。其中的危险性在于,竞争的全球化有可能激化而导致全球化的租值消散,从而使全球化本身演化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退出就无利可图,不退出也无利可图。当然,这是一种极端可能性,而更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当不合作博弈导致无利可图的时候,合作博弈就会重新成为诱惑——至少按照艾克斯罗德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看是这样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人类总是陷入困境,但也总能够想出办法脱困。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问题链”会有多远多深,是否会触及并动摇人类思想的深层概念,即哲学层次的概念,这一点将决定新冠病毒是否有着长时段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穿越到未来去提前察看病毒大流行的结果,但目前可以看得见“提醒物”。提醒物未必指示结果,但暗示问题。
在提醒物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长时间欢乐中被遗忘的“无处幸免状态”。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常性并且无处不在的“嘉年华状态”中遗忘了灾难的无处幸免状态。无论是假日旅游、演唱会、体育比赛、产品发布会、首映式、电视节目、公司年会、销售活动、购物中心、艺术展览,都可以做成嘉年华,以至于嘉年华不仅占据了时间,而且变成了空间本身。时间性的存在占有空间的时间足够长,就改变了空间的性质,即使时间性的活动结束了,空间也已经感染了难以消退的嘉年华性质。终于,无论是生活空间(外空间)还是心理空间(内空间)都感染了嘉年华的性质。

新冠病毒以事实说话,其高强度的传染性使得世界无处幸免,压倒了嘉年华的感染力。本来,作为极端可能性的“无处幸免状态”从未在理论中缺席,可是理论却缺席了,欢乐不需要理论,因此理论被遗忘了。“无处幸免状态”并非抽象的可能性,它有着许多具体意象,比如全球核大战、星体撞击地球、不友好的外星文明入侵之类,此类可能性据说概率很低,而且一旦发生就是人类的终结,也就不值得思考了,因此,“无处幸免状态”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结论,或者是问题的终结。“无处幸免状态”在问题清单上消失了,转而在心理上被识别为恐怖传说或科幻故事,与现实有着安全距离,因此可以安全地受虐,大毁灭的故事反倒具有了娱乐性和超现实感。然而,“无处幸免状态”并非没有历史先例,恐龙灭绝虽然是恐龙的灾难,但所蕴含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同样有效;各地历史都流传着灭绝性的大洪水故事;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大流感;冷战期间险些发生的核大战,如此等等,但这些历史都已化为被时间隔开了的老故事而遮蔽了问题。新冠病毒未必有以上历史事例那么致命,却因现代交通和全球化而形成迅雷效果,直接把“无处幸免状态”变成现实,从而暴露了需要面对的相关问题,也把原本不成问题的事情重新变回了问题。这种“问题化”是创造性的,意味着原本可信任的社会系统、制度和观念在意外条件下可以突变为问题。人类的社会系统经得起慢慢的巨变,但经不起突变。严重的不仅是病毒,而是病毒的时刻—全球化的流通能量超过了每个地方承受风险能力的当代时刻。
大规模传染病并非全球化的独特现象,而是古老问题。在全球化之前,病毒通过“慢慢的”传播,最终也能传遍世界,假如不是由于某种运气被终结在某处的话。虽说太阳下无新事,但新冠病毒把老问题推至新的条件下,就转化成了新问题。新冠病毒在当代交往与交通条件下的高速传播形成了类似“闪电战”的效果,使各地的医疗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经济运作和相关物质资源系统猝不及防而陷入困境,使传染病由单纯的疾病问题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叠加的总体问题,直接造成了两个效果:一个问题即所有问题,这是政治最棘手的情况;并且,一个地方即所有地方,这是社会最难应对的情况。这种连锁反应如不可控制地溃堤,就会穿透脆弱的社会系统而叩问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概念,如果因此部分地改变了文明的基本概念,新冠病毒事件就可能具有长时段的意义。
形而下问题暴露了形而上问题
新冠病毒大流行粗鲁而直接提出的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即现代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或按照博弈论的说法,现代系统缺乏“鲁棒性”(robustness)[4]。现代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几乎完成了系统化。环环相扣的系统化意味着高效率,也意味着脆弱性。现代系统不断追求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因此通常缺乏缓冲余量而加重了系统的脆弱性。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的资金、物资、装备、生产、运输、供应系统都环环相扣而全马力运行,不仅在能力上缺乏余量,甚至预支了未来,总是处于能力透支的临界点,事实上很多系统都处于赤字状态,所以难以应对突变事件。塔勒布早就以其“黑天鹅”理论解释了现代系统的脆弱性。现代社会中唯一有着庞大余量的系统恐怕只有军备,比如可以毁灭全球若干次的核武器,而最大程度预支了未来的大概是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因此,“预支未来”就成为当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当代系统的基本意向是厌恶不确定性,可是不确定性却无法避免。就事实状态而言,或就存在论而言,不确定性才是真实事态,而“确定性”其实是一个概念,是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于现代系统是正中要害的精准打击,这个要害就是人,或者说生命。现代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只是隐患,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遇到不确定性甚至严重挑战,往往最终仍然能够脱困,原因在于,系统的关键因素是人,是人在解决问题。人是具有灵活性的生命,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都具有天然的“鲁棒性”,所以,有人的系统就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