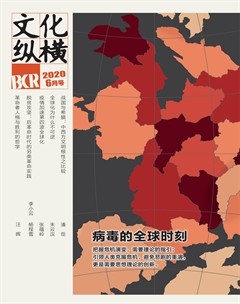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脱贫运动
激进革命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革命成为一种珍藏的记忆。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革命党治理下的国家依然面临未完成的革命使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期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种修辞性的提醒,而是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力图保持其革命性质的具体行动的思想准备。贫困,就是这个行动的先行场域。
自2012年以来,扶贫上升为由党的总书记亲自负责的全党全社会的中心工作,从科层技术治理角度开始的精准扶贫发展到制度治理创新的脱贫攻坚,从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工作扩展到全国上下的“脱贫运动”。显然,扶贫超越了扶贫本身,被赋予了新时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新内涵。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中,贫困被寓意为“敌人”,扶贫被寓意为“战场”,脱贫行动被寓意为“攻坚战”,大批青年干部被派往扶贫的“战场”,生命的极致性付出被弘扬为“战场牺牲的英雄”,扶贫工作会成了向贫困的宣战会,脱贫的总结表扬会成了“战役”胜利的庆祝会……脱贫攻坚的战场充满了“革命”话语。革命化语言和标语也让扶贫这一社会问题产生了神圣感和宏大的仪式感。这一“革命化”现象,说明“扶贫”不是简单的“脱贫群众运动”,也不只是后革命时代社会动员的需要,而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理念的日益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政治回应和象征性暗示。换句话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后革命时代针对如何把握社会利益分配这个全球性难题上向革命本质议程的某种回归,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阶段力图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巩固“初心”和“使命”的先行实践。
用革命色彩衬托的扶贫当然是隐喻性的。阶级敌人不再存在,自当需要告别革命;但革命当初誓言要彻底消除的贫困依然存在,革命的“敌人”自然存在。因此,革命的本质任务仍未完成。在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其掌握的政治和体制资源超越现有科层技术和社会利益群体的束缚,对扶贫的社会经济资源展开重新分配,动员资源的力度和强度几乎达到了历史之最。中国共产党通过其领导的国家体制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展现出相比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国家能力的根本性提升,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既能发动面向市场的改革,同时也有能力矫正发展差异的强大体制优势。脱贫攻坚的实践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社会发展行动的范畴,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外溢。但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后这场极为少见的大规模的民生实践,却很少有从贫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的关系角度展开的讨论。
近年来,在党史界对于革命主题的传统关注以外,社会学家提出了“把革命带回来”的学术倡议。[1]思想界和社会学科界似乎正在为从“革命”的发生逻辑出发,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文明和现代中国的思想变局这样的宏大叙事做学术准备。[2]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形态”的脱贫攻坚实践,为研究中国党政国家的机制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塑造新的政治传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并非对革命和后革命的含义展开学术讨论,也不是对脱贫攻坚展开评价,而是旨在借用“革命”和“后革命”的表述,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变革逻辑上,讨论这场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民生运动的意义。
貧困: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
革命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表述。革命几乎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段最主要的标志。与中国历史上江山异姓、改朝换代的“革命”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发生的革命开始脱离朝代更迭的传统模式,逐渐开始与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西方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相联系。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进入一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主要是因为清王朝统治体制之内已经不存在应付外强内乱的可能,体制外的倒逼机制自然形成,这就是地方势力(中下层官绅和民族资产阶级)、民间社会(会党和新知识界)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新军)的自下而上、内外呼吁的造反运动。[3]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的体制外造反力量与晚清之前改朝换代的造反力量,在构成、思想资源及行动样板模式上都完全不同。
尽管有学者从儒学的自我批判、阐释和修订机制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晚清以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延续和本土现代性的结果。[4]但是,19世纪中叶国门逐渐开放后,中国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应对性”的变革动力的观点并非完全来自推演。当清王朝几百年统治走向没落之时,欲取而代之的反抗者不再是那些重复历史轨迹的传统变革力量,而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之落后根源与制度的革命者。如果说民不聊生是中国历代朝代更替或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的话,那么清王朝统治的危机也不例外;但与历史上的造反者不同的是,清末革命者的主张是通过与西方的对话和反思后获得的,是中国历史上继宗教文化的学习之后,又一次系统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全面反思性学习。
贫困问题是引发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危机最为重要的动因,是穿越不同革命阶段的重要线索。1904年光绪发布的一道圣旨中指出“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光绪皇帝虽然认识到了中国民力已极凋敝,也就是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是他无法认识到清王朝的体制和机制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从而缓解贫困的现实,而革命者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通过实现现代化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严复认为贫困是中国的大患:“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严复不仅将贫困提到了中国所有问题之核心的地位,同时提出路矿扶贫(可以认为是“要想富先修路”思想的来源)、教育扶贫、综合扶贫与小农经济扶贫的一系列扶贫主张。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也是建立在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上,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贫困形成的原因。他在1924年出版的《民生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以民生为重心”的三民主义的治国方略,力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5]
虽然通过推动现代化实现中国富强并消除贫困,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的一致主张,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实践并未使国家步入摆脱贫困的轨迹。对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民间社会和市场极不发达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发生。先由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重新建构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型国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是正如罗荣渠指出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清王朝解体后并未建立起一个现代型国家。[6]国民党虽然在民国的国家建设中试图通过以党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克服辛亥革命之后多元地方权力中心导致的现代型国家建设的障碍,但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依然是一个由多元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左右的联合体,其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与中国乡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