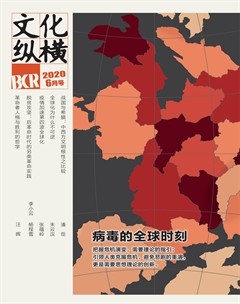[文章导读]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后,我们对于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的期冀也越发强烈。然而回顾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既取得了不少成就,也有过停滞或挫折。那么,推动技术创新的隐秘动力究竟是什么?本文以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为例,揭示了政府调控下的集竞争与合作于一体的模式,是这一领域创新成功的根本。更重要的是,文章细致地回顾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铁路领域的诸多行动者,如何因应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在竞争合作模式的大框架下创造和调试出不同的具体
机制,以持续推动实现技术创新。两位作者认为,在技术创新领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效率或最优模式,有的只是能够适应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对最优模式”。这也提醒我们,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不能沉湎于一时一地的成就和定式,而是必须坚持改革,必须对中国发展模式不断进行再讨论。
金融危机爆发十年有余,世界经济发展受阻,国家保护主义日趋明显,英国脱欧愈演愈烈,中美、日韩等国间的贸易摩擦频发,美德等发达国家重提制造业回归,种种迹象表明“后全球化”时代正日益逼近。[1]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技术合作模式面临挑战,获取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成为各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否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创新路径?这是学术界乃至政界、商界多年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中国技术创新不断探索的70年。这期间既有两弹一星、高铁、特高压等多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也有汽车、芯片等技术仍待提升。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成功,又是什么导致了技术研发的迟缓?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技术来源论将中国技术创新成功归结为技术引进的功劳,但这种观点在解释中国汽车技术创新时遇到瓶颈;创新体制论则强调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一统体制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解释过度强调政府单方面的因素,忽略了政府与其他行动主体(如企业、高校等)之间的制度关联。[2]
本文以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为例,深度剖析中国技术创新成功的根源性力量。我們以往的研究发现,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模式(以下简称“竞合模式”)是推动中国高铁技术创新的根本。[3]这种模式包含三种组织关系,即政府调控下的协调与控制、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受控竞争与产学研之间的合作。[4]在此基础上,本文要回答的是,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与“怎样”推动创新的。竞合模式在中国铁路产业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制度演进,这种“最优”的创新模式是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构建的结果。
一、创新中的竞争与合作
(一)何为技术创新的“最优模式”?
自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最优”模式的探寻从未停歇。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们坚信,存在一种理性的“无形之手”指引市场走向“最优”。基于此假设,学者们先后提出了竞争或合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创新模式。熊彼特及其继任者新熊彼特学派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指出企业家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动进行创新,因而竞争模式就是促进创新的最优路径。[5]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产学研合作模式下,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技术转化壁垒被打破,大大提升了技术研发的效率,精细分工下的合作研发模式能更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因而合作模式被认为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最优路径。[6]
发展型国家理论兴起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通过产业政策概念被引入创新理论,打破了原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论,同时集聚竞争与合作两种模式的竞合模式由此出现。[7] 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经济的崛起,发展型政府成为有别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兴代表,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卡特尔这类在英美被认为阻碍自由竞争的行会组织被接纳,甚至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通过卡特尔组织强制推动产业内部各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由此形成由少数寡头集聚的有限竞争市场。[8]因此对发展型政府而言,有限竞争环境下的竞合模式是推动创新最有效的路径。
(二)“最优模式”的社会建构
为何同是“最优”路径,却演绎出三种不同的模式?这是传统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的盲点。事实上,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三种不同的“最优”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所谓的“最优”是某一特定场域环境下社会建构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微电子工业的兴起,硅谷被认为是当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集聚地,以英美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因此被视为创新力培育的“最优”孵化器,进而不可避免地在世界各地广为扩散。然而,石油危机后亚洲四小龙崛起,尤其是丰田模式在制造业领域迅速扩散,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受到了挑战。合作模式和有限竞争环境下的竞合模式开始被接受。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亚洲四小龙衰落,英美自由竞争模式再次成为主流。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世人对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与此同时,逆势而上的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黑马,各国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经济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竞合模式。

由此可见,某种模式被认为最有利于创新,并非源于其具有超越制度环境的“绝对效率”,而是因为其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域环境之下实现了“相对最优”。当某种模式在某一时间节点最有利于推动创新,研究者们便会将其理论化,总结出所谓的最佳路径;但随着时间推进,这种模式走向下坡时,便会出现负向论证,重新树立起一种新的“最优”模式。[9]可见,组织理性下所谓的“最优”路径,并非源自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效率,而是因为其在特定制度环境之下被赋予的“合法性”及“高效性”。
二、中国高铁竞合模式的社会建构
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铁路速度等级实现了从每小时160公里到350公里的三级跳,并成功研发具有中国标准的高速动车组列车“复兴号”。提及这些成就,大多数研究认为这是中国举国体制下合作模式的典范,但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不仅有产、学、研的三方合作,更有政府调控下的寡头竞争,这种集竞争与合作于一体的模式才是创新成功的根本。一方面,国务院及原铁道部、科技部等相关行业部委以项目制的形式集中全国人才,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有意识的产业调控,在铁路产业内部树立两大列车制造企业龙头,引进四大技术系统,形成行业内寡头竞争格局,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
如果从表面现象来看,中国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的形成似乎是政府有意识安排的结果。诚然,这期间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绝非制度决定论的结构主义。如果统览中国科技社会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技术并非脱离政治、经济与社会而独立存在,中国高铁创新模式的形成深深“嵌入”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模式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在不同时期,竞合模式的形成与扩散表现为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不同机制。迪马乔和鲍威尔将制度形成与扩散的三种机制概括为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和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强制性同构是指组织面对法律等正式压力时的趋同行为,但在中国,强制性同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压力,只要这些压力来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更强势组织,比如政府的规章制度、党内法律等。模仿性同构是指组织的制度模仿,这种同质化往往发生在组织转型或者目标模糊时。规范性同构主要来源于专业化和共享的知识框架,这些将在领域内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制度环境,最终导致制度的扩散与趋同。[10]无论受哪种机制的推动,创新模式的最有效路径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非仅仅是经济理性的产物。
(一)第一阶段:制度遗产与强制性同构
竞合模式的形成初期,主要表现为垄断竞争格局:所谓垄断是指铁道部一级的行政垄断,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制度遺产;所谓竞争是指路局一级的市场化竞争。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铁路运力不足的瓶颈,中国启动高速动车组研发。此时恰逢市场经济改革浪潮,打破计划经济,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成为改革重心。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打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环境。在强制性制度的压力下,中国铁路产业也被迫顺应改革方向,探寻市场化改革路径。原铁道部对原计划经济时期下辖的30余家列车制造企业(以下简称“主机厂”)、5家科研机构和10所高校进行转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