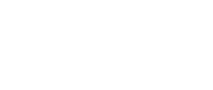一
出了火车站,吴向葵偏起脑袋看了看太阳。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到一个地方,先把太阳的方位确定下来,就分得清东南西北。
昏昏沉沉的日头正努力向西滑落,像个混日子的人,希望早点结束这一天。风沙弥漫的天空却像没疯够的浑小子,把贫血的太阳搓揉得像一枚掉进黄沙中的蛋黄,随时准备侵吞。太阳却也顽强,无论如何不让浮沙附着上去。浮沙只好从一侧进入,横着飞过太阳表面,又从另一侧滑出去。
要是在1999年之前,无论从哪里回来,双脚只要沾到这块叫廊坊的土地,吴向葵闭起眼睛都能分辨东南西北。这里是他的故乡。
1999年规划东方大学城,圈地的时候他想,将来无论安置到什么地方,老家的大致方位,即便化成灰,他都能指认得出来。等大学城建好,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实验楼、图书馆、食堂、报告厅、影剧院、设计院、绿化带、道路、水渠、橱窗、车棚、操场,一应俱全,从前的村庄、小路、老树、田地、水窖、看庄稼的窝棚、老水井……一样都没有了,他便迷惘,怀疑自己出生在这里、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征地之后,他们便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去了香河县,门前有条潮白河,儿子吴潮白的名字由此而得。两年前,潮白河边上的房子被开发掉了,换成了几大沓钞票和两张拆迁证,钞票悉数供儿子留学美国。这小子倒好,出了国就成了国际公民,一年半时间,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发过一条短消息,更别说写哪怕只有一句话的书信了。吴向葵爱读书看报,借用曾经读过的一句话,他们一家就像水上的浮萍、风中的叶子,到了哪儿,都找不着自己的根。看,在这陌生的故乡,不看太阳,他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看手机上的地图,就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二十多年时间啊,好像换了好几个世界。
北方9月底的傍晚已经起了凉意。而这时节,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啟东,暑热正盛,偶有凉风也似做客,十天半月不来一回,夜里倒是凉快许多。到10月份,白天才会起凉意,真正到了秋天,都还有秋老虎出没,冷不丁地,把人热得喘不过气。出门时他竞忘了自己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的天气,身上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背包里塞件灰夹克,把地里的活儿向孙小涓和几个工人交代一番,就上这里来了。
把夹克拽出来穿上,不过举手之劳。吴向葵嫌麻烦。他往下拽了拽衬衣下摆,耸耸肩,把背上的牛仔包背正,迈开腿向龙珠骐达工地走去。四五辆摩的围上来问他要不要车,十块钱一个。他摆摆手。下火车之前,他在手机地图上查过,龙珠骐达工地就在火车站附近,出了火车站广场朝北,拐上新华路,走上一千六百多米,两千来步,到了金光道过马路,左拐便是。
吴向葵来找自己的老婆潘慧。
这一趟不为别的,只为跟她办离婚手续,他俩的户口都还在香河。
吴向葵说不清白己的心情。说喜,有二十多年一起承担过的风风雨雨,不可能说断、说离、说舍,就能断离舍;说悲,毕竟孩子大了,无须承受更多的来自孩子脆弱无助的成长悲哀。当然,一桩没有前景的婚姻终究是要了结的,早晚的事,早了结比晚了结对双方都好,断离舍之后,谁也没有机会互吐不快,摩擦的机会就没有了——既然没有好好年轻过,彼此撒手,各自认认真真变老。
想当初,他们也算相洽的一对,经人介绍认识,彼此满意对方。婚后,吴向葵的父母随他弟弟去天津做生意,定居在那头。潘慧只有一个老娘,爹早死了。她这娘却是个倔强强硬的人,寡居之后,先后相了一两百次亲,跟七八个各种形状的老头儿生活过,她倒是有心跟人家相携到老,可人家受不了她的臭脾气,长则两三年,短则两三个月,全都不欢而散。
潘慧的老娘本想靠潘慧的爹留下的房子换套新房,等了好多年,左等等不到拆迁,右等等不到开发,自己的婚姻大事左右不如意,实在耐不住性子,一气之下把三百多平方米的旧屋换成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跟他们住到香河去。
不住在一起倒也无妨,隔得远,再臭不熏人。住到一起,问题来了。别的老太婆看女婿,越看越欢喜,这个老太婆看女婿越看越来气。不是嫌女婿眼不巧,就是嫌女婿不会哄孩子,要不就嫌女婿做的菜不合口味,还嫌女婿没事就喜欢讲古,她责备女婿说:“都是棺材里的事情,有啥好嚼舌头的?你的本分是好好干活儿,好好吃饭,而不是整天口嘚啵嘚啵,用嘴巴挖祖坟!”
吴向葵呢,起先装憨,心想您是长辈,您是潘慧的娘也就是咱的妈,您高兴教育几句就教育几句,您想要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咱拿耳朵听就是,不一定搁到心里去。日子久了,再好的脾气也憋不下了,尤其是当着街坊邻居的面,三分薄面都不给,得了,咱下地劳累回来做上饭菜端上桌,还嫌七嫌八,要顺口自己动手啊;咱吭哧吭哧干一天活儿,没找到个说话的人,还不允许咱吃饭的时候唠几句嗑?你们是咱的家人,咱在你们面前不说几句,难不成要让咱做哑巴……一来二去,就算交上火了。大仇恨没有,小矛盾不断。日积月累,也算一桩大功德。
等吴潮白到了叛逆期,吴向葵教育孩子要刻苦用心、要听老师的教导。话音未落,孩子立马用他老爹顶他外婆的事儿,反过来教育吴向葵,自己都没管好自己,有什么资格做他的爹!看你这窝囊劲儿,不张嘴猥琐得像孙子,一张嘴不是跟外婆干仗就是骂你的儿子,我像是你亲生的吗?到考取托福,他向儿子表示祝贺,儿子吴潮白指着他鼻子对他说:“吴向葵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跑那么远不是说我有多聪明,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大抱负,而是,我耻于有你这样一个爹!我三百六十五天哪怕只看见你一眼,都觉得丢人!从此以后好了,你没我这儿子,我没你这爹,各人顾各人,眼不见心不烦,我讨口要饭也不来求你,饿死尿朝天!”二十一岁的孩子,说这话,得攒多少年的不屑和蔑视?
那时候香河的安置房还没有建好,租住在城乡接合部。话说到这份儿上,吴向葵觉得香河也没必要待下去了,对孩子教育的失败,让吴向葵觉得自己这辈子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忍耻含垢、茹苦含辛,都是失败。人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精心培养的孩子,竞成为自己最不期望的样子,成为自己的敌人。吴向葵把两套房的拆迁证卖掉一套,留了一套给老太太,带上潘慧,跟一帮闯世界闯出名堂的乡邻,到跟上海一江之隔的启东承包土地种菜。
人到中年,过去关系再好的两口子,都各自会背负一些不平和怨气。这种不平和怨气的生发滋长,跟生存的条件比如家庭条件、家庭背景,甚至跟生活地的土壤和温度,都有极大关系,一旦机缘成熟,爆发起来,夫妻感情就像白瓷碗上的裂缝,越敲越大,直至破碎分裂,无法修补。从干燥的北方来到湿润的南方,潘慧尤其不适应的是,冬天屋子没有暖气,又湿又冷,钻心刺骨;到了梅雨天气,一天不搓身上的皮垢,便黏黏腻歪,从头到脚像刷了层糨糊;夏秋风大,吹大风的时候,潘慧随时担心被吹到天上去;要是遇上台风,她便整天担心房子会腾空而起。
在启东过得不如意,潘慧就想香河了,哪怕那里没有家,没有孩子,毕竟还有个老娘。她开始念叨吴向葵,要是当初忍气,何至于把孩子言传身教成那番模样。吴向葵心灰意冷,潘慧有哥哥两个,两个都不待见他们的老娘,以媳妇不同意为由,拒绝接纳他们的老娘。是他一个做女婿的“收留”老太太,不但有吃有住,有病有痛都是他顶风冒雨蹬三轮车上医院,药费全包。孩子的外婆起初责骂吴向葵的时候,吴向葵希望潘慧替他主持公道,或者请她母亲悠着点,毕竟是母女,话轻话重都能自我消化,谁想潘慧跟个没事儿人一样,一句腔不搭,光顾照料儿子。等后来他跟潘慧的娘交上火,潘慧反倒成为她老娘的帮腔;等到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成长叛逆期,孩子一跟他顶嘴,那老太婆就在一边自说自话:“屋檐水点点滴,滴滴无差异。吴潮白是有样学样,都是跟吴向葵学的。老天有眼,真是报应!”吴潮白得了他外婆撑腰,越发不听吴向葵的。吴向葵便谁也不指望了,每天只认着当牛做马干活,生活一无趣味,什么日子不日子,生活不生活,将就过呗,熬过一天算一天。
今年春天,一场谁都理不出头绪的吵架之后,潘慧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回到北方,一个月后发短信说,她在一个叫龙珠骐达工地上做塔吊指挥。两个月前又发信息来说,孩子大了,没有其他负担,南方她过不习惯,大家好合好散。她让吴向葵抽时间先到工地,然后一起回香河办离婚手续。眼看都是奔五十岁的人了,还有半世的人生,各自找个人,好好从头开始,翻篇继续。他想也是,从此以后,岳母的责骂一笔勾销,潘慧的责备一笔勾销,跟吴潮白的父子感情也一笔勾销,他便想也没有多想,同意了。
潘慧给他发消息:有件事咱要先跟你说好,算咱求你,你来便来,不要惊动别人,也不要让别人看出咱离了婚,只要你不说,工地上便没有人知道咱离婚。她还说,到了这个年龄,重新单身,人家想骚便骚,想扰便扰,谁也不珍惜,谁也不在乎。
龙珠骐达工地大得超出想象,横向和竖向,各有两公里多,每个方向一道门,一共四道门出入。吴向葵根据太阳判断的方位,找到了西门。
太阳在天上彻底消失,风越发吹得起劲,冷意浓厚。站在西门边上,吴向葵到底抵抗不住寒气,把牛仔包移到胸前,拽出外套加上。
西门口,车辆只见出,不见进。因为大风,工地暂停夜班。楼房上刺目的灯光从脚手架和安全网中照射出来,明亮的地方比太阳底下还要明亮,背光的地方一片漆黑。
半个小时前,潘慧给他发微信,让他六点钟在西门口等她。此时,只见五六个年轻女子戴着安全帽向工地门口走来。女子右手腕上各自挎了个透明的塑料包裹,装着毛线球和小半截成品,口子上露出三根竹棒针。她们在准备过冬的毛衣。一个壮硕的男子挡在她们前面,扯开嗓门大吼:“不准上去!”头上的板寸,随他咬字的节奏一耸一耸的。
吴向葵心想,都快下工了,这群女子还进工地干吗呢?手上的毛线扦子表明,她们不可能是工地上的工人。
二
一个长发大眼的年轻女人,用怎么压也压不下去的铁岭腔问那男子:“工地上有哪一条规定不准我们上去?”
男子说:“别的时候可以打个马虎眼。今天风大,工地马上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得下来,包括你们的男人!再说,在这块地方我说了算,我说不准就不准!”
另一个短发的漂亮女子,把手上的饭盒往男子面前一送,說:“我们是去给我们各家的老公送晚饭的。”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们手上捧的是饭盒,腋窝底下夹的都是什么?你们以为我不懂你们那挡子事?”男子说。
吴向葵注意到,女子们腋下要么夹着一床草席,要么夹着旧床单。
一个两排牙齿又白又整齐的女子,脸上不笑都带三分笑意:“既然你都懂,就不能光顾自己吃饱,忍心看我们挨饿是吧!你多行好事,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管的工地大吉大利,不惹是非。”
“就你们这点花言巧语,不可能让我改变主意。好好的房子,房主一天没住,倒给你们涂满了精斑!不像话!太不像话!”
长短不齐的笑声立即从这一小堆女人中传出。有个女子低声白说白话:“啧啧啧,‘精斑’,好深奥哦!”这女子扭头问旁边一个说:“这两个字怎么写?”
旁边一个笑得哧哧哧地开她玩笑:“你是专家还问我!你们哪一趟写这两个字不要半个小时的?”
旁边另一个抖着刚洗过的长发笑着搭腔:“半个小时够?别人一场足球赛都踢完了,他们还写得热火朝天。”
说笑一回,女人继续跟男子交涉。这时说话的明显是四川口音:“朱锅锅,你做个好事要不要得?反正今天吹大风,不加夜班,那个啥斑,又不会在楼板上发芽。菩萨都说,人世最大的善,就是与人方便。你看菩萨都说了得嘛,你多正经就太没名堂了哈!”
“有本事你告诉我你们男人是谁,你们现在告诉我,我下一分钟就让你们的男人滚蛋。本人向来说话算话,说一不二。”板寸男发火了,他停留了差不多一分钟,继续用火爆爆的声音说,“不说是吧,不说你们打哪里来回哪里去。”其实她们的名字他个个喊得出来,跟她们的男人住哪间板房他也一清二楚,关键是这时候,他就该含糊。
女人们不再说话,脸上除了愤怒,还有失望,看他那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只得各自散了,向西跨过马路,消失在横七竖八乱糟糟摆放的板房宿舍。“变态”“遭瘟的”之类词语随着她们远去的脚步,像秋风中的黄叶,在风中翻滚。
灰蒙蒙的薄暮里,到处是紫红色的灯光,马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时间已经过了六点,还不见潘慧出来。那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赶走了女子,注意力就集中到吴向葵身上,他看吴向葵的眼神怪怪的,好像知道他是谁,又好像很陌生,既有想搭腔的意思,又有几分躲闪。他没跟吴向葵说话,吴向葵也不想跟他说话。从刚才的阵势看,吴向葵估计他是个工头。也就是说,他是潘慧的领导。吴向葵心想,在工地上,潘慧凭力气吃饭,再说马上也不是我的潘慧了,我没必要跟你黏糊,更没有必要套近乎,下矮桩。
天黑透,灰蒙蒙的天空不见了,城市上空反倒映出一片鸡蛋清般的光明,在这片光明之下,所有建筑物的轮廓都分明起来。夜空变成紫色的,所有灯光都偏蓝。北方的天空赶不上长江人海口干净。他种菜的启东,早在几年前,空气质量就赶上欧洲标准。有时候,他感激时代变化,如果不是城市开发,他可能一辈子就窝在大学城那片土地上,在直径十公里范围内终老。如今,他不仅有资格评说大学城那片土地,评说香河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庄稼和河流,还能评说启东那片土地的肥力、墒情、农时和蔬菜市场行情,他伺候土地是一把好手,他的菜地一年四季都被他周密筹划得生机勃勃,种什么出什么,出什么卖什么,样样都能卖出合适的价钱。有时候他又怨恨这种变化,如果城市不开发,潘慧的娘就不会住到他家去,孩子在相对单纯的环境下成长,他们的生活平静如水,说不定这会儿还在为把秋天最后一批粮食搬回家而忙碌呢!
正走神,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他:“大侄子,你什么时候到的?”
扭头看去,是大学城从前那地儿的表舅九成仙。回头一算,快二十年没见,表舅一脸老相了。表舅不是亲舅,是亲舅的隔房兄弟,年轻的时候跟人学修道,自称学到九成,不需要干活,也不需要吃饭喝水,给他爹一怒之下锁在屋子里,一锁锁三天,饿得气息奄奄,用剩下的两口气求爹告奶要吃要喝。修道不成,不妨碍被心胸宽广的乡邻喊做九成仙。九成仙一身灯光从工地里向大门口走来。吴向葵答道:“刚到,表舅。”九成仙跟那守在工地门口的男子打了个招呼,向他介绍吴向葵:“这是潘慧的老公吴向葵。”转过背来,指着那男子对吴向葵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朱可以朱经理!”
朱可以拍拍身上的灰,取下安全帽挠挠后脑勺说:“有钱发给大家就是经理,没钱发给大家卵都不是!狗日的这帮女子,弄得我天天晚饭吃不安生!”
九成仙也拍拍身上的灰,取下安全帽说:“让我说,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在家好歹还有张床,是狗也得找个清静的地方,如今人家顶多临时占你草席大一块地。”
朱可以说:“新砌的房子,给他们这么胡搞,传出去,影响整个工地的声誉。再说今天吹那么大的风,也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你没见我以往,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九成仙说:“你不想想前几年,大家都不带家属,工地开到哪儿,洗头房就开到哪儿,按摩院就开到哪儿。不干净不说,还动不动给人打电话要你们这些做经理的拿五千块去捞人,这又不影响工地的声誉?”
两人说罢,向马路对面的板房宿舍区走去。朱可以让吴向葵跟他走,九成仙对朱可以说,让他等上他老婆再走。朱可以便扭头跟著九成仙走了。走出去十几步,九成仙转过头来对吴向葵说:“你这一来就不走了吧?我记得你会电工,要是不走,我们这里正缺人手。过几天我约上几个老乡来给你接风。”说罢,没等吴向葵回答,转身跟朱可以走了。冷风把他们的交谈越吹越远,他俩说话声音大,背对着吴向葵也能听清一些。朱可以给九成仙递了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打火机把他的脸照亮,他似乎早就知道吴向葵要来。朱可以对九成仙说:“裤裆里那点事,不好管啊!”
“让我说你就别管。我们建的是商业楼,商业楼就该热闹点,留点骚气,说不定将来商铺开张,红火得像开合法妓院!”九成仙说。
“你个狗日的,整天光知道满嘴跑火车!”
他们后来还说了些什么,吴向葵没心思听,潘慧来了,潘慧手里捏着两把卷了一半的信号旗,一红一蓝,脖子上挂着哨子和对讲机,戴着安全帽,披着一身工地的电灯光,向他走过来。七个月没见上啦,仇恨再大,马上也吵不起来,何况他们那些事情都是一地鸡毛。客观评价,潘慧算得美人,个子不高,墩笃匀称,该凸的地方,凸得恰到好处,该翘的地方,翘得低调奢华。从前面朝黄土低眉顺眼,如今在工地上整天上瞅下看,看人的眼神自然多了几分自信和沉稳。
要是他们不是要离婚,按照电影里的情节,潘慧也许会把信号旗递给吴向葵问:“你想不想咱啊?”“想!”“哪儿想?”吴向葵嘿嘿笑:“哪儿都想!”
实际情况是,潘慧没有递信号旗,没有撒娇,也没有说更多的话,只说:“该吃晚饭了,咱带你一起去吃饭。”
在路上,潘慧说:“咱过两天才休班。”吴向葵心想,也就说大后天才能上香河了,一起过了二十多年的日子,多这么几天,谁好意思嫌多呢。
三
从板房宿舍区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出来,夜更深了。潘慧取下安全帽,一头秀发散落下来,从前的波波头,又长了一柞,靠发根那一半溜顺,发梢卷成了卷。要是在他们刚做夫妻那几年,吴向葵会用指尖挠起她的卷发说:“看,北方的风真懂行,把你头发吹卷了。”这是变着方儿表扬潘慧,潘慧一定会晃晃脑袋,笑得像个孩子,脖子两边浪花飞卷。过去的岁月,虽然彼此怨气深重,可只要愿意打捞,到处都是愉快的记忆。这时候,愉快的记忆只会让人越发悲伤,越发坚定离婚的念想。
吴向葵不知道,为给吴向葵留下个自信、翻篇儿就能扬帆远航的印象,潘慧前天特意请假,到街上花费108元巨资烫了个头。
走到宿舍区门口,潘慧对吴向葵说,工地上有不成文的规定,家属来工地,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意思是说,他今晚跟她挤一个被窝。吴向葵没有意识到潘慧住的是集体宿舍,心想,只要那张证还没领到手,挤一个被窝合理合法。
宿舍区的板房一共七栋,每栋两层,每层三间,每间都是前门后窗,每间四张高低铁床,床柱与床柱之间,只要能牵绳子,都牵上了绳子,绳子上晾晒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洗漱的,聊天的、唱歌的、打麻将的、喝酒的、抽烟的,热闹非凡。每间敞开的门里都飘出热气烘烘的气味,每道门里的气味大不一样,麻辣味的具有四川特色,大葱味的充满山东韵味,还有酸醋味的,霉干菜味的,泡萝卜味的……无一例外地,都混合了方便面气味、脚丫子臭味和汗臭味。
潘慧的宿舍在第五栋二层尽头,八个年轻女子住一个屋子,潘慧的铺位在靠窗的角落里。走到宿舍门口,吴向葵不进去,这怎么能住?八个女人,一个男人,这哪是咱跟潘慧一个女人挤一个被窝?这简直就是咱一个男人跟八个女人一屋睡觉。平生第一次。
潘慧转身,果断坚决而且别无选择地明确对他说:“委屈你,今晚上只能这样将就了。”转身对同室的其他姐妹说:“姐妹们担待些哈,这是咱老公!”
吴向葵个子高,眼神散乱,跟在潘慧身后走到铺位前。横七竖八斜拉着的绳子上的胸罩和内裤在他的头上打来打去。屋子里乱七八糟,洗漱用品、简单的化妆品、台扇、小吊扇、面盆、水盆、帆布胶鞋、高跟皮鞋,诸如此类,摆得随心所欲。
其他七个女人大概都是结过婚的,对潘慧领着自己老公进屋并不觉得奇怪。
吴向葵估计她们自己的男人来了工地,大抵也这般处理。潘慧再次跟那几个女人打招呼:“姐妹们,今晚给大家带来不方便啦,包涵包涵!”
一个正脱裤子的女人说:“你自己的老公有什么不方便的,大家都是出门人。”说罢脱了裤子,粉色碎花的内裤在床前闪了一下,消失到被窝里。
另一个女人在唱川剧,进门的时候正“汤菜,汤菜,汤一钵钵菜一钵钵,汤一钵钵菜一钵钵,汤汤菜,汤汤菜”吼得热闹,这时唱道:“你夫妻依旧是多情眷,反显得小青心意偏,倒不如辞姐姐天涯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