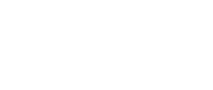一
第一次看到《是一是二图》的人,一定会感到诧异,因为在这幅画上,一个身着汉人服饰的文人正闲坐榻上,身边的家具上,摆满了名器佳品。在他身后,有一道画屏,这种以画屏为背景的绘画,我在《一个皇帝的三次元空间》里说过了。但这幅画有意思的地方是,屏风上挂着一幅人物肖像,画的正是榻上坐着的那个人。
看过乾隆朝服像的人一眼便可认出,座中与榻上,都是一个人——乾隆。
与父亲雍正一样,乾隆喜欢在绘画里玩cosplay(“变装游戏”),尤其喜欢在画里把自己打扮成风雅之士,比如,在《王羲之采芝图》上,我们看到的年轻王羲之,就是一位头戴凉帽、手持如意、衣带生风、神色淡然的青年才俊形象。
《平安春信图》比《王羲之采芝图》更加有名。关于图中人物的身份,学者们有不同的指认。故宫博物院聂崇正先生认为,图中年长者为雍正,年少者为乾隆。巫鸿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年长者是雍正,根据是他的长相与雍正的其他画像一致,尤其是“嘴角蓄着向下垂着的小胡子”,“他表情严肃,站得笔直,正将一枝梅花传交给王羲之”,“而身为皇子的后者恭敬地接过这枝花,他上身微微前屈,显得几乎矮那位长者一头,抬着头尊敬地看着长者。”扬之水、王子林则认为,《平安春信图》的长者不是雍正,而是乾隆。
但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平安春信图》中至少有一人是乾隆——要么是画中长者,要么是画中少者。
目前在故宫博物院,共藏有四件《是一是二图》,画面构图基本相同,唯有第四幅(落款为“长春书屋偶笔”)中屏风上绘的不是山水,而是梅花。2018年秋天,故宫博物院家具馆在南大库开馆时,不仅复制了《是一是二图》,而且用清宫家具,恢复了这幅图上描绘的物质空间——坐榻几案、葵花式桌,都与图中的摆设一模一样。
从这些绘画可以看到,乾隆不只是恋物癖患者(这一点很像宋徽宗),同时也是严重的白恋症患者。他一再让自己成为图像表现的对象,在宫廷绘画中不停地“抢镜”,而且,在同一幅画中,他的形象也是反复出现,与自己形影不离,就像他在《是一是二图》的题诗中的所写(四个版本都有):“是一是二,不即不离”,让人想到李渔的名句:“是一是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
二
乾隆的“变装照”与雍正的不同,雍正的“变装照”(参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虽然变化多端,但画中只有他一个人。或许,只有在一个无人(没有他人)的世界,在不被观看的环境里,雍正才能从皇帝的身份中逃离,回归“真实”的自我,才能玩得尽兴,一旦回到人群,他的表情、身段、举手投足,又将被“体制”套牢,所有旁逸斜出的个性都被删掉,重新变回那个死板无趣的皇帝。
乾隆与他爹的不同在于,在他的“变装照”里,总是有“别人”存在的。比如《王羲之采芝图》里,有一个小青年,右手荷锄,左手提篮,神情专注地看着乾隆;在《平安春信图》里,假若如扬之水等人所说的,长者为乾隆,那么他身边同样有一个年轻男子,手持梅花,恭敬地站立。《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同样不会形单影只,除了那弯腰恭立的童子,在乾隆身后的画屏上,还挂着自己的肖像,仿佛一个老朋友在注视着他,与他娓娓倾谈。
假如说乾隆自己是“变装照”里的主角,那么画中的配角,仍然是乾隆。乾隆在画里纠集的“同伴”,原来就是他自己。有人把它称作乾隆皇帝的“自我合影”。也就是说,在这些“变装肖像”里,装着两个乾隆。《是一是二图》自不必多言了,《王羲之采芝图》和《平安春信图》中那两个恭敬站立的年轻人,其实也都是乾隆自己——这样说的根据是,从长相看,画面上的少者与长者很相像;更重要的,在《王羲之采芝图》有乾隆题诗,最后两句是:
谁识当年真面貌
图入生绡属偶然
而《平安春信图》中,乾隆题诗道:
写真世宁擅
缋我少年时
入室皤然者
不知此是谁
在前面一首诗中,乾隆暗示画中少年是自己“当年真面貌”。后面一首诗则说郎世宁擅长写真,绘制了乾隆少年时的容貌,让陡然入室的老者(“皤然”是用来形容白发的词),不知道画中人是谁。
其实,乾隆早已把破译这两组绘画密码的钥匙交到我们手里。
画来画去,看来看去,画中人,其实都是乾隆。
乾隆为观画者,摆下了一个迷魂阵。
三
乾隆是一个有着鲜明白我意识的人,他总是想看见自己。
作为皇帝,他主宰朝廷,主宰天下,成为所有人视线的焦点,他是被观看者,但他也希望变成一个观看者,希望变成一个外部的视角,来看见“自我”。他不想只做天空中的一颗孤星,他还想像一个黑夜里的旅人那样仰望天空。因此,在乾隆真实的生活空间里,镜子的元素时常浮现,背后隐藏的,就是他“看见自己”的强大冲动。
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里写过,乾隆花园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居处。乾隆二十五岁登极,日日勤政,等他年纪大了,疲倦了,就想歇歇了,去作闲云野鹤。乾隆在符望阁内题诗中写“耆期致倦勤,颐养谢喧尘”,就流露了这样的心境。在这花园里,埋伏着许多镜子的意象。水、月、镜、花,在这花园里,都落到了实处。
花园里有一座玉粹轩,此轩明间西壁上,有一幅通景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岁朝婴戏图》。画上有三位佳人、八个婴孩,在一间敞亮的厅堂里休闲嬉戏。画右的那位佳人,侧背对着观者,面对隔扇,望着自己。她的面容,透过隔扇的反光,被我们看见。这构图,不知是否借鉴了東晋顾恺之著名的《女史箴图》,因为在这幅手卷上,有一位对镜梳妆的女子,也是侧后方对着观众的,她的面容,通过镜子反射出来。总之,《岁朝婴戏图》里,那油漆光洁的隔扇,客观上起到了镜子的作用,透过这面“镜子”,画中美人才能打量自己的青春容颜,今天的观众也才能看见她的面孔。
《岁朝婴戏图》中的反光体,并不是真正的“镜子”。在倦勤斋——乾隆最私密的空间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镜子(玻璃镜子)。博尔赫斯同样迷恋过镜子,他说:“镜子是非常奇特的东西”,还说:“视觉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在一片玻璃、一块水晶里得到复制,这个事实真匪夷所思”。自从西方传教士把玻璃镜带人中国,在乾隆的时代,玻璃镜越来越多地在宫廷中得到使用。玻璃镜就成了一个无比神奇的事物,让一个人清晰地看见他自己,让他与自己相遇。
出于工作原因,我无数次走进过倦勤斋,但每一次进入,我都感到无比诧异。它是一座永远保持新鲜感、让人永不厌倦的建筑。倦勤斋是乾隆花园的最后一排建筑,目前没有开放,因此游览了乾隆花园的游客,从它的面前经过,最多匆匆扫上一眼,更多的人看都不看一眼,就从东侧门穿过,去看珍妃井了,对倦勤斋内部的秘密茫然无知。
这座建筑面南背北,面阔九间,分成“东五间”和“西四间”两个部分,内部被隔扇分成许多狭小的空间,有如“迷楼”。从“东五间”进入“西四间”,有一连串的小门,组成一个有纵深的夹道,乍看上去,恍若一面镜子。2018年9月,我们在那里录制节目,演员邓伦就以为那是镜子,但镜子里看不到自己。往里走,又怕撞到“镜子”上,邓伦就调皮地用手“摸”着前行。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这样的“假镜子”,设计得那么逼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乾隆很痴迷这种真真假假的游戏。乾隆在这里虚晃一枪,在夹道里制造了一个酷似镜子的假象,表明了他对“镜子”这一意象的热衷,也预告了在前面的空间,定然会有镜子出现。
穿过这些小门(好像从“镜子”里穿过),拐人“东五间”最后的一间小室,两面落地大镜终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