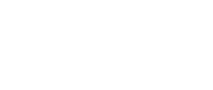教育……就像是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
——希波克拉底
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教育的馈赠。
——卢梭《爱弥尔》
我有一种很难克服的“整理癖”,不停地倒腾,再倒腾,一经多次倒腾,往往想找的东西找不到,没想找的反而碰着了。今年大年初三,我在书柜遍找黑塞的《荒原狼》而不得,却碰上了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着发黄变脆的纸页,那歪歪斜斜的墨迹,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刚上高中的那些日子。
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
高中第一个新学期来了,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还念错,一口甘肃民勤话实在太难懂,台下的学生乱成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得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自己的学生,后来管不过来,完全放任自流了。
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
补记:学校开大会时的秩序是历届校领导最头疼的一件事,至此为止,我经历过的各种全校大会,多数会沦为不欢而散的玩闹,能白始至终安安静静开下来的少而又少,会场的秩序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1977年底高考恢复,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三四个人被传为神话。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語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进步并不大。
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和安排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家修理钟表或收音机,因家庭成分不好,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记得新娘子腮上有两朵很深的高原红。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没有出现过多少谴责的声音。我有位小学同班同学曾四五次高考才圆了大学梦,二十多年后,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便兴奋地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高考,也吸引了不少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
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
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绕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路上,高(40)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
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其中最经常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权,高个子,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也不愿意当,反复找他谈,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地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女生别看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权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里才托他给剪发头女生鲍翠递过纸条儿。
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
座钟按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里刷完牙吃早饭,骑家里老旧的白行车来到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得出奇,没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裤裆会不会绷裂,张刚戴了副怪模怪样的墨镜,(42)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它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立华,课间操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补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个子不高,很精干,戴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学生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
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课,能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他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后,校园像被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改变着,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有变化。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院子里大大方方地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项目才可以,不管球类、田径、棋类。过去學校只有春季一场运动会,现在改为春秋两次,过去只有田径赛之外有篮球足球比赛,现在则增加了排球、乒乓球和象棋比赛。不管你过去是否爱唱歌跳舞,现在必须人人上阵。
1978年4月27日星期五,晴,无风
最近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一男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远,招来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白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副食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假装没看见。她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