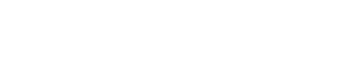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都是小姑娘呀!”
闷热的南昌午后,当我和摄影记者走进这栋工厂宿舍的老楼时,首先传来的便是杨本芬爽朗的笑声。
桌子上摆着切好的西瓜、泡好的热茶,她像任何一个寻常人家的奶奶,欢喜地迎接前来光顾的小孩,麻利地切菜做事,精力充沛,热情而明媚,浑然不见作品里的伤痕。
今年80岁的杨本芬,刚刚出版了她人生的第一本书—《秋园》。秋园,是她的母亲,本名梁秋芳,生于1914年,逝于2003年,跨越了中国社会的几番变迁,度过了时代更迭的诸多荒诞。
《秋园》是一本近乎复刻杨本芬全部真实回忆的作品。在这个“母亲一生的故事”里,杨本芬写了以秋园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写了一家人如何在时代的颠簸中挣扎求生,写了邻里乡亲的生生死死,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无需想起,不曾忘记
在杨本芬的书房里,我见到了凝固在相框里、88岁的秋园。她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扣子系得整齐,露出内里端正的白色立领。
杨本芬的大女儿章南记得,这件上衣是外婆88岁时南昌来,自己带她去买的料。外婆亲自挑了布料,说料子正面不好看,要反面,就用反面做了这衣服,拍了照片。“你看她这一生,都是小白领要露出来,对襟,扣紧扣子,很精致。”
拍摄照片的次年,秋园便去世了。那一年,杨本芬正在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孩子,自己也做了外婆。
母亲的死令暮年的她极为痛苦,也让她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人死如灯灭”,母亲在这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那些艰辛痛楚、一生颠沛,就白白经历了吗?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家里有许多藏书。年轻时就喜爱读书的杨本芬常常在家务闲暇之余找书来看。在不同的字里行间,她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母亲。她们像秋园一样,渺小又伟大—而文字,令她们音容闪耀,鲜活而永恒。
直到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再不写恐怕来不及了。在章红家,那个由封闭阳台改造成的狭长厨房里,杨本芬开始迫不及待地动笔。
她在厨房里写作。4平方米的空间布满水池、灶台、冰箱,容不下一张书桌。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用一叠方格稿纸、一支笔来写。写完的那些,就收进不怕水溅油污的塑料袋里。
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有时,是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的空闲;有时,是灶头炖着肉,等待汤水滚沸的时候。
杨本芬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种田、切草药、会计、承包汽车零配件仓库、供职汽运公司……没有一样与文学有关,她“喜欢看小说,很崇拜作家,觉得作家好了不起”,但从没奢想过自己也能像作家那样去写作。
但在女儿厨房抽油烟机的轰鸣声里,杨本芬发现,写作自己的母亲与过往,太容易了。只要提起笔,杨本芬觉得自己“像个演员进入了电影中”,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烙印在生命中,刻骨铭心;只要闭上眼想一想,画面就潮水一般地涌来,过去的日子拥在笔尖,争先恐后地等待被诉说出来。
“就像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翻涌的记忆里,杨本芬按照时间顺序,从妈妈的童年开始写起。
每写一笔,就是和妈妈重新相会一次。
1919年,5岁的秋园不谙世事,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阳,在雨后的屋檐下光脚踩水,还不知道命运为她准备了怎样的磨难。
1926年,12岁的秋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在那个春天,也永远结束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1931年,17岁的秋园用“送我读书”为条件嫁给杨参谋,也就是杨本芬的父亲。杨本芬为父亲取了化名“仁受”—这也像他的一生,仁慈善良、甘于忍受。
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1937年,23岁的秋园随同仁受供职的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在中途停靠的武汉下船,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吊桥那头。
1940年,26岁的秋园生下女儿杨本芬。在书中,杨本芬叫自己“之骅”,这是她旧时在家乡的名字。
30岁的秋园、40岁的秋园……挨饿、受苦、丈夫去世、改嫁、远走他乡,在漫长而苦痛的岁月里,她生下6个孩子,带活3个,夭折3个。孩子夭亡,丈夫早逝,社会饥饿动荡,苦难堆叠的一生里,她常说“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