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今昔扬州梦
姜夔,字白石,其父姜噩,进士出身,官至汉阳知县。姜夔自小跟随父亲往来于江西、湖北一带。一一七六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此时南宋已建立约五十年,他经过扬州时作《扬州慢》一词,序曰:“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词曰: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词常有词前小序交代与主旨有关的背景,文辞精心结撰,与词相映而成为一个意义整体。此词主旨是“感慨今昔”,文与词有主次之别,前者具交代背景的叙事功能,后者属象征性文本。通篇将晚唐诗人杜牧作为今昔盛衰的比照,以明譬暗喻手法将其有关扬州的诗句巧妙织入词中,而语言的平仄四声与音律波动形成情绪的节奏。读者仿佛被置于互文结构与文学记忆的迷宫,通过文学联想与情绪往复而体会作者的今昔感慨,达到对其自我形象的体认。
此词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起句,离扬州城外五里有竹西亭,表示自己路过以繁华著称的名都。指明地点已暗用杜牧《题禅智寺》中“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典故,由是文本开始舒张古今交叉的脉络,隐寓“感慨今昔”的主旨。“解鞍”息歇,刚下过雪,满目春光,田野上荠麦青青,作者心境舒畅。然而进城则满目荒凉。“自胡马窥江去后”乃回溯历史,指十六年前金主完颜亮领军南下,南宋江淮军败,扬州惨遭劫掠。序文已有“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之语,因此仅以“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足以表达残败荒芜的景象,从心理侧面表现谈虎色变的精神创伤,笔力凝练而雄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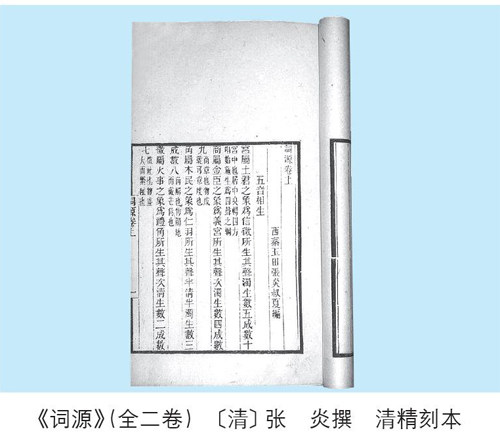
读者不难发觉,序文中“夜雪初霁”表明时值寒冬,与“过春风十里”相矛盾。其实这也来自杜牧《赠别》一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在文学记忆的作用下,作者魂附杜牧,似一个风流俊少在揚州路上,对诗中描绘的豆蔻少女不免浮想翩翩。“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沈括《梦溪笔谈》),杜牧对扬州情有独钟,在那里留下不少香艳踪迹,上面为一心爱妓女所作的《赠别》诗可见一斑。脍炙人口的是他的《遣怀》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这种真率颓唐的自白在唐代之前的诗歌当中很少见,而这一浪荡子形象在后世赢得的歆慕远超道德的谴责。像姜夔那样的文青自然会把杜牧当作偶像,更何况来到扬州。“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之句混合着悦目景色与文学幻想,然而进入城中,幻觉骤然破灭而跌入残酷的现实,“四顾萧条,寒水自碧”,一切似乎被凝固在历史时空中。末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总结一天里的奇幻感受,面对为凄清空寂所笼罩的现实,在此映照下“过春风十里”显出心理错觉的反讽,而作者与杜牧的重合镜像也告破裂。

词的下片也叫“换头”,须与上片气脉连贯,如张炎所说:“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词源》)如苏轼《念奴娇》中“遥想公瑾当年”与上片“三国周郎赤壁”相呼应。这首《扬州慢》的“杜郎俊赏”看似突兀,其实上片中隐约闪动杜牧的身影,这是姜词的微妙处。其中含有昔日扬州繁华的幻影,却在现实面前烟消云散,作者在追星失望之后显出其真身。于是在下片直接请出杜牧在前台亮相。所谓“算而今重到须惊”,作者似舞台监督为他安排重临扬州的角色,并快镜般摄下他眼中的惊愕表情。虽然“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已经以当地人口吻表现扬州所遭受的劫难之深,而这里通过杜牧的表情再度凸显扬州现状,为伤感加码。陈廷焯说:“‘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白雨斋词话》)姜夔利用换头的转折抒发议论,将“感慨今昔”的主旨推向高潮。“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中“豆蔻”与“青楼”分别摘自上引《遣怀》与《赠别》,典型勾画出杜牧落魄风流的形象,然而“难赋深情”如重磅一击,乃此词核心所在。意谓萧条异代,盛况不再,自己不可能像杜牧那样倜傥优游,而且处于国破家难的时代,像杜牧那样的风流才情是不够的,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首《扬州慢》在感情上更为深沉,由是与杜牧拉开距离而凸显带有时代特征的自我。
将近尾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继续使用互文策略,令人想起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也是描写扬州的名篇。玉人的箫声飘拂在明月照彻的“二十四桥”上,良辰美景足以销魂,略带赏心乐事谁家院的伤感。姜夔在衰败扬州的画卷上添加二十四桥这一标志性美景,“仍在”两字以去声落下,饱含遗恨之泪。“波心荡冷月无声”从杜诗化出,诗情画意统一在冷色调中,如死寂一般。其意境如“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刘熙载《艺概》)。这一“荡”字下得极重,万念俱灰,难掩内心激荡。所谓“一字得力,通首光彩”(先著《词洁》)。最后“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天道有常,草木无情,这一无奈的诘问纠结着万般思绪,给读者留下寻思回味的空间。

这首词读来不露艰涩苦吟的痕迹,而用语讲究,刻意追求一种清俊冷峭的风格。就运用典故而言,没有炫耀学问的习气,结构上看似单纯,围绕杜牧诗中的扬州典故而展开,把杜牧作为一面映照今昔的镜子,这无疑是独具匠心的选择。姜夔自言:“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杜牧的这几首诗脍炙人口,属于“熟事”,如“春风十里”“豆蔻”“青楼”与“二十四桥”皆“实用”杜诗,唤醒读者的文学记忆而在今昔对比中感慨万千,更精妙的是在“虚用”方面,即把杜牧作为繁华扬州的象征指符,同時通过自己与杜牧的镜像重叠,隐含自我从认同到抽离的过程。虽未直接抒发“感慨今昔”,但让读者通过暗示、意象与时空之间的想象而获得感官与情绪的体验与理解。布列松说:“隐藏观念,但要令人找得到。最重要的藏得最密。”(《电影书写札记》,三联书店2001年,页23)这需要一种高难度的表现技能。姜夔作这首《扬州慢》时才二十岁出头,技巧上相当圆熟,其清丽冷峻的风格已见端倪。

“艳词”传统的内在裂变
从词的发展来看,苏轼“以诗为词”至南宋大放异彩,形成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姜夔比辛弃疾小十来岁,不像同辈刘过、叶适等追随豪放一路。然而姜词中有表现感伤时事、不忘君国的内容,且有几首词是写给辛弃疾的,不免豪放风格的痕迹,因此不止一人把姜夔与辛弃疾作比较。谭献认为:“白石、稼轩,同音笙磬,但清脆与镗鞳异响。”(《评周氏词辨》)说两人同台演奏,调门不同。陈洵说:“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龙洲、后村、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二刘笃守师门,白石别开家法。”(《海绡说词》)“龙洲”即刘过,“后村”即刘克庄。这很像辛氏铁粉的论调,但说姜夔“别开家法”则另有见地。刘熙载说:“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艺概》)既把姜夔看作“才子”,就难作豪放派同道了。
更多的是把姜夔与周邦彦作比较,因为同属“婉约”营垒。其实自明代张綖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之后,至今似乎约定俗成,却也有简约化危险。“婉约”一路包括从隋唐以来的众多作者,远较“豪放”派复杂,涉及“源流正变”的问题,词家争论不休。周、姜之争起始于张炎的《词源》,他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自温庭筠、柳永以来不脱“艳词”范畴,周的“软媚”当然属于这一路。张炎以“清空”概括姜夔的词风,标举“骚雅”的高格调,由是把周邦彦比了下去。
但是周邦彦也有不少铁粉,如沈义父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语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最为知音”指周邦彦精通音律,徽宗时担任国立音乐机关大晟府提举,而法度和用典指他对词朝“雅”化方向发展的贡献。近代陈匪石曰:“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宋词举》)其实千门万户互相影响,流变多端,复杂交叉,任何定于一尊无非是一家之言。
较为平允的如黄昇曰:“白石词极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绝妙词选》)陈廷焯说:“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白雨斋词话》)都认为姜夔的“气体”高于周邦彦。最为形象的是郭麐把词分为四种“体”式,一种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从《花间集》到晏殊与欧阳修皆为代表;一种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柳永之后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属于这一类;苏东坡则“以横绝一代之才”“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弃疾与刘过属这一派,然“粗豪太甚”;姜夔、张炎等人“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其后吴文英、周密“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灵芬馆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