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摹仿论》中,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特别讨论了一个现象,就是欧洲文学创作中文体的雅俗混用问题;还有在这种混用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中的欧洲人所看到的現实是什么样的。所谓“雅”不仅是一种书面语的语体之雅,还意指着表现世界的主人公是英雄、国王、大臣、贵族、神职人员,以及这个由神的空间和人的空间共构的神圣化的世界。而所谓“俗”则意指着一个凡人的世界、俗人的世界、平民的世界。二者在文体上最鲜明的区别就是悲剧和喜剧的对峙。在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悲剧和喜剧一方面是文体论意义上的,另一方面更是风格和文化意义上的:悲剧的世界是神圣世界的形式,喜剧的世界则是凡尘世界的结构。二者一方面分野鲜明,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相混合,而这就形成了全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词“文体混用”。在对文体混用的叙述中,奥尔巴赫特别注意的是在雅的文体中,俗的文体是如何重新构建那个雅的世界的,其表现就是日常生活场景怎样成为神圣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让神圣世界获得了现实感、时间感、尘俗感。也是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奥尔巴赫将意大利诗人但丁作为全书的枢纽,因为正是“但丁的著作第一次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五光十色的人类现实的总体世界”。

但丁的《神曲》所记录的虽然是人在彼世世界的状态,但那个彼世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不变的。现实世界以各种方式介入到了这个彼世世界中,并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只有现实世界才会有的无数景象,并在这无数景象中发现了人之为人的情感和意志。奥尔巴赫特意引述了游历者但丁(不是创作《神曲》的诗人但丁)在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路过一条燃烧的敞棺夹持的道路时的叙述,这一场景出自《神曲·地狱篇》第十歌。维吉尔解释说,在这条路的两侧,棺椁中躺着的都是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而但丁可以和其中的两个人对话。也是在此,法利那太和加发尔甘底先后坐了起来,和但丁谈天。奥尔巴赫以为,这虽然是一个彼世场景,但无论是法利那太面对地狱时,脸上表现出的不屑而蔑视的神情,还是加发尔甘底听到自己儿子不幸遭遇时的忧伤和痛苦,都是高度世俗化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有的情感。这种世俗化的情绪描写,让一个丧失了时间的空间,恢复了时间的流动性,并让历史的延续成为可能。但丁在这个地方所书写的,绝不是超越凡尘的所谓英雄的颂歌,而是对虽然失去生命,却依然保留着生命意识的人的赞叹。法利那太面对但丁时先问但丁的祖先是谁,以此判断但丁是贵族还是平民;加发尔甘底在看到只有但丁和维吉尔时,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对自己生前未能更好地照顾儿子归多而产生的悔恨。奥尔巴赫由此认为,这种描写,这种对人的情感变化的描写,正是现实世界中才有的,并由此打破了地狱世界中的冰冷和严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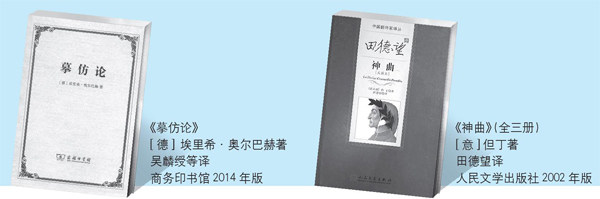
《神曲·地狱篇》第三歌开篇,诗人但丁就在地狱之门上写下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游历者但丁进入这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以直观的形象塑造一个个末日审判的场景,还要在这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中,塑造一切人的自我完成的样子。奥尔巴赫以为,“两个存身于棺材中的人的存在和此存在的场所虽然是终极的和永恒的,却不是非历史的”。打破这时空凝固性的,就是但丁对现实日常生活世界的把握;也恰恰是这种历史性,让处于绝境中的个体依然获得了鲜明的现实个性。“作为尘世事件标志的焦急和发展已不复存在,然而历史的浪涛依旧涌入彼世,一部分是对尘世往事的回忆,一部分是对尘世现时的关心,一部分是对尘世未来的忧虑。处处是作为形象保留在无时的永恒中的有时性。每个死者都将他在彼世的境地当作自己尘世剧的最后一幕,继续上演着的,时刻上演着的最后一幕。”可以说,诗人但丁借助游历者但丁之眼,将他所看到的彼世世界中的现实世界中的形象,刻印在纸页上,并打破了那句刻写在地狱之门上的箴言,让所有的死者再一次获得了生命。这也让《神曲》成为对人类事件进行大规模叙述的“大型史诗”。也因此,《神曲》虽名曰“神”之曲,但“神”只是终极的象征,“人”才是世界的主角。在彼世世界的悲剧中,时时呈现的是现实世界的喜剧。但丁没有像此前的那些作者,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那样,将一切现实世界的塑造都归为神圣世界的书写结果。但丁看到的是人的世界,并试图发现神的世界中所闪烁着的人的辉光。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赞叹但丁,说他是耸立在历史时间门槛上的诗人!
尽管文体混用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但能将这一混用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准的,即在日常场景的描述中见出神圣性的,但丁无疑是居功至伟。和但丁相比,写出《十日谈》的薄伽丘将文学俗的一面,即现实的一面、日常生活的一面、语言生活化的一面,发挥得更为出色,薄伽丘“越是成熟,市民性、人文性,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鲜明的通俗性就表现得越加强烈”。奥尔巴赫还认为,“没有《神曲》,《十日谈》永远也写不出来”。因为正是但丁在《神曲》中开创性地对现实世界的描写,使薄伽丘在一个宗教化的世界中书写尘俗凡事成为可能。可与但丁相比,薄伽丘一处理悲剧,就会显示出他苍白无力的一面;同时薄伽丘的写作缺少的是一种对悲剧问题,尤其是对道德问题思考的严肃性。这也构成了薄伽丘写作的致命伤。
奥尔巴赫认为,莎士比亚是沿着这条文体混用的道路继续写作的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但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却是有争议的。奥尔巴赫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莎士比亚不仅与平民的情感世界相距甚远,而且在他身上甚至看不到丝毫启蒙主义的先兆,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先兆,维护情感的先兆;在他那些几乎一直不署名的作品里,吹出的气息与德意志觉醒时期那些形象身上的大不相同,在后者身上,人们总能听见那个感受深刻、情感丰富的人的声音,他坐在一个老市民的斗室里,为自由和伟大而欢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