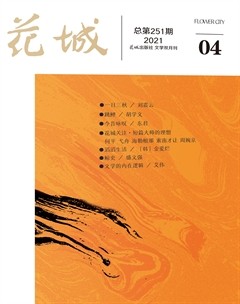十岁以前,我的时间都很富裕,包括五十七岁的外婆,六十六岁的爷爷,三十四岁的舅舅,我们都有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那是1999年11月的一天,爸爸终于也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只是一天的短假,也堪称生活或者命运的一次特赦了。在连续上了四十九个昼夜颠倒的班之后,该死的锅炉房终于顺利投产。爸爸半夜回来,没有惊动任何人。天亮以后,我和妈妈也没吵醒蒙头大睡的爸爸。浅灰色的被子从他的胸部到膝盖凹陷下去,在脚趾那儿再隆起,仿佛有个庞然大物,极其沉重地压在他身上,如果不是均匀的呼吸使胸膛起伏,我会觉得被子是裹尸布。知道裹尸布没什么稀奇的,我还知道众志成城、抗洪抢险、子宫、盆腔炎、肾亏、计划生育、紫荆花、石楠花等等。
爸爸睡到中午才起来,双眼充血,右手一直扶着腰,俨然肾亏病人在床沿坐了很久。妈妈出锅最后一道红烧带鱼,就坐餐桌边等爸爸。你爸可能还要再睡一会儿。妈妈语气中有不容置疑的忧伤,仿佛爸爸下班回家如战场凯旋。我不禁又想到裹尸布,爸爸睡得太死了。从卧室走进餐厅,睡意依然笼罩他,爸爸闭着也可能是半闭着双眼,往缓慢蠕动的双唇之间送饭送菜,然后缓慢地撇撇嘴,异常缓慢地吐出带鱼的刺。
爸爸没吃多少,走到阳光照着但依旧寒冷的阳台上,这才彻底清醒。他伸了个懒腰顺便扯了扯晾衣绳,又仔细观察了一番晾衣竿,上次加固的部分依然牢固,于是右手握杆,猛挥了几下。冷风受了劈砍,猎猎响。目光追随风声而去,宿舍楼与宿舍楼之间的那一小片天,烟蒙蒙、黄澄澄,像一张新鲜的捕蝇纸,挡住了爸爸的视线,而楼下的空地看上去像一个秃头那样闪闪发亮。他本能地转身背向光,这时看见了我,发现我一直在看他,于是又不自在地挥舞起晾衣杆,左手三下,右手三下,阳台就成了马戏团的简陋舞台。
昨晚,我和妈妈看了一场免费的马戏表演。傍晚,马戏演出的消息随一辆带喇叭的金杯车开进社区,并在社区里七弯八拐绕了半天而人尽皆知:晚上七点,琉璃路青年路交叉口,免费看马戏,免费看表演,猴子骑车、猴子画画,更有拇指姑娘现场演唱,精彩不容错过……我只期待拇指姑娘。毛发稀疏的瘦猴子骑着破破烂烂的独轮车一遍遍经过我的脚边,我只是觉得可怜。我边上一个小男孩说,外公还不如小猴。小男孩妈妈说,外公生病了,要躺床上静养。小男孩说,外公不如小猴,外公讲话都没人听,外公骑独轮车肯定也没人看。小男孩妈妈给了耍猴人五块钱的纸币,据我观察,那是当晚全场的最高纪录了。我抬头看妈妈,她和我一样,有些心不在焉。耍猴人过来时,妈妈往后退了一步,留我在原地把头低得低低的,偏偏瘦猴子骑过来龇牙咧嘴,严重破坏了我的忏悔。终于等到拇指姑娘,原来是一群侏儒。小男孩问他妈妈,为什么这些小学生看上去那么老、那么苦?小男孩妈妈似乎也吃不准,就望向我妈。我妈没说话。男女侏儒各握一个时不时漏出电流声的旧话筒,对唱了《知心爱人》。掌声寥寥。男侏儒就把他的搭档,那位在情歌对唱中几次破音的女侏儒拉回身边,拖长音叫了声“老婆”。女侏儒也拖长音应了一声“老公”,然后把大脑袋搁到对方的窄肩膀上。男侏儒面向全场恢复语调,不瞒大家说,我和老婆结婚五年了,再过两年就“七年之痒”了,可我这个宝贝老婆啊,还没结婚就开始痒了,结婚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今年第五年了,还是年年痒,去他妈的七年之痒。人群中的男人们笑出了声,我边上的小男孩被他妈拽走了。我妈向前一步,和我并排站。男侏儒从裤兜掏出一管尿黄色的浑浊液体,声称是哪里不舒服就抹哪里的独门药酒,哪里疼就抹哪里,哪里酸胀就抹哪里,哪里痒当然也一样,保管药到病除,全身舒泰。女侏儒在小丈夫的坏笑声中用一辆小推车推出一只密封的铁皮桶到场地中央,开盖,刺鼻的药酒味袭击全场,她双手抓出一团湿淋淋黑乎乎还带花纹的不明物。我堵住鼻孔慢慢看清那是一团经长时间浸泡变得软绵绵的蟒蛇。实打实看得见,我们的药酒绝对真材实料,用了我们的药酒,绝对男人女人都满意。男侏儒吆喝完,又绵绵地唤了一声“老婆”。手捧蟒蛇的女侏儒立即投怀送抱,一路滴滴答答,直到头碰头依偎在一起。从我的位置看过去,那条蟒蛇就像连接他们的脐带。
我问爸爸见没见过大蟒蛇。他疑惑地看了我一会儿,眼神迟钝,嘴巴微张,看样子再过几年就可以进社区老年大学了。于是我没提妈妈身体不舒服的事,我没告诉爸爸,昨晚的药酒十块钱一管,妈妈买了两管。爸爸慢吞吞地从阳台踱回屋里,突然一伸右臂,迅疾如十一月的北风,右掌啪一声扣住书架上的部分书脊。停在《海洋生物学辞典》上的苍蝇便逃不出爸爸干燥的手掌心了。还是家里暖和,冬天还有苍蝇。爸爸捂着苍蝇丢入水池,冲进下水道。接着就在水池边检查了一番,水龙头和水管都健康完好,滴水不漏。爷爷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小半年,虽然破裂的脑血管都补上了,但医师重点强调,出院后千万千万要特别小心。从此爷爷无缘烟酒麻将,在家如出家,如在动物园——动物园的铁笼里。奶奶每天准时准点投喂的三餐清淡饮食让口味重的爷爷生不如死,但谁也没把“不活啦”“活着没意思”之类的抗议当回事,就像没人会把一只充老虎的病猫当真。于是我问爸爸,爷爷怎么样了,还挑食吗?爸爸想了一下说,你想去看爷爷吗?我想了想,摇摇头,爷爷成天在床上,看见我也不说话。爸爸说,你爷爷不舒服,得静养。两年后,我得水痘,在家关了半月。每当黄昏像瘟疫般弥漫开来,窗外便响起同龄人活蹦乱跳的动静。我通过窗玻璃的反光瞥见了一个可怜而虚弱的家伙,除了嫉妒,还有恐慌,两年前爷爷对我的那种嫉妒与恐慌。疾病对健康,衰老对青春,我在爷爷面前有多生龙活虎,爷爷就相应地意识到自己有多无能为力,当我愉快地度日如年,爷爷只有苦熬。他肯定盘算过这是他倒数第几次和孙子见面,每一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因此必须用面无表情来掩盖那些汹涌澎湃的恨意妒意和那些恐慌无望。某种程度上,他的孙子无异于死神。
假如那天我赞成爸爸的提议,我们去看爷爷,或者说让爷爷看看我们,爸爸也许就不会无事生非,以检查的名义拧断淋浴的喷头了。喷头挂着一线铁锈水砸到卫生间的地瓷砖上,砸出一小块三角形的缺,也毁了妈妈浅浅的午睡。枕巾在她的半边脸上压出了一块印痕,她的眼睛,赤裸裸、水汪汪又可憐巴巴,仿佛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刺痛了,更刺痛她的无疑是赤裸裸、水汪汪又可怜巴巴的半截喷头,却让爸爸生动起来。现在他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早些年灯泡需要爸爸,五斗柜需要爸爸,锅碗瓢盆还有我都需要爸爸,直到进了锅炉厂,妈妈才逐渐接管了爸爸过去掌控的这一切。我去五金店一趟。爸爸用一张草纸将锈蚀的喷头包起来。不着急,妈妈说,夏天还远着呢。比喷头更早恶化的是家中热水器,再怎么加热也只能流出温水,秋冬两季我们全家都上锅炉厂的职工澡堂解决,因此只有夏天冲凉才需要喷头。妈妈赤裸裸、水汪汪又可怜巴巴的眼睛暗下去,声音干哑,夏天再说吧,我现在要睡觉了,我今天早上六点去菜场买带鱼,我现在只想睡一觉。于是爸爸轻拿轻放下喷头,轻手轻脚回到挨着阳台的书房,轻轻抽出《海洋生物学辞典》,翻开来。
爸爸一直对海很感兴趣,搜集过不少相关资料,包括小说,自己也写过一些诗,大海组诗、珊瑚颂什么的。但爷爷认为和文字打交道风险太大,宁愿爸爸去考电工证,天天带电作业也比舞文弄墨安全。爸爸的兴趣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天性就被抑制了,但又没到彻底扼杀的地步,可怜爸爸只好别别扭扭地见縫插针,利用零碎时间维护那部分不被承认的自己。而1999年11月这天,爸爸难得有了一个完整的下午,却坐立不安了,一会儿起身泡茶,一会儿去撒尿;一会儿翻翻电视报,一会儿去撒尿;一会儿抬头看看还有没有苍蝇,一会儿又去撒尿。我简直怀疑他的膀胱出毛病了。托电视广告的福,我很早就知道尿频尿急不是小事。我用妈妈教训我的那一套对付爸爸,专心一点,专注一点。爸爸这才老老实实坐下来,让膀胱好歹适应了下午两点钟的清闲,又开始抖腿,写字台跟着晃。他就在有规律的震动中进入了阔别已久的海洋世界。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物种消失了,有一些正在消失的路上。我坐在爸爸的斜对角看《电视报》,正圈出几部动画片的播放信息,爸爸突然伸过手来盖住报纸,好让我的眼神追随他略微泛白的唇,从天空到陆地,从陆地到海洋,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可能你这辈子永远不会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正在消失。我点点头。爸爸用食指点点自己又指了指我,我们也都会消失。我点点头,模仿语文老师的腔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爸爸纠正我,不是死,是消失,连鸿毛都没有。我想到陈列在教室后面的白鹭标本,残存的生命力集聚在羽毛上,集中在外表装饰上,内里除了一些木屑,空空荡荡,白鹭在制成标本时死了一次,如今标本残旧马上要沦为废品了,白鹭即将迎来第二次死亡,这是我当时心目中的“消失”,死两次,死透。爸爸说,世界上已经消失的人种,有苏美尔人、古埃及人、玛雅人,还有很多很多。他又拿了一本书,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句子:一个地球满载腐臭熏人的战争、伤痛与死亡,却仍不可理喻地轻巧旋转。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婺城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爸爸居然笑了,笑意把他的黑脸揉得更皱了。我乘机摊开《电视报》上的影讯,我们去看电影吧,看看他们拯救地球。
爸爸在卧室抽屉翻找锅炉厂发的电影票时又把妈妈吵醒了,妈妈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为什么这个时间爸爸会出现在卧室,她很紧张爸爸有没有请假,会不会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