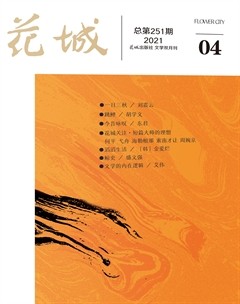索南才让,蒙古族,1985年出生于青海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学员。在《收获》《十月》《小说月报》《青年作家》《山花》《民族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政府文艺奖、2020年《收获》文学奖、第四届《红豆》“文学双年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野色失痕》《哈桑的岛屿》,小说集《巡山队》《荒原上》等。
玛曲才让从县上回来的那天晚上,民兵班长那日森在德州民兵微信群里面通知:明天早上,民兵集合去找人。要找的这人叫大成,是民兵更登加措的父亲。因为和妻子吵架,被这个儿子架在墙角抽了耳光,他羞愤欲绝,借酒消愁了一个星期,失踪了。他的小汽车停在乡上信用联社门口,最后一次有人在乡政府东南莲花湖方向的沙土路上见过他。所以他有可能进入沙窝了。当时他身穿黑色廉价人造皮衣,一顶儿子戴过的深蓝色棒球帽,一条牛仔裤,脚上是黑色旅游鞋。在他失踪之前,他给儿子发了二十几条微信语音,但除了前面寥寥三四条,余者含混不清,仿佛那时他已经陷入谵妄,胡言乱语 。前面几条语音里最重要的信息是他交代了财务状况。他有五十万的高利贷在三个村的五个人手里,他说了这些人的名字,但他没说利息是多少。他欠银行二十万贷款。早就有传言,大成拿银行的钱放高利贷,确实如此。
莲花湖在沙漠边缘,一块湿地,天鹅和鸟儿的天堂。他们在硬化路的尽头聚集。因为是要找一个大有可能已经死去的人,民兵们很有兴趣,快乐地分配了行动任务。十个人,十辆越野摩托车,好像要进行一场越野摩托车拉力赛。他们首先要进入沙窝,这里是尕海片区,重点搜寻“三个沙山”一带和铁路沿途的各个桥洞,由熟悉这里地形的巴尔绍乙带领六个民兵前去搜寻。而与“三个沙山”平行排列的“三个绿洲”一带,则有那日森、玛曲才让和更登加措,还有一个叫格东的少年四人前往搜寻。那片地区相比要小一些,那日森也很熟悉那里,因为他每年都会有两个月时间偷偷游牧在那里。他背着食物和被褥,跟随羊群在“三个绿洲”之间游牧。他狡猾得很,人人都知道他偷吃沙窝绿洲,却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他否认时理直气壮,说你们只是怀疑,而怀疑不是证据。
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寻找一个消失多日,很可能已经沦为野兽饱腹之物的小个子男人,无疑大海捞针。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志愿和心意。更登加措说,虽然我们十个人进入沙漠,就好像十个羊粪蛋蛋撒进大草山里,但我还是真谢谢你们!
这件事在他看来好像自欺欺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就是这样吗?这样的行动又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好像是最开心的人。玛曲才让认为,也许悲痛能使人释放快意,毕竟这两者像孪生出于同一个地方。
分工后六人的大队离开了,他们三个在等那个少年。玛曲才让将昨天去镇上时发生在车上的谈话描述了一遍。
玛曲才让有一套手艺,编织马具的技艺堪称一绝。他出手的马笼头、缰绳、肚带、鞍裘等,无一不是精品。他将这些东西放到镇上的民族手工艺产品专卖店里卖,只要他稳定出产,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为此他很踏实。他牢记一句俗语:一技在手,吃穿不愁。
昨天专卖店店主民华打电话:有一个人订了一套马具。你下来我们详谈。
玛曲才让骑着摩托车到公路边,在天然的停车场停好车,把车钥匙压在一块石头底下。然后他走上213号国道,等候一班小客车。他等车时候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创新的问题。事实是玛曲才让从来不缺乏创造力,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时常有一些新的元素加入,他认为自己不是匠人,而是一位艺术家。但这里的人,牧区,艺术的行为是有的,却没有艺术家的位置。艺术家就是牧人,或者一个酒鬼。玛曲才让不喝酒,得益于身体的反抗,他三十年来一直清醒着,或者说是孤独地醒着,牧人眼中的糊涂人。他坚持创作,把内心经营得充实自然,但这还不够,他需要更加细微的雕琢,局部的、细节的,感官的和精神的。而且人们喜好的变化很有分析的必要,也很有意思。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在马和马具这里分歧巨大,令人惊叹!他从这里找到一些为什么没有女人愿意当他老婆的原因——他过于强调一个男人和马的牢固而天然的关系,而将女性和马的关系比喻成猫和老鼠。这些话他说过,无形中肯定惹恼了一些女性,尤其是信息灵通的年轻女性。
但他是一名自命不凡的人,在没有遇到重大变故之前他维护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觉得这么说是瞧不起女性,而是很认真地认为,女性和马,还是存在一种无形的壁障。马天然拒绝女人的屁股,这是事实。
马具这一行本身的局限性控制他,如同套牢了马笼头,有一条看似松懈实则结实的缰绳拴住他。想要突破,难!对此他倒是不怕,反而激发了创作欲望。他进入实验阶段,又从具有想象力的牧人那里吸取点子,正如这次他要去见的那个客户,提出来的点子让他大受启发。这人居然想要把马辔子做成汽车的模样,而且这个“汽车”还要有银质的车标,车标他自己也设计好了,是一匹马奔跑的姿态。这一套马辔子上了马头,在视觉上会让马平白长一截,就好像人戴了一顶帽子,身高都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依然太过于保守,为什么马具就不能是惊世骇俗的,不能是颠覆常识的,甚至不能是疯狂的?而玛曲才让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要达到另外一种境界,他必须催眠自己,折磨自己,忘掉过去的模式和经验,忘掉马笼头、马镫、肚带,忘掉马鞍,忘掉马。
他招手拦一辆黑色小轿车。小客车晚点半个小时也没来,等于告知今日停班。小车停在他跟前,他没看见车牌号,但汽车的样子告诉了他这是谁。只有开黑车拉客的东珠加木措才有胆子将“穆勒——西海”的牌子竖在前挡风玻璃,堂而皇之地来回奔驶在公路上如入无人之境。他还没有驾照、没有任何有关的证件。但他一次也没有被抓住过,仿佛他和这辆破旧的黑色卡罗拉是一对幽灵。东珠加木措打开车窗打过招呼,他很有经验地安排后排的坐法。因为车里已经坐满了,玛曲才让必须加进去,挤出一个位置来。两个人的屁股和身子都要往前挪一挪,其中一个小姑娘,做得很輕松,另一个老一点的女人有些不高兴,说既然坐满了为什么还要停下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