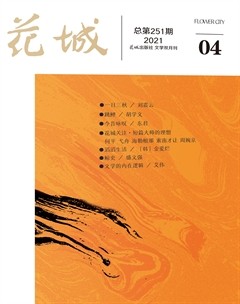在音乐学院,我最先学会的是弹“哆”。因为这是第一个音,更因为要用第一根手指弹。按下琴键,“哆”勉强发出“哆——”的音。为了记住刚才的“哆”,我又一次按下琴键。“哆”好像有些慌张地发出“哆”音,然后注视着自己的名字经过的轨迹。我坐在声音彻底消失之后的地方,挺直小指,僵住不动。午后的阳光透过绿色的玻璃窗贴膜,浑浊地照射进来。寂静流过钢琴和初次触摸钢琴的我之间。我像是吐出一个慎重挑选的单词,低声地喃喃自语。哆……
手放在键盘上的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老师让我放松,做出轻轻抓握的手形。当时我不相信在不用力的情况下可以抓握某件东西,也不相信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事。我从早到晚用两只手指练习“哆来——哆来”。同时按下低音和高音,低音持续更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钢琴的琴键形状都一模一样。颜色或黑或白,又有相同的尺寸和质感。我常常忘记“哆”的位置。这个不是“来”,是“哆”。这个不是“咪”,是“发”。触摸琴键之前我无法确信。我要找的“哆”位于从左侧边缘开始的第24个琴键。每当我在琴键上迷路时,我就从1数到24。这样就找到了“哆”,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再弹一下“哆”。我喜欢这个身躯庞大,性格内向的乐器发出的第一个声音,顽固而平静的“哆——”的震颤。庆幸的是,只要找到“哆”,弹“来”就容易多了。“来”就在“哆”旁边。“咪”在“来”旁边,“发”是“咪”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是找到“哆”。
练琴室的门上写着已故音乐家的名字。我坐在贝多芬室里练习“哆来——哆来”。我在李斯特室里弹奏“哆来来”,在亨德尔室里弹奏 “哆来咪发唆”。只用两根手指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用三根手指时扬扬得意地以为很简单。直到要用五根手指了,我才大呼太难了,学不会。我所在的小镇只有一家音乐学院。那里简单地教钢琴,教长笛,也教演讲。幸好没人报名学习小提琴或长笛。如果有人想学,院方首先就会劝阻。附近会拉小提琴的只有音乐学院院长的女儿。每当学校有才艺表演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身穿带翅膀的连衣裙弹奏连小学生都听不下去的小提琴曲。听着她蹩脚的演奏,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学院要教演讲。演讲又不是音乐。不过,好像也有人在这里学演讲。有的是即将参加演讲比赛的学生,有的是因为性格内向而被父母拉来学习的孩子。我在练琴房里享受第一个音干净消失的感觉,别处常常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贝多芬耳朵聋、听不见,我却第二次产生了打人的冲动。总之,这是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没有李斯特的李斯特室。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练琴累了的时候,我就描画各个声音的表情。“来”是眼角斜视,“唆”是踮起脚跟。“咪”擅长装糊涂,“发”比“唆”低,好像更快活。我渐渐适应了这五个音,也理解了钢琴不是键盘本身发声,而是通过“打击”内部的什么东西来制造声音。同时我也明白,越是高音消失得越快,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时间。不同的音符汇聚起来成为音乐,或许就是不同的时间相遇,从而导致某个事件的发生。
问题开始于“拉”。遇到“拉”之前,我就一直犯愁。五個手指弹奏五个音,这没有问题,也符合常识。当五个手指弹奏六个以上的音时,我就不知所措了,好像只懂五进制的文明人遇到了十二进制。我想遇到“拉”,却又觉得一旦和“拉”遭遇会有麻烦,所以我感到恐惧。我不喜欢困难,很多曲子就是用五声音阶谱成的。一辈子只弹五个音不行吗?学习“拉”那天,我屏住呼吸,注视着老师手上的动作。老师在我旁边弹了“哆”,和我弹的方式一样。老师弹了“来”,也和我一样。老师不出所料地弹了“咪”。我有些焦急。紧接着,老师弹下“发”的瞬间,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我的眼前。她没有用无名指弹奏,而是迅速把拇指移到“发”的位置,然后用第二根指弹了“唆”。其他的手指自然而然地触摸“拉”和“西”。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完整的七音阶。我看着老师手上的动作,感叹似的喃喃自语。现在,我似乎知道音乐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经营饺子馆的妈妈怎么会想到让我学钢琴。她不贪心,也不会强求什么。妈妈没有学问,常常对自己的教育选择没有信心。当时的妈妈是在追随某种“普通”的标准,就像去游乐园,去博览会,某个时期都流行着当时该做的事。回忆起来,小时候去博览会、去博物馆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送我参加博览会之后,妈妈会陪我去游乐园,这让我对妈妈心生感激。虽然这只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普通的童年程序,可是我会想起流露出无知的眼神,冲着时代潮流点头的妈妈,想起她带着包好的紫菜寿司踏上旅游车时疲惫的脸孔。偶尔我会想起我在旋转木马上面尖叫的时候,一手遮着脸躺在长椅上的妈妈。脱掉鞋子,小憩片刻的妈妈,她的面孔不正像“哆”一样低沉而宁静?我模仿妈妈的样子,躺在琴凳上。老师看着我,是不是像“拉”一样惊讶?那时我觉得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妈妈,请给我100块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坐在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里学音乐。妈妈像贝多芬一样披散着头发包饺子。恰好在那个时候,我们镇上开了家音乐学院,而妈妈的饺子生意也很红火。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学音乐。
妈妈给我买了钢琴。蓝色卡车从镇上掀起尘土飞驰而来,停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记得妈妈特别开心。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这让我莫名地以为我们家的生活质量顿时变得时尚起来。钢琴是用淡黄色的原木制成,看上去要比音乐学院的钢琴更好。原木上刻着优雅的藤蔓浮雕,金属踏板泛着淡淡的光泽,盖在键盘上的红色防尘罩的颜色又是那么煽情。单从色泽来说,就截然不同于我们家原有的家具了。唯一尴尬的是钢琴没有放在普通人家的客厅,而是放在饺子馆里。我们家的生活起居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这个房子在白天属于客人,晚上才是我们家人铺上被子睡觉。钢琴放在我和姐姐住的小房间里。大卧室对着厨房,小卧室对着大厅。
整个下午,我就待在店里弹钢琴。我踩着具有强音效果的右踏板,装模作样地弹奏《少女的祈祷》和《水边的阿狄丽娜》。蒸笼里呼呼冒着热气,商贩和农夫们穿着沾满泥土的长靴在大厅里吧唧吧唧吃饺子。在这样的空间里,我的演奏会让人在吃完饺子后哭着离开饺子馆;虽然简单又好听,其实很土气,所以有人从门前经过时,我会感到脸红。如果遇到直性子的人,可能会掀翻饺子盘,大喊:“够了!”有一次,我弹完钢琴,听到有人鼓掌。转头看去,只见大厅里有个白人男子拍着手大喊“Wonderful”。我和外国人之间流过尴尬的沉默。我很惭愧,却还是羞涩地说,Thank you……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纷飞舞,触摸键盘的手指下埋藏着白色的指纹。
我在学院里学习了大约两年。这期间我学完了两本《拜厄》,开始接触《车尔尼》和《哈农》。车尔尼,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从异国吹来的风,带给我不同于肥猪肉和甜萝卜的共鸣。与其说我想学车尔尼,不如说我想听到《车尔尼》这三个字。
生意结束后,妈妈躺在小卧室里听我弹钢琴。我跟随妈妈用脚打的拍子演奏《朱鹮》和《思念哥哥》。妈妈的脚在半空里打着拍子,袜子前尖浸透了洗碗水。那只脚就像妈妈飘浮在半空的内心一角。爸爸更擅长唱歌,然而想听我弹琴的常常是妈妈。爸爸负责送外卖。他把烤水饺、蒸饺和水饺送到小镇各处,经常多管闲事,开些无趣的玩笑。那时店里特别忙,可是经常找不到爸爸的人影,要么是送完外賣顺便跟人赌起了钱,要么就是在小商店门前玩娃娃机。有一次,爸爸整整一天没来饺子馆,妈妈为此大发雷霆。外卖订单全部取消。妈妈在蒸笼和电话间不停地穿梭。日落时分,爸爸悄悄打开店门,走到大厅,因为打不开卧室门而来回踱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喊出正在小卧室玩耍的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难得见到爸爸这么温柔,我们都很开心,乖乖地从小卧室里爬出来。爸爸把推拉门打开一半,开始唱歌。爸爸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爸爸低沉的嗓音在傍晚的小镇上空回荡。“故乡有多远,蔚蓝的天空,可是同一片天……”奇怪啊!爸爸的故乡明明就是这里,可是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凄凉,仿佛他还有另一个故乡。“白色洋槐花在风中飞舞……”三个探出门外的脑袋唱着同样的歌曲,卧室里阒寂无声。也许妈妈在想,早在很久以前,从她喜欢上这个歌声动听的男人时,她的不幸就开始了。
当时我九岁,弹琴的时间不如捣乱的时间多。每次听到玻璃哗啦啦破碎的声音或者姐姐的尖叫声,妈妈都会放下手中的饺子皮,飞快地跑过来揍我们一顿,再箭一般冲出去蒸饺子。妈妈总是很忙。孩子要快快地打,快快地长大,饺子要更快地蒸熟。妈妈的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的时候,面粉扑簌簌地飞溅到四面八方。虽说我懂点儿音乐,可是面对毒打,我仍然只是张大嘴巴,发出“呜呜”的哭声。有一次谱架断了,便代替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稍微长大些之后,我不再“呜呜”地哭,而是“嘤嘤”啜泣。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乐器好可怕。
音乐学院有很多钢琴弹得好的孩子,不过弹得不好的孩子更多。没有定期调音的钢琴全都患上了鼻窦炎。相框里的贝多芬和莫扎特坐在小学生们制造出的噪声中间,流露出无比厌倦的神情。孩子们懒懒散散,老师也是例行公事,我却觉得学钢琴很有意思。指关节下冒出的声音律动令人愉悦,内心深处荡漾着某种情感,促使我心生思念。这种感觉我也很喜欢。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要把钢琴弹“好”的念头。我只想适当地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