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译完《苦闷的象征》半个月后,鲁迅又购买了厨川白村另两部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第二年一月即开始翻译《出了象牙之塔》。虽未译《走向十字街头》,但在《出了象牙之塔》的译后记里,谈到走出了象牙之塔以后又将如何时,他全文译介了厨川在《走向十字街头》序文中对此所作的描述: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彷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暂时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骚扰之巷里,来一说意所欲言的事罢。用了这寓意,便题这漫笔以十字街头的字样。
作为人类的生活与艺术,这是迄今的两条路。我站在两路相会而成为一个广场的点上,试来一思索,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如摩理思,则就照字面地走到街头发议论。有人说,现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没有碰壁,不过立在十字街头罢了,道路是多着。
年逾四十的厨川,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虽有所迷惑,但他显然是赞同英国那些怀着社会改造理想,走到十字街头发议论的文明批评家所做的选择的。鲁迅也已跨过四十岁这道人生门槛,步入了中年;五四退潮后他陷入“荷戟独彷徨”之境,正在寻找一条可走之路,厨川这些话想必会在他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其“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写《这个与那个》中的这段文字,尽管意思不同于厨川,但二者间的关系还是隐约可见的。

自从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以后,鲁迅一直在“寻路”,在探求摸索一条自己可以走、能够走,也应当走的道路。而他这一时期的文章里,关于“路”“道路”,关于“走路”“寻路”,关于“活在人间”,以及“如何走人生的长途”之类的表述和意象颇多,恐怕绝非偶然。
鲁迅曾经对朋友表示,其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而《野草》里唯一一部短诗剧《过客》,据说他在脑子里酝酿了将近十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表现形式,一直迁延着没有动笔;尽管最后写出来了,但并不十分满意。可见“走路”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鲁迅,久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旨在表现自己独特生命哲学的《过客》,他是格外看重的。
诗剧的主角,黄昏时分仍在踉跄赶路的“过客”,酷肖鲁迅。这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显然是作者自况性的形象,而又明显具有深邃婉曲的象征意味。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自有记忆起就只一个人这么走。作为一个“独行者”,他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只知道要走到前面的一個地方去。
过客已走了太多的路,脚早已经走破,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血不够了,需要喝些血,但不知道血在哪里;只好靠喝水,来做些补充。他喝下了小女孩捧来的一木杯水,但却谢绝了她又递上让他裹伤的一片布,担心这“太好”的“最上”的“布施”,会影响自己义无反顾的“前行”。
这个独自寻路前行的人,不会在中途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名副其实“过客”而已。他的使命,只是听着一个声音的召唤,在“似路非路”的荒野往前“走”。他“息不下”,“只得走”。“走”几乎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宿命,亦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谓“良心命令我去做的特定行动”。他并不介意也不确知“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不管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抑或坟地(按:即生命终点,亦为死亡的隐喻),或者坟地之后还有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这么不停地往前面、朝远方,一直走下去……
过客的生命意义,自然并非用前边那个终点就能够标示与衡定。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走”的行动当中,在“走”的过程之中。西哲有所谓“向死而生”之说。鲁迅的过客,大概会让人想起那个来自西土的反复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但恐怕是更近于他笔下在淡漠的悲哀和淡红色的血色中“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的。显然,对于鲁迅来说,“走”就是他的“行动”,就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在伪自由、无自由的现实世界中,他由此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希望和绝望皆为虚妄,那么鲁迅便不再纠葛于这两者之孰有孰无,那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他最看重的,就唯有“行动”,唯有“走”,唯有“向前进取”,“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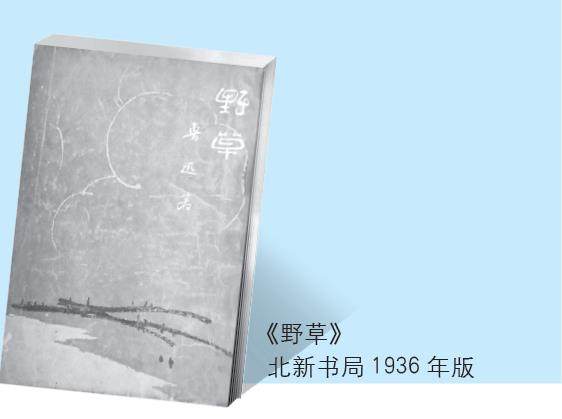
鲁迅的自由,不过选择的自由、“走路的自由”而已。“走”即“行动”,即鲁迅的人生实践、存在意义和自由意志,即他的“与黑暗捣乱”“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与哲学家罗素所说的耽于幻想的“感情哲学”,或沉溺于大体系建构的“理论哲学”均迥然不同;鲁迅这一独特的哲学,无疑属于“把行动看成最高的善”的“实践哲学”。走,也是反复出现在《呐喊》《彷徨》中的多篇小说,以及《野草》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他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时,署名“迅行”“令飞”,是“取前进”之意。而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第一次署名“鲁迅”,则是“承迅行”而来。减去“行”字,加以“鲁”作姓,因为母亲姓鲁,“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平常鲁迅出门、走路也大都是这个样子,“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他一生都在行动,都在抗争,都在路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下来。作为孤独的精神战士,鲁迅在五四落潮后的生存形态、写作方式和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则是直接得益于厨川白村的启发、示范和引导的。

二
在《出了象牙之塔》的译后记里,鲁迅引述了厨川对于出了象牙之塔又将如何的看法后,又接着发议论道:造化所赋予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与经历相伴,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彷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