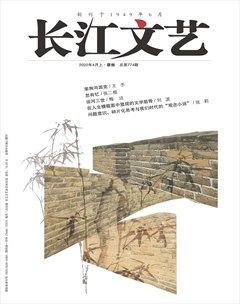一
狂风刮了好几天,我在布日古德山脚的毡房内盘算着日子,最严酷的西伯利亚寒流就要来了,西日嘎草原将遭受一场惨烈的白灾。天灰蒙蒙的。马棚里的三十匹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来临,躁动不安地踢腾着四蹄,发出刺耳的嘶鸣。我骑上黄骠马,领着黑狗在无垠的牧场上打转。马群的主人乌雅泰去了很远的地方,临走前交代,一定要让马群安全地度过冬季。之前我是西日嘎村的牧马人。每年春夏,村民们将家里为数不多的马匹合在一起,让我一个人放牧。他们把更多的心思和经历放在羊群。唯有乌雅泰一人,只养马不养其他牲畜。去年冬季他的马群损失了一半。今年秋季,他走进我的毡房说,我的安达,帮我照料马群。我理解他的苦衷,更心疼他的马群,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何况他这趟出远门,明年春季才能回来。
乌雅泰是骑着白马走的。他没有狗。黄骠马和黑狗是我多年的两个安达。我从十八岁牧马,至今已孤身一人生活了三十年。在一座遥远的山脚,埋葬着我阿爸额吉的尸骨,埋葬着两匹黄骠马和两只黑狗的尸骨。三十年来,我没有在冬季照料过畜群。每当严酷的冬季来临,除了喂饱黄骠马和黑狗以外,我躲在西日嘎村的土房里,等待暖春的到来。我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那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在河边牧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流浪的汉子。他要去北方寻找家人。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脸上却有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他向我讨要食物的样子,更像是在下达命令。我给了他风干肉、奶豆腐和烈酒。汉子吃饱喝足便走到河边,说要给我回报。他双手叉腰,像岩石一样站在河边,对着遥远的方向发出奇怪的声音,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不像是人体能发出的声音,可那声音的确是从他口内发出的。
汉子的声音像河水一样绵绵不绝,不知他从哪里涌动出这样的气息。他的声音时而低沉哀婉,像古老的潮尔琴声,时而苍劲高亮,像鹰唳长空。我惊愕地问他,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这叫什么哆,你是怎么发出来的?他嘿嘿笑着说,这叫浩林潮尔,气息通过闭气的方式猛烈撞击声带产生低音,通过口腔共鸣产生高音。你学会以后,可以教给更多的牧民唱。他说完再次给我做了示范。当我想继续询问时,他朝着遥远的方向走了。浩林潮尔的声音回荡在他身后,他逐渐消失在茫茫的草原。那些天,我一直用心学着他的样子唱,偶尔能发出有那么一点类似低音的声音。我抓住这仅有的相似音,在漫长的夏季和短暂的秋季反复进行练习,却始终不得要领。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冬季的第一场雪下来了。我牵着黄骠马,领着黑狗穿过雪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远远看到,几块颜色模糊的东西在雪野深处站立不動。走近发现,那是几匹像一块块刚硬的石头一样的野马。它们身上结满冰碴子,睁着眼睛冻死在荒野。它们冻死也要站着。如此惨烈,如此悲壮。我的心像是被雷击中,瞬间震撼了。黄骠马悲鸣,黑狗大声狂吠。就在刹那间,我身体里燃烧一团烈火。我竟然发出了浩林潮尔。
乌雅泰走的方向有些模糊,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我每天在牧场上消磨时间。我能与村民融在一起,也能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当我一个人时,不会感到寂寞,甚至会享受独有的快乐。我喜欢炭火的味道,喜欢每天起身走出毡房,看辽远的天际,呼吸新鲜的氧气。我喜欢用收音机听乌力格尔,喜欢与我的黄骠马和黑狗在草原上结伴而行。我习惯这一切。多年前,城里的姑姑想把我安置在城市,想在企业给我找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进城,身体和精神总是很容易紧张。并不是城市不好,而是我无法适应。姑姑看我可怜,就没有勉强我留下。回到西日嘎村,我顾不上喝奶茶,赶紧去看寄养在牧民家的黄骠马和黑狗,似乎没有什么比它们更亲切的了。时光匆匆,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决然不能改变。没有什么能撼动我的心了。我踏踏实实地当起了牧马人。
二
天阴沉沉的,雪花慢慢飘落下来。常年牧马的经历,使我能像马一样嗅到危险。某种可怕的气息逐渐逼近,我惶恐不安。喂饱马匹后,我认真观察马棚的每一个细节,发现稍有松散的地方,立刻用铁钉铁线进行加固。安静的夜里,黑狗在炭火旁蜷缩着身体,我盖上厚厚的棉被闭上了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黑狗哼哼叫着,我从睡梦中醒来。毡房外面刮起了强风,风声大得惊人,像一群猛兽正在经过牧场。天色渐亮,我起身重新生一堆炭火,穿上厚衣服走出毡房,强劲的风差点把我刮倒。西伯利亚的寒流来得无比凶猛。雪已有半米深,我拿着铁铲艰难地走进马棚。三十匹马挤在一起取暖。我的黄骠马拴在另一个角落。马棚顶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我一铲一铲地将雪清理干净,还在马棚和毡房之间铲出了一条路。风停了。做完这些,我疲惫地走进毡房,瘫倒在炭火边。
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下雪,牧场呈现出斑驳的景象。我经常从午后睡到半夜。一个后半夜,我被持续不断的噼啪声惊醒。我快速跑出毡房查看情况。马棚顶塌了好几处,马匹乱作一团。寒风再次袭来。我戴上手套和绒帽,绑紧腰带,迅速进入战斗。完全受惊的马群正试图跳出马棚。突然啪一声巨响,马棚的墙也塌了,有几匹马从缺口纵身一跃,逃入迷茫的夜色。接着整个马群陆续逃走。唯有我的黄骠马表现冷静,尽管还在拴着缰绳,却没有过多地挣扎。它在等待着我。三十匹马很快跟着风跑了。我曾经没有遇到过这样紧急的情况,但是听老一辈牧人讲,马群顺风跑就不会停下来,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局面,就要紧随其后,直到风速降下来再把马群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