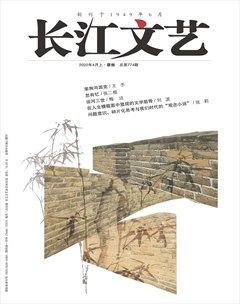一头小鹿爬上厅堂的饭桌,啃香蕉吃,被午睡起床的明启看见了。他刚踏出厢房门,见小鹿嘴巴里塞着香蕉,吃得津津有味。小鹿见了人,迟疑了一下,继续啃,一节香蕉啃完了,又咬了一根香蕉。明启走到桌边,伸出手,想摸摸小鹿的下巴,小鹿跳下凳子,惊慌地往屋外的山林跑去。
明启是河南信阳人,来雁坞生活有三年多了。他是一个久病的人。在雁坞生活的七个人,都是久病的人。至于谁得了什么病,只有自己清楚,甚至自己也不清楚。病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没办法诠释。
两条自北向南斜缓下去的山梁,夹出了一个狭长的山坞。某一年,大雁向南迁徙,嘎嘎嘎的雁声如暴雨飘落山谷。有一只大雁因翅膀被风所伤,而暂落于谷中山塘,长鸣三日,它的伴侣返身伴游,成双成对戏水觅食,繁衍生息。山坞因此得名雁坞。雁坞有人烟七户,山田数十亩。1998年,雁坞人外迁至四华里外的公路边,山田荒落,芒草丛生,瓦房破败。2007年,主持兴修太平圣寺的妇人徐氏,见雁坞瓦房和田产败落,从山民手中流转过来,对民房着手修缮,在网上招收生态养生者,入居时间不低于一年,免费提供屋舍、山田。第一年来了两人,第二年来了五人。
雁坞远离集市和公路,无商店无诊所,通电通网络,通土公路。这里树木茂密,饮水洁净,适合养病。来的七人都是久病的中壮年人,三男四女,各居一栋瓦房。他们来自湖北、河南、山东、吉林。有的人住了两年,返乡了,空出的瓦房又来了养生者。有的人一直住在雁坞,过年也不回去。养生者欲入居逾百,在排着队,等待有屋子空出来。胡氏又把坳头村的十几栋瓦房流转过来,修缮,供外人使用。
太平圣寺与雁坞、坳头,呈三角之势,有土公路互联,即使是步行,也仅需一刻钟。养生者自己种水稻种菜种黄豆,自己榨油,自己酿酒制豆醬,自己养猪养鸡鸭。他们与外界没有交往,甚至与家人都很少交流。明启第一个入居雁坞。
山坞野猪多,他是常见的。他见过大野猪带着七八头小野猪在翻藕吃。大野猪跳下烂田,嘴巴拱烂泥,拱出鲜嫩的白藕,唝着吃。他吓坏了,他爬上田埂往屋里跑。有一次,他把番薯堆在养猪的茅棚里,野猪也去吃。他拿着棍子,想打野猪。野猪扇了扇大肥耳,向他 ■,哄哄哄地叫。他撒腿跑进屋里。可他没见过小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这种名为黄麂的小鹿。
有一次,一个来山里挖草药的人,有七十来岁了,在明启家搭膳午饭。挖药人对明启说:村里有人藏了黄麂骨吗?我收黄麂骨。
“黄麂?我没听说过,见了也不知道。长得啥样子?”明启有些疑惑。
“南方小鹿的一种,皮毛红棕,雄麂长两枝小鹿角,雌麂不长鹿角。这一带,黄麂很多,叫声像狗又像鸭。黄麂因此也叫吠鹿。”
“黄麂骨很值钱吗?”
“黄麂骨磨粉,给孩子吃,孩子长得高。”
“人只有一条命,黄麂也只有一条命,动物不能随便杀害。我是一个不敢杀鸡杀鱼的人,何况屋后就是太平圣寺,菩萨在看着呢。”明启说。
挖药人每年来山中两次,每次都在他家搭膳。他见了小鹿后的一个月,挖药人又来了。他对挖药人说:黄麂来了我厅堂,很友善,吃了好几根香蕉。
挖药人说:黄麂乱闯进了屋子是有的,可进屋子吃东西,还是第一次听说。
明启说:说来奇怪,黄麂跑出屋子,还回头两次看我,我当时很激动。可这一个来月了,它再也不来了。
“这是莫大的缘分。兴许才开始了缘起。后面的事谁说得清呢?”挖药人说。
半年过去了,黄麂还没出现过。在夜深时,明启经常听到山边有“喔喔喔”的叫声,像狗叫又像鸭叫。嗯。这是黄麂在叫。叫声离村子很近。有时候,这几天在东边山窝叫,过几天在西边山窝叫。叫声绵柔,节奏短促。他站在屋前院子看着山窝。他用手电照一下山窝,叫声便停歇了。明启想,黄麂真是既敏感又聪明的动物。
山塘下有一块沙地,明启在沙地种上了花生。山坞所种植的农作物,都是他们自己育种。花生是土花生。九月,收花生了。他收了满满一箩筐。夜里,他听到窗外有啃花生的声音。箩筐加了竹编盖子盖着,老鼠爬不进去,那会是什么动物在偷吃呢?他披衣起床,灯亮开,啃花生的声音没了。他站了一会儿,又没听到什么响动。他又睡下去。第二天起床,他发现箩筐盖被翻落了,花生少了,地上又没花生壳,抖落的花生泥倒有不少。
花生撒在两张大圆匾上,晒在屋顶。花生晒上八天,水分便抽干了。早上端上去,晚上收下来,搁在两条长板凳上过夜。有一天深夜,他听到了有人在推自己的门,门闩在咯吱咯吱作响,但门始终没推开。生活在雁坞的七个人,晚上八点以后,便无人亮灯了。早睡早起,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他们信奉的修养信念之一。他问了一声:谁找我啊,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无人应答。推门声也没了。他侧耳听,也没听出其他动静。是不是自己有幻觉呢?有一阵子,他经常产生幻觉,老觉得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一个鬼影也没有。他还听到了他前妻对他说:天冷了,记得加衣服。他患病第三年,他前妻和他办了离婚,已十余年了。他以前是个油漆匠,做了二十多年的油漆。他脸黄黄的,有些肿胀。他去了很多上海、北京的医院,都查不出病因。医生说,查不出病因的病最可怕,胆红素代谢出现了问题是肯定的,为什么会有代谢障碍,不得而知。他服用降胆红素的药,服用了一年多,也没什么效果。他停止了服用。哪有那么多钱呢?天下雪了,他偎在火桶边烤火,他前妻对他说:我没能力照顾你啊,你也没能力照顾我和孩子,你在外面,记得天冷多加衣。他四顾惘然,屋子别无他人,他流下了滚热的泪水。
是谁推门呢?他端着早粥,去串门,问了其他养生者,都说昨夜早睡了,没推门,推门得先喊名字啊,不然还以为来窃贼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山光水净的地方,没一件值钱的东西,谁会来盗窃?明启这样想。
又过了两天,夜里又有了推门声。他轻手轻脚开了后门,拿着一根铁条,贴墙边走往大门。他挨着墙角,看见一头没长鹿角的黄麂用头顶木门,门轴咿呀咿呀,门闩咯吱咯吱。他无声地发笑。
黄麂爱吃花生。明启夜里不闩门了,虚掩着。他撒了一斤多花生在厅堂,等黄麂来吃。他开了厢房的门,靠在床头打瞌睡。等了三个晚上,黄麂也没来。
一日清晨,明启去山边的菜地拔青豆。他种了三块地的大豆。青豆完全饱满了,拔3株,可以剥一碗,切青椒小炒,是他百吃不厌的。他坐在厅堂剥,凳子上摆一个碗,低着头,指甲剜开豆荚剥,豆子青青,水色充沛。他还没走到地头,看见豆秆在动。豆秆摇动得厉害,他捡了一个石块扔过去,一头棕黄的黄麂惊慌地抬起头,见了人,它一跃一跃地跑走了。他察看了一下,有一垄豆子被黄麂踩倒了,有十几株豆子被吃得精光,叶子也吃了。
前些时候,他就发现有豆子被吃了。兔子和松鼠也吃豆子,但不吃豆叶。他还以为是獾吃了的。黄麂还真贪吃。他砍了桂竹,编了两米高的竹篱笆,围了豆子地。
拔豆子了,他多拔3株,放在门口过夜。放了两次,豆子被吃了,啃了一地的豆壳,叶子也没吃。这是老鼠吃的。他便把豆秆用一个麻线捆起来,挂在晾衣杆上。挂了几次,黄麂也没吃。
春节了,屋主来看自己的老房子,提了3斤香蕉、3斤脐橙当伴手礼。屋主七十来岁,随儿子生活在上饶市。屋主是个质朴厚道的人,每年春节都要来看看明启,说:我这个老房子多亏了你照料,房子三年不住人,便破败了。老房子还在,我也有了念想,外面再好,都不如一栋老房子好。
明启陪着屋主在四周山边走走。雁坞有一条直通山外的石头铺的山道,因多年没有走,芒草丛生,灌木比人高。屋主走着山道,又说:世世代代走的路长满了草,心里荒凉,心里也幽静。他说起年轻时挑木柴去山外卖,卖了钱,买农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