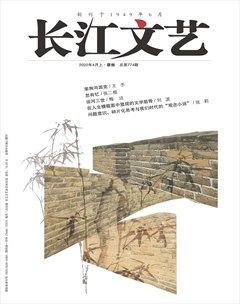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阳刚之气”,是生活经历的不自觉流露
吴佳燕(以下简称“吴”):王手老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您聊聊。我这次集中读了您的中短篇小说,读着读着常常会忍俊不禁。您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的熟稔了解,那种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潜藏的幽默、机锋与人性的微妙之处,让人会心一笑又有所击中。我想您的小说应该是追求通俗好看的,真正地面向大众深入生活,有某种“平民文学”的意味。“好看”也越来越成为当下写作的某种趋势:既要考虑到外部读屏时代阅读的耐心,更来自纯文学圈子内部的突围冲动。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好看”的?
王手(以下简称“王”):谢谢佳燕,这么短的时间里阅读我这么多小说是很辛苦的,也感谢《长江文艺》给我这样一次对话的机会。我想,每一个作者都是乐意做对话的,因为对话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而作者也可以借助于对话传递一些小说里不能完成的意味。我1973年初中毕业即走上了社会,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混了十年,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十年,人们马上会想,这十年里你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之后我又在一个相对正规的厂里待了十年,这十年我也是自由散漫的,有时候在三班倒地上班,有时候去一个杂志社里打杂,有时候也没有负担地跑跑社会。后来,在我快到四十岁时去了文联,才算真正地安下心来。前面的二十年,我等于就是在社会的底层,这种情况下,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怎样和人接触,怎样保护自己,怎样让自己生存得活泛一点。也因此,底层的人等、生活、艰辛、快活,我是很熟悉的。如果说我的小说写得平实通俗,我想这可能和我的先天“基因”有关,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写出深奥冷僻的小说来。“

平民文学”不可怕,平民文学应该也算是一种品质,但平民文学一定要鲜活,要有血有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说不是学说,它是以故事为基础,既然是写故事,那就一定要寫得好看,这应该也是每个作者的追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小说好读,好读和好看还是有区别的:好读一般是指读得顺畅,读得舒服,不涩口,没有疙里疙瘩;好看就不一样,好看就是看热闹,看稀奇,看西洋景,那是有内容指向的。多年前,有一次和何平老师聊天,他也说到我小说的特点,我记得他当时还说了一个词,说你的小说里有另类的生活。另类就是不一样呗,我暗暗高兴。
吴:关于写作的地域性,对于您而言其实就指温州。我觉得温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但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当代作家。您说“写小说靠的就是生活”,您的创作一方面与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其他温州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您是讲究某种“文武之道”的。听说您个人非常热爱运动,您的小说无论题材还是写法也都具有某种阳刚之气,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您写温州人的各种工厂生活和做生意的经历,还涉及生活与运动、文学与体育等方面,这在相对自我或阴柔的文学氛围中简直是一股清流,也与当下普遍的宅生存、宅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还让我想到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一个目光深邃、身体硬朗的健美男子图片,忍不住想问是不是带有某种自况的意思?可否谈谈温州对您写作上的滋养?
王:温州有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小、方便、自由度高、没那么多规章,很适合我这样的人生活。温州人有一种散淡、无所谓的秉性,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比如排队,他不会老实地走在队伍里,而是在边上跟着队伍走,要是有人以为这位置是空的,想占据它,他会说,这是我的,我早就在这里了。我也喜欢这样,或者说我也正式不到哪里去。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局限于做一件事,千方百计地想再做一件事。我在温州就做过很多事,我可以有固定的工作,但我不安于现状,东做西做,乐此不疲。有一次在温州大学和喜欢写作的同学们交流,我说的题目是:人人都可以写小说,但前提是你要有生活,要有见识,要有阅历。我列举了我像他们这个年龄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打群架、调解纠纷、管理一个工厂、上街看武斗枪战、去海上买走私货、到上海贩紧俏物品等等。我发现同学们的眼里一片茫然,他们不知我所云,他们太顺境了,太平淡了,太幸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里多少有那么点社会习气、有那么点江湖意味的原因。温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个,好友东君在一次对话里讲了很多,也讲得很好。温州也有许多不错的小说家,我有幸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有的有很大的阅读量,有的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两项我都比较弱,比不上。不适合我读的书我不会去硬读,没有生活的想象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只写我熟悉的,我经历过的,或者我知道的而且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样才不至于迷失逻辑,才不会太离谱。我听说有评论家议论,说我的小说看不出学过什么,看不出什么出处,我觉得这就对了,这样挺好。至于你说的“文武之道”“阳刚之气”,我想,这也许是有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吧。我原来用QQ时,“头像”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头人,我的签名是“我是温州的土著”,这是想亮明我的出身。现在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外国的健美老头,肌肉不大,但线条很好,这是我心向往之的,但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吴:小说创作中方言的运用既可以增加小说的特色,又要注意不影响阅读,如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流》都用到很多本土方言。您在小说中用到的温州方言并不多,但是一些方言俚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让不懂温州话的读者也能大致揣摩出它的意思,如“老司”是“老师傅”的意思,“浙江省”被化用成了“浙江最省”,还有“塌了神气”“像虱子烫了一样舒服”“叫我吃我也不敢夹”等等,而“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直接被您用作小说的题目。这些方言口语带有浓烈的大众生活气息,生动传神而接地气,不经意间形成了您小说的某种叙述风格,又通俗又有趣又形象,以至于东君说您写完一篇小说都要用温州方言念一遍。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小说创作中方言的选择和运用的?
王:一般来讲,我在短篇里尝试运用方言会相对多一些,像金宇澄老师的长篇《繁花》,方言运用得这么彻底,这么成功,且被人津津乐道是不多见的。不过,上海的方言基本上還算好懂的,它的腔调很有特色。林白老师的《北流》我还没有读到,不好意思。温州的方言是极其难懂的,也是极难呈现的,它虽然生发在浙江,又和福建比邻,却和他们完全不搭界,自成一体。文学前辈林斤澜先生是温州市区人,他一直致力于在小说里运用温州方言,但也仅仅是一些词语的运用,叙述和对话呈现温州味道的也很少,而效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怪味”“生涩”。作为一种文本研究,他的小说在这方面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因为出身在温州的大杂院,青年时期又长期在底层劳作生活,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平民语言、民间语言,这也是我在温州的标识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地方上的会议,不讲温州话几乎不会发言。现在我在地方上做一些分享会什么的,经常也是“温普”和“温方”交替使用。我发现,出彩的地方、引来大家会心一笑的地方,往往是温州话里的形象比喻。但我没有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我怕外地的读者不接受我,只是偶尔用一下一些意义可以共通的俚语;而在叙述和对话上,我常常运用的也是温州民间的讲话习惯、民间句式以及一些底层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