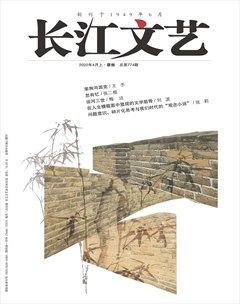淡豹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名为“美满”,但《美满》中的故事无一美满,甚至或多或少地出发于、停泊于“伤逝”。
《美满》中收有九个短篇,主要讲述了三种故事:《女儿》《养生》《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与《旅行家》是“那两个人”作为“一对人”与“两个人”,在不同生命时刻的遭际。四篇似从不同面向重述同一个人、同一对人在不同时刻的处境,他们以恋人、友人、家人、故人的身份时而重返共同的生命段落,交集片刻成为他们后来人生的一种底色;《山河》《过火》与《父母》有清晰的故事背景,讲述家庭内部冰山的生长与沉没,以“母”与“女”、“女”与“缺失的父”、“父”与“子”、“母”与“缺失的子”所触发的生活为起点,单亲家庭、失独家庭以及恐惧失去孩子的家庭内部的幽微、隐秘的紧张被觉察;《乱世佳人》与《海和海绵体》是关于人之晚景的呈现,前者从“李太太”的回忆进入,后者从“教授”生命最后一程着手,叙写丈夫的不忠与婚姻内部漫长的沉默之战如何以丈夫的死亡告一段落。九种日常几无惊涛骇浪的部分。或者有,但故事开始时浪的尾声已趋平息。作者似乎对叙事动力中的“戏剧性”怀有警惕,九个故事在不断回到日常本身的音量与音色,“故事”的进程因而如白噪音般弥漫而不觉。
淡豹曾有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学术训练与媒体从业经历,她的生活半径从小说落款地点约可见出。专业的学科训练与以文字为业塑造着她的思辨方式;游走世界,《美满》的锚却一再抛向家庭生活、日常磨损这片岸的边缘。《美满》落笔的人,正在溺水,不觉或已习惯。他们呓语、梦游、挣扎或不再挣扎,他们在与水形成新的关系。简要勾勒故事轮廓,不足以说明《美满》到底是怎样一部小说集,因为它本质上消解着对故事的讲述。
被略去名字的人
《美满》中九个短篇的主要人物几无外貌刻画,甚至连名字也被有意无意地抹去了。或是使用叙事人称的习惯,或是有意编织的散点化,作者不以面目,而以心智的行动轨迹与方式定义人物。文本中多以第三人称、第一人称以及某个社会身份指代人物,取消了“名字”作为过渡:“她”和“他”(《女儿》),“我”(《养生》《旅行家》),“父亲”、“爸爸”、“妈妈”(《山河》《父母》)穿行通篇;或是以身体的某部分特征完成命名,如“跛脚良”(《过火》);更具体一点的,是“李先生”、“李太太”和“小李”(《乱世佳人》),是“教授”和“妻子”(《海和海绵体》),是“W”与“数学家”(《旅行家》)。
这一定不是巧合。在《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中,开篇头一句,是“一个叫家莉,一个叫家明吧”,这样“随意”地分配两个名字给人物,后文又以“她”和“他”来指代两位了。《美满》中拥有名字的人物是少数,且往往是叙事中较为边缘的那个。《父母》以“爸爸”“妈妈”的称谓展开叙事,这意味着一切生活的进行其实是以那个失去孩子的眼睛来打量的,好像孩子在冥冥中目睹着被规定了身份归属的父母如何在“空无”中继续生活。
人称代词的使用有时将微妙地改变阅读关系。在《美满》中,略去的名字使叙事生成了目睹之感。曾经心心相印的男女,可能、已经或永不进入婚姻关系,那些活泼的与死灰的生命所历,不是道听途说,是发生着且被我们目睹着。这“有意”的虚化反而使“他”、“她”、“爸爸”、“妈妈”、“教授”、“妻子”有了普泛的面孔与更多的名字,那是从芸芸众生的眼里看去的芸芸众生的故事。淡豹不是在写“某一个”,而是在写“每一个”。
《女儿》为小说集中第一篇,虽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事,但作者在潜意识或有意识地,使叙事重心发生倾斜,小说中具有态度的判断几乎都出自“他”:他以为、他认定、他不那样想、他逐渐相信、他才会觉得、他强迫似的始终在考虑、他早该知道、他真正抱着歉疚、他意识到、他已经发现、他非常愿意……显然作者更共情于“他”,甚至只共情于“他”,这就使得小说的面目基本是以“他”的判断、感知、推测、揣摩展开,如此,小说的叙事动力极有可能来自作者对世界的把握与不确定,出自作者的目之所及,所以,《女儿》尽管以第三人称相对“全知”的视角展开,但更像是“第一人称式”的第三人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