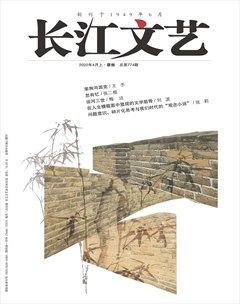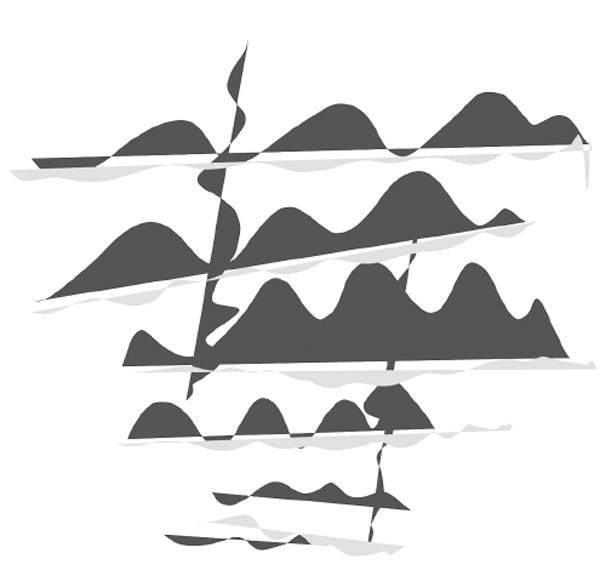
今年夏天,我被辞退以后,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阵,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我找来以前的旧手机,把通讯录从A翻到Z,挨个打过去。除了几个令我犹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数寒暄。“你好,打扰了,我是xxx,还记得吗?”“是我是我,你在家吗?有空出来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约出来吃饭。有时我请客,更多的是对方请。
提到霍明的时候,我正坐在两个老同学的对面,往碗里的鱼头上弹烟灰。我们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这顿饭吃吃停停,已经一个多小时。我们把各自的工作与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对结婚的恐惧,已经聊了个遍,烟也吸了一包半。本来还有个做销售员的同学坐我旁边,总想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关于国际形势的话题,也被我们掐灭,终于在两分钟前接起一个电话,向我们道歉后,没有结账就起身离开了。
“没意思啊,“坐在里侧做工程的同学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外侧的律师助理对着手机屏幕傻笑,没回应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镜,望向我。他戴着远视眼镜,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的眼球像是挤在玻璃瓶子里的香槟,即将从镜框里喷射出来。
他说:“我记得你以前和霍明的关系也挺好吧。”
我说,“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两声,牙齿白得不像是抽烟喝酒的人,“他在我这背过几万块钱的债,我还是上门找了他爸,才把这笔钱给要回来的。”
律师助理抬头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说:“你懂什么,你跟他又不熟。对吧。”
他又转向我说。“你应该见识过吧,他花起钱来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没辙才找的他爸。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来?”
我们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霍明坐进律师助理的车时,底座嘎吱一响,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艇。上初中时,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个还没长开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课本垒成的城堡后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题的时候,我会隔着衣服,把手指塞进他肚子的褶皱里,上下三层,起伏如平稳的海浪,手指在里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场梦里。如今,褶皱被更多的肉填满,连成一个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过去,他已经彻底长开,身型壮硕,吹过的风沙也印入到皮肤里。只有手丝毫没变。中学时代,班上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捏过霍明的手。他的指节修长,手掌柔软,夹起烟来有一股怪异的阴柔感,让人联想起太宰治小说里的人物。以前我總对他说,你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你应该去学钢琴。但他并不懂音乐,甚至连撒尿时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见到我,就用胳膊夹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拳,“多少年没回来了,啊?连个音讯也没有。”我把手撑在肮脏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意识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转过头去,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四处兜风,开无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闹之中,绕开了许多本该去谈论的话题。临近午夜时,做工程的把我们挨个送回去,互相承诺有空常联系,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多找找他们。我允诺后,很自然地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门口的早餐店排队买热干面的时候,霍明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再见一面。他的声音里有一层低沉的水雾,不像昨晚四个人一起谈天时那么兴致勃勃。
我太熟悉他声音里的那层水雾。许多年前,当他刚从浴缸里爬出来,披着浴袍,光着脚,嘴里叼一支烟,在他空旷的家里寻找一个打火机时候,就会用那种带着雾气的嗓音跟我说话。“你莫光站着,快来帮我找。”他嘴里与皮肤上的水汽会慢慢浸进那支烟里,让它变得疲软下去,逐渐透明。
那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但并不同班。所谓半封闭式的意思,就是能办下走读证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学校大门,其他人则只要靠近校门二十米内,就会被门卫警告或驱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拿到过那张神秘的走读证。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另一种解读方式,更能体现出半封闭式的含义:学校的围墙上有两处近似缺口的地方,一处在南端,宿舍楼附近,墙顶的玻璃渣被人用石头细细磨平了,被我们称作南门;一处在北端,大门附近,铁栏杆顶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弯,被我们称作北门。南端的那个靠近网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从这儿走;北端的那个靠近餐馆,逃课或加餐的人从那儿出。
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师或门卫经过这里,也会扭过头假装没有看见。反正大门是不许走的,交了学费又不想学习的混子们,想要出去玩,就得各凭本事。于是,在我们学校,读书和翻墙,总得会一样才行。而且,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学不会翻墙的软蛋,或者没胆子逃课的■,才会认命地弯下腰好好读书,去谋求那条更艰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会翻墙的人。不光会翻墙,而且是身手矫健的佼佼者,所以我们连南门北门都不屑于走,专门找教学楼附近,透过教室窗户就能看见的墙。助跑几步,沉住下盘,心里想着一个讨厌的人,对着墙壁飞蹬一脚,手臂轻飘飘地搭上墙沿。再往侧边伸出条腿,身子就能甩到墙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环节,需要我在后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几乎每次逃课都会叫上我。
黄金时间是在下午第一节课后。再早出去的时间太长,比较危险,再晚出去的时间太短,这风险就冒得毫无意义。出了学校,直奔他家,一两公里的距离。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个公子哥脾气,骂我抠门,非要打车。付账的时候又总在裤兜里摸来摸去,假装没看见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神。最后我给了钱,埋怨他两句,他再骂一次我抠门,“裤兜太深,多摸几下不就有了。上去请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他的姥姥庇护我们,答应替我们保守逃学的秘密。他家是个双层结构,我们在旋转楼梯上的房间里打游戏,每隔一会儿,姥姥就会把他叫到楼下,交给他点儿什么。两杯水,或是刚刚洗好的水果。她腿脚不便,无法弯曲得太多,走不了家里那个狭窄陡峭的楼梯。
楼上的房间对姥姥来说,是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她只能永远地待在楼下,在大厅、厨房和她那间永远拉上窗帘的暗沉房间里来回走动,脚步碎得像在发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起身把放在桌头的果盘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皺抖平,唤几声霍明,通常十次会有三次得到回应。
相反的,我会尽量减少在他家的一楼逗留。进门和姥姥打招呼后,我就溜到二楼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楼吃饭。
我讨厌一楼的那片空间。摆在电视墙旁的柜式钟摆,像一柄沉闷的大锤,每秒敲击一次,声音大得吓人,把整个屋子笼罩其中。只要待在那里,就无法不意识到,时间是一个多么坚硬而危险的东西,它扣击在四周的墙壁上,仿佛死神的指关节。即使窝在二楼的房间里,把游戏声开到很大,依然能听到余音穿门而来。我问过霍明,为什么不把那个蠢钟给扔了,这不利于健康。他告诉我说,习惯了。
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还有另一个不喜欢下楼的理由。我有点害怕他姥姥。
其实我也无法说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觉。与对蛇、对山谷、对噩梦的那种恐惧当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一旦进入视线,随即就会钻入脑中,需要用力才能甩开的不适感。
面对他姥姥时的恐惧,就像正对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镜子,让我局促不安,无所适从。面对它时,我无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应该摆出哪种姿态才好。因此,每次进霍明的家门之前,我都要在门口的防滑垫上多蹬几下鞋底,进门以后赶紧弯腰脱鞋,开始对鞋尖有没有对齐、摆放是否工整产生莫大的兴趣。
“来啦,哎呀,真懂礼貌。”他姥姥这么说道。我哈着腰叫一声姥姥好,转而捋起袜子上的褶皱来。
“我们要可乐,冰的。”霍明说。
等他姥姥用颤抖的手把霍明的两条胳膊从上到下捏一遍后,她会转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们上楼,打开电脑,把书包放到飘窗上,霍明会在他姥姥的吆喝声里下去拿水。
其实,我常会偷偷地观察他姥姥。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见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点,仿佛正在一点点缩回孩童的状态。
她患着一种奇怪的病,会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说起话来,语调会被头部摆得乱飞起来,有时一个音尚未吐完,又被舌头甩回了口腔里,听起来含混不清。手和腿脚也时刻颤动着,仿佛总有一股冷风缠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战。我第一次来时,就想问霍明怎么回事,但他并无向我解释点什么的意思,我也就没有问出口了。
他姥姥使我想起我的姥姥。但我其实没有姥姥。这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妈妈说,在她17岁那年,她和她当时的小男朋友在课间的楼道阴影里接吻,相互抚摸,被准备回办公室拿书的老师撞个正着。在那个年代,过早萌生的情欲是一头可怕的怪兽,足以吞没一个人的命运。妈妈被开除了。每当谈论起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书包离开校园的那个时刻。她说,那天姥爷穿着沾满深色油渍的工作服来领她回家的,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厂里报到吧。”
姥姥则表现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妈妈争吵,用最刺耳的话咒骂她。后来的许多天里,整个屋子都成了她们的战场。不到一年的时间,姥姥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时,工厂即将倒闭,妈妈刚刚成年。
尽管我们都说,和她没有关系,但妈妈总觉得,癌细胞就是在她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凭空出现的,并在那些让人绝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养。
我没有见过我的姥姥,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听过妈妈的讲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象姥姥的模样。我猜想,她应该很瘦,但整个身子往里扣着,显得很沉重,乳房无力地吊着,像两个没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应该是充满愤怒的,但最终还是被生活搅拌成了绝望。
后来,我不再想象了。见到霍明的姥姥后,我又开始想了。但霍明的姥姥显然和我姥姥——或者说我想象中的姥姥——不太一样。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阴影。
有一次我问霍明,姥姥叫什么名字,他那会儿正夹着一支烟,头从打开的窗户缝里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说:“你这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啊。”
我说:“你不晓得你姥姥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哪晓得,我爸叫她妈妈,我叫她姥姥,买菜的叫她吴婆婆。我没事叫她名字干什么。”
他在窗沿上摁灭了烟头,顺手朝外一甩,按下开机键,问我:“你今天要玩哪个英雄?”
我们在二楼房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但那里只有一台电脑,我们只能换着玩儿,一人来一局。大部分时候,他都会赖皮,趁着那局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去他书房的抽屉里找一支烟抽,是从他爸爸那里翻出来的黄鹤楼1916。或是叫我下楼帮他拿一点吃的,趁此机会偷偷再开一局。
晚饭之前,霍明会在二楼的浴室洗个澡。他一天要洗两次澡。听到水声响起来,他姥姥便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一般只做我们三个人的饭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丰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来,我便默契地不会留宿。晚饭后,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学校,从墙外面翻回宿舍里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默认的规矩。我们遵守这个没有理由的规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这种规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无效了。
这本是一个无所谓的规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许多时候,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想起那天的事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学校的惯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一节是没课的,专门用来大扫除。那是周围网吧最紧俏的一段时间,第二节的下课铃一响,南北门前排满了人,有感觉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胆子会去试一试往学校的后门冲,盼着趁门卫给住在学校的老师家属开门时一起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