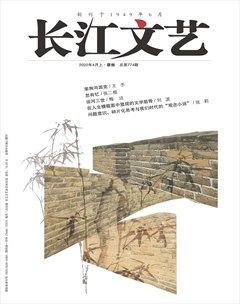淡豹是文坛新锐。当然,除了新锐作者,她身上还贴有为人熟知的若干标签:有着良好人类学背景的学院派、新媒体记者……这些标签显示了淡豹的知识结构和问题意识。要而言之,即淡豹的社会问题视野、人类学知识与“民族志/个人志”书写(何平语)的抱负。淡豹的作者意识因而常欲胀破文本,恨不能亲自出场,即席演讲。然而淡豹的文学阅读毕竟足够结实,尤其是她对世界文学的阅读经验,又时时刻刻校准着写作的实验性。谈论新作者总是冒险的,评论者往往过于傲慢而不自知,不能领会写作者的深深焦虑,何尝不是男性中心话语的积习?伊格尔顿在整理英国批评的历史时,曾设想了一个经典场景:“一位批评家坐下开始研究某个主题或某位作家,忽然他被一组令人困扰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打算研究给谁看、影响谁、令谁印象深刻?”长久以来,文学批评只能流转于文学史家之手,而放弃了对作者、读者说话。笔者首先启开作者的口述、访谈,重新讨论关于淡豹写作的既有共识,尝试为淡豹的创作个性赋形。
一
正是淡豹的问题意识发明了她的小说形式。淡豹健谈。在与编辑家徐晨亮的对谈中,淡豹谈道:“现实没有形状,现实中有随机、无端、武断、偶然的事件,许多纷繁的线,溢出结构的要素,不连贯的感情,不应该在那儿但偏偏一直在那儿的事物。”?譹?訛受过相当完整学术训练的作者带有明显的个案思维,更关心现实的偶然性。也是因此,作者无意于设置寓言结构和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倾心于更加具体、流动的文体形式。批评化地说,即以社会议题为题材,以亲密关系为系列个案,以小说为社会文化专栏。她倦于从那些具体的情感中提炼出普遍性,却在意现实事件的偶然性(特殊性)。淡豹所择取的现实经验尽可能流动而敞开,她的小说是流动的、不拘一格的。
谈论淡豹的知识结构,是为了理解其问题意识的来源。就题材而言,淡豹的写作一般取材于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以淡豹在文学期刊上次第发表的近作为例,《女儿》关乎亲密关系,《养生》关于养老话题,《山河》牵连代际、性别与生育问题,《父母》则聚焦于失独家庭创伤的疗愈。只看小说题目,自然是抽象甚至笨拙的,只是一组社会关系的名词(《山河》好像稍微好些?)。但若只存此想,可能并不体贴作者。我更愿意认为,作者拟定的这些题目,是浑欲直抒胸臆:她企图以“社会关系/亲密关系”为系列小说的主题。
有批评家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关系”的叙事(洪治纲语)。洪治纲先生认为,小说中的“关系”不仅是表面上的叙事技术问题,“关系”所指系伦理,伦理背后则是思想。一位脱胎于社会学训练的作者会如何理解小说中的“关系”?
淡豹所关心的显然是最基本的亲密关系。《女儿》写一个中年男人分手多年以后对前女友的酒后追忆,男女关系到同居为止。《养生》则是一位发达国家养老机构工作者自述行藏与旁观他人生活的碎碎念,并未定格于某一具体的关系,而全是关于关系的个人意见。由此观之,淡豹的写作并未设限于关系一种,而在于探索关系外延的动机、情感、观念。即使是在格外意识流的作品《女儿》中,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小说情节本身,而是叙述者密密匝匝的分析、议论。小说通篇以自由间接引语来写男主人公心事,而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又从议论中时时跳出,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双重自反:主人公对既往恋情的反省,与叙述者对主人公追忆行为的反思。在小说叙述的中段,作者不吝敷衍出连篇累牍来表达对悼亡叙事(悼亡诗、悼亡散文)的嘲讽。若单独摘出来,这简直不逊是一篇使人拍案的抨击男权社会的文化随笔。你看,作者说了,“悼亡是真正的男人的文体”。但须知,醉汉哪得如此惊警言语?从隐含作者大发议论回到叙述者的重温鸳梦,这段文字脱节而散落,反讽效果略显仓促,而精彩之处在于观念。毕竟在熟门熟路的文学课堂上,难见对悼亡作品的如此洞见,即便它只是生发于女性主义立场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