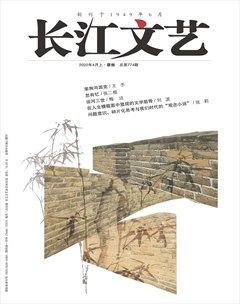若是诗歌像我们时下在网络上看到的部分“现实”一样虚假,那么诗就没有了意义和价值。作为诗人,应真诚地面对自我和真实世界,用哪怕微弱的声音去呐喊,抑或敦厚地记录,也从不失去本我的思考与观点。毋庸置疑,也恰恰是因了“意义”的存在,那些即使最微渺的事物在诗歌里才有了无穷尽的侧面。毕竟诗歌唯有通过希望赋予平凡生活的事件与事物以意义的需要,才能使它们免于毁灭在某种糟糕的处境。于此同时,这种带着“意义”的书写带来的愉悦与力量,在语言的作用下,会多出迷人的一面,甚至可能给出更多的谜面(诗的多义性),因为“诗令语词摆脱意指的任务,把它们还给那些在深渊边缘看到勿忘我的人,为这一有关场所的思想、为场所确定存在的思想提供帮助”(伊夫·博纳富瓦语)。
诗人在创作时是重新体验生命的快乐、忧愁,以及希望与绝望,他们用诗的形式传达的是个人情感的双目看到的世界的真实模样,并有着自己的色彩、嗓音和自己那可能转变成暴风雨的光线。从这点而言,一个好诗人与一个好导演有着近似性。如小津安二郎。他的电影最为非凡之处,或许就是其在描绘所认定的美好之物与事时,会毫不怀疑其美好,并能作为共情者充分地理解它们。这也是作为诗人的张二棍所具有的共性。他的诗歌有时像一个电影画面或几个画面,个人经验与想象(在这里指代思想的自由)在以诗歌形式呈现时,有着一种温情之外的无可名状的悲怆况味,抑或是悲情之外难以言喻的温情,《恩光》《穿墙术》《哭丧者说》《喊》等,都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不妨来看下他最近出版的诗集《搬山寄》里的同名诗。这首诗显然有着他对现实书写不时带来的失望感触,或是某种精神寄托,“我不舍昼夜,研习着搬山法/只求摆脱这遗世又困厄的无用/这丧家犬般的无用”,“我不愿目睹,我这苦命的一生/都在徒劳地,搬运着自己的艰辛”,他的如此这般的清醒意识无疑也成为他作为诗人“苦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