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松居直曾这样说道:“如果将我们的人生与李欧·李奥尼(Leo Lionni,1910-1999)的《田鼠阿佛》中的老鼠诗人相对照,或许有人会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的种子》,刘涤昭译,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向往诗意的梦想让一只老鼠重返心灵的宇宙,并感受语言星空的照耀。因为在这里,诗之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芳香艺术,想象的飞升永远忠于这副翅膀,田鼠阿佛“我思”故我梦,这是对语言之谜的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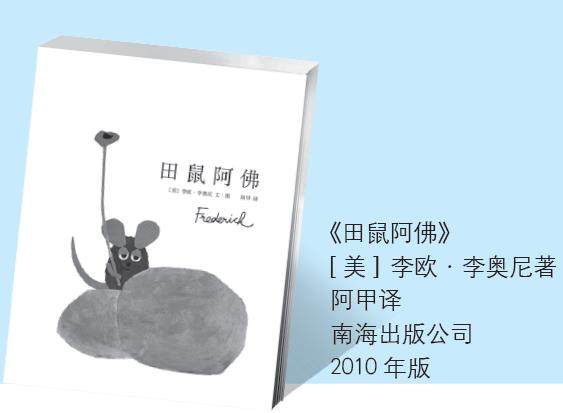
田鼠阿佛对语言的采集让我想起周朝的采诗官,《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皆出于此。而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永恒和一日》中也有一个诗人购买自己从未听过的词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采集词语、诗句与采集光和颜色并无本质的不同。或者可以用巴尔扎克在《幽谷百合》中的话来形容,它们是“墨水瓶里长出的鲜花”。
无论如何,一只写诗的老鼠的灵魂比诗人本身更加有趣,也许它可以直接化身为诗人T. S.艾略特,重新演绎《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又译《老负鼠的现世猫书》)。正如我们看到的,李奥尼创造了一个动物的缪斯,他所有的图画书本质上都是诗意的、流动的、充满空间感的。作为语言中的语言,诗必须成为语言的水晶,才能直抵核心,图画书的故事也是如此。“诗是无法解释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如是说。有些图画本身带给孩子的冲击有时也具有这种心理暗示。
对于儿童而言,图画比文字更具有魔力,因为图画的视觉信息直观丰富,更容易被接受。“观看先于语言……我们看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二者的关系从未被澄清。”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早已这样言明。儿童似乎具有天然的读图能力,在他们的世界中,故事有时仅仅是图像的指引。这依赖于儿童的感受和认知,图像中流动的光影投射到他们身上,想象就会赋予他们与图画书互动的自由。比如在《共读绘本的一年》中,幼儿园五岁的小女孩瑞妮认为阿佛这只棕色的小老鼠很像自己,因为她也喜欢思考“颜色”和“词语”的问题。当她的朋友柯芮认为“阿佛对朋友一点也不好”“他太自私了”时,瑞妮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和自私没关系,他是在思考……”(薇薇安·嘉辛·佩利著,枣泥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儿童对李奥尼的理解有时超乎你的想象,因为他们没有范式和惯例的约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进入内心的认知体验,这种对图画书的介入本身就让儿童身处奇妙的语境之中。作为一只老鼠,阿佛因为体型娇小,很容易引起儿童的共情。当然儿童的认知难以预料,他们的情绪、直觉、感受往往因自身理解故事的逻辑而赋予图画书更多有趣的解读的可能。
也许可以这么说,《田鼠阿佛》揭示了精神与物质或者说是天真与经验的某种碰撞,“诗”之无用构建的幻想图式如同那荒漠中的泉水,就像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中所说:“沙漠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那里隐藏着一口井。”阿佛的梦想指向虚无的力量,相较于其他老鼠采集的玉米、坚果、小麦和禾秆,并无实质的载体。但是,诗歌带来的内心抚慰却是其他老鼠无法体会的。直到阿佛将内心的场景诗化出来,一切才开始发生改变。这与《伊索寓言·蝉和蚂蚁》的故事形成对照。歌唱的蝉希望整个世界都充满自己的歌声,但是冬天来临,蝉向储存粮食的蚂蚁借粮时却被讥笑:“你夏天要唱歌的话,那冬天就去跳舞吧。”然而,如果循着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一文中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阿佛的心理演化:“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是一个诗人的世界,即使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必定还是个诗人……游戏是对儿童最具有吸引力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我们不妨这样说,每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正在展开想象的诗人。”阿佛的诗意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游戏的愉快想往,或者说呈现的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的特征,即“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流露出来的……”这是否就意味着阿佛并不幸福呢?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阿佛本质上就是在做自己的“白日梦”,但是,作为诗人的阿佛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神灵(灵感)的降临,他的幸福是真实的,至少最后他获得了老鼠们的尊重与理解,这在故事的结尾可以窥见端倪,当老鼠们一起为阿佛鼓掌喝彩,并称他是一位诗人时,阿佛这样说道:“是的,我知道。”这种情绪的表达充满自信,身份的认同让阿佛的社会化功能得以彰显,李奥尼的叙事逻辑一点点浸透在图画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老鼠的艺术形象在西方的作品中非常常見,英国作家格雷厄姆在《柳林风声》中就有这么一个画面:鼹鼠和水鼠在河流中缓缓划桨航行,两岸是丛林、鲜花和不停浮动的水草,他们的船是蓝色的,这种描绘与图画没有什么两样。在《一只老鼠的传奇》中,美国作家托尔塞·德勒也刻画出疯鼠家族的艺术气氛:他们喜欢在贝壳上画画,从开始的不被理解到收获信任,不断实现着自我成长。最经典的是怀特呈现的《精灵鼠小弟》的世界:“美国纽约有一位弗雷德里克·利特尔先生,他的第二个儿子一生下来,人人马上看到,这位小少爷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事实上,这个小宝宝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活像一只老鼠。他只有两英寸左右高,长着老鼠的尖鼻子、老鼠的长尾巴、老鼠的八字须,而且有老鼠那种灵活、害羞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