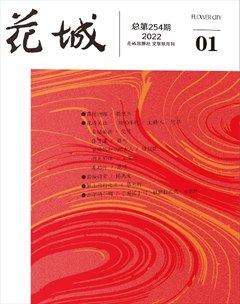一、所谓时代和个人的交集,在它们相遇的那一刻,个人也许是懵懂不觉的。意义可能是其后很久的忽然发现、赋予和添加。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谈话。这一系列谈话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2年6月,我大学毕业。和那一年毕业的绝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到基层去工作。我的基层是苏北县城的一个中等师范。这所1902年创办的公立师范学堂,在20世纪90年代(后文简称“90年代”)结束后的新世纪事实上消失了。1992年,距今三十年。
比1992年早两年,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这也是本专题路内小说《体育课》的时代背景。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是刘欢和韦唯唱的《亚洲雄风》。
时间开始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90年代开始了。
二、时间开始了,也是一个文学代际的出场。2020年12月5日,“莫干山花城文学论坛”,邀请了艾伟、张楚、弋舟、路内、付秀莹、阿乙、石一枫、孙频等小说家,主题是“‘不惑’和‘知天命’之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本专题是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的延续。论坛上,我提出一个扩容文学代际的设想,即,将20个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这十几年出生的作家作为一个社会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共同建构的文学代际。此前,在《文汇报》的短文中,我把这个文学代际命名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他们的文学出场是在90年代。和他们之前的“50后”“60后”不同,也跟他们后面更年轻的20世纪80年代(后文简称“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不同,这些作家发表作品的起点基本上是在90年代到新世纪初。准确地说,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从他们的写作和时代的关系来讲,他们和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的80年代出场的那批作家,不是一个代际。
参与本论坛的艾伟和路内都谈到90年代的问题。
何平:艾伟是对中国当代史有思考的作家。我们谈论文学代际,应该考虑到文学代际内部的思想演变,也应该考虑共同的时代体验和感受。90年代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挪用一句话,可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整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路内2020长篇小说的题目《雾行者》。“雾行”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90年代,至少是某些阶段共同的时代体验和感受。80年代大家以为已经看得很清楚的许多东西,但是到了90年代好像又不是那样了。
艾伟:刚才何教授其实谈到了90年代文学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讲到80年代文学的时候,它是非常清晰地被命名的。比如有几个关键词,有一个现代化的目标,有理想主义启蒙的逻辑在里面,所以80年代文学确实是被“命名”的。90年代的命名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文学“碎片化”。这个“碎片化”的命名,当然,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刚才何平也讲,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
80年代的文学有一个启蒙的逻辑在里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的继续。90年代开始的文学逻辑就是刚才何平说的,“南方谈话”以后的一个逻辑。如何命名90年代文学,这是一件亟须要做的事情。90年代以来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内部真正的逻辑是什么?90年代文学很成熟了,我们经常说80年代具有先锋意义,先锋是凌空蹈虚,它是不及物的,到90年代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走向了人间大地,有了人间烟火,从没有温度的人走向有温度的人。90年代的文学无论从文本、从技术上讲,都完全消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写作的技法,我们很自觉地和中国经验进行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90年代文学确实是很重要的存在,这个存在如果没能为之命名,没有批评家进行重新的阐释,我觉得是批评家的失责,而不是作家的不努力。
路内: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的一代人,和平常所说的“一代人”不是一个概念,有偏差。文学的一代人,有地域政治的因素掺入,还有一些是精英分子话语。打个比方,没有中国内地的一系列年代背景,即使这个作家用华语写作,也很难被纳入同代人。我作为作家来看下一代作者,和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看下一代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
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1997年,非要计较的话,我也算是90年代出来的作家。90年代的气氛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我们都会比较多地读文学期刊,2000年前后就不太看期刊了,你可以到网上看这些作品。但是20年过去了,现在我又会愿意看一看期刊了,这些期刊的关注度又变得很高。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跟“80后”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是同时使用电脑,同时上网的,共同语言就特别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互联网跟热水器不是一回事,互联网对人的精神影响太大了,如果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上网的话,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共同语言。但是这种情况、这种技术变革,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能很难再有类似的了。在手机这种东西上我会落后,小孩的语言我听不懂,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上一代人。但是在使用互联网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是否还存在技术的原因,造成了代沟的产生?
何平:刚才路内谈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地理空间和媒介。地理空间政治的问题肯定不只是在90年代才存在的,但90年代有它的独特性;而媒介,用笔还是电脑写,则完全不同。路内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说的文学代际,不是把里面的复杂性抹平,反而恰恰是要描述文学代际的复杂性。
路内:我们这所谓的“一代人”里,已经包含了“我者”和“他者”。说实话,有一些作家让我感觉不到是“一代人”,但是我在摇滚歌手,甚至电视剧的编剧中间,都能够很清晰地辨识出哪个和我是一代人,哪个和我不是一代人。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文学代际,在泛文化的层面上就已经开始归纳出所谓的“我者”和“他者”这样的“一代人”的概念。
三、小说家自觉处理个人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历史遗产问题,是近年中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2020年小说家钟求是出版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等待呼吸》写杜怡与夏小松在莫斯科的故事,他们在莫斯科不可能完全进入苏联的那一历史时刻,在那里他们既是边缘人又是异乡人,因此写的也是革命时代的异乡人的故事。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杜怡和夏小松是80年代的历史剩余物。这部小说体现了一个作家在解决他必须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时的写作难度和策略,为当下类似的写作提供了有意义、可借鉴的案例,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专题的参考文本。应该说,我们这个专题可以引入大量的参考文本,比如80年代成名的作家余华、格非、苏童等都曾经试图处理90年代中国经验。
《走起书》对这个议题的文学表达也许不像职业作家那么自觉。故虽然是小说,但节选的《走起书》第一部分更接近未经加工的时代实录。有意思的是,小说寻找失踪的弟弟方小亮,起于建省不久的海南,也终于莫斯科。小说时间从80年代末流转到90年代,空间则从北京位移到海南、广州、南海的岛屿,一直延展到莫斯科。这中间是90年代以“走起”為精神内核的人生传奇,包括财富传说和个体命运浮沉。可资对读的是鲁敏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冬季卷),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金色河流》。小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海南部分,这是一个国家的“海南往事”,并且没有被我们时代的文学充分表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海南开放自由的氛围吸引了大量移民的到来。小说中对于南方之南的“荒蛮之境、瘴疠之地”的描写,失序的经济和沉沦的文化,闯海生存与“钱老师”时代的恋爱狂想纠缠在一起。小说岛屿延伸到我们固有领土的南海“未名礁”,这似乎是一种隐喻,岛屿与大陆的对照记,亦可是审美飞地狂想。这部小说更重要的意义可能是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忆。
四、2014年,在和批评家何言宏的一次对谈中,艾伟提出一个疑问:“我们有如此庞大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可为什么我们的写作却很少真正正面地触及这些问题?”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整体性的内在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如艾伟说的,有着人世间的暖意和欢娱,存在人性的挤压和宽放;改革开放时代也当然地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前特殊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遗产。艾伟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或者实践分为“革命意识形态”和“市场欲望”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对私生活,尤其是对男女之爱的组织是完全不同的。《幸福旅社》是对发表于《江南》2013年第6期的《离家五百里》的重写。小说的现在时间,按照小说的提示:“酒吧的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则纪录片。纪录片播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传奇人生,一个月前这位流行天王意外离世,整个世界都在纪念他。”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于2009年6月,这意味着小说十年前的过去时间是1999年。这篇“小镇往事”应该属于艾伟理解的“市场欲望”经验,艾伟写怀着心事来到小镇的神秘异乡客,结识了身世坎坷、身心破碎的少女。少女欲对异乡客献出身体,意求被带离小镇,从不伦的家庭获得解救。而异乡客其实是十年前,在小镇欲对少女的姐姐图谋不轨时错手杀死对方,并埋尸远走的两个凶手之一。二人无法告解,无从救赎,各自在过往的阴影中无法走向光亮。小说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隐约的细节,10年前,小镇经济正盛的时候,外来的游客带来的新的消闲方式对于宁静小镇的冲击,人群的流动带来的犯罪并逃逸于人群的可能,那是一个欲望恣意张狂的90年代缩影。十年后,小镇的水与形都浑浊黯淡,罪恶的影子依然游荡在其中,成为影子中的影子、更深处的黑暗。
2020年12月,路内的《雾行者》入选“收获文学榜”,我给这部小说写了推荐语。《雾行者》是路内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小说以“雾”命名世纪之交1998到2008年的过渡时代,以“行者”指认流徙的江湖儿女们。小说中如雾的时代不只是前途未卜,不只是暧昧不明,而是包裹和深藏着激流过峡谷般的动荡、喧腾和泥沙俱下。那些江湖儿女们,譬如周劭,譬如端木云,譬如林杰,譬如杨雄,他们确实是隐失在我们时代的无名者和匿名人,但他们又是他们自己世界的“当代英雄”。《雾行者》直逼时代问题和困境,但它不是为时代写信史,路内最终面对的是自己的问题和困境。《雾行者》以残余的青春热血灌注即将到来的沉潜中年之思,从混沌的时代萃取和发明小说的结构,已然将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审美拉升到新的高度。巧合的是《雾行者》的小说时间和《幸福旅社》几乎同时。《体育课》是路内“少年热血”的“职校往事”,也是《雾行者》的青春前史。这个系列的小说,路内2018年结集为《十七岁的轻骑兵》。《体育课》,1990年的职业学校,半社会半学校,半恣意半疯癫,半诗意半人间。小说回到青春期,也回到90年代的起点。走回去,走回到没心没肺的岁月里,在慌乱莽撞中停住,发现某个至关重要的瞬间,如此戏谑,如此深情,如此伤感。
《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并无确定的时间标记。2000年,徐则臣大学本科毕业,不久他将要到更大的世界去,这个世界是他小说的“北京”。他把他小说的过去“回故乡”留在了新世纪到来之前,不只是那个给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花街往事”。与惊惧世界之变不同,徐则臣“回故乡”依然有着世道人心的恒常,故而,这里可以成为他“到世界”去的精神故地。《宋骑鹅和他的女人》中白胖的宋骑鹅是个糊里糊涂的好人,他拿出所有积蓄给撞了船的船掌柜补窟窿,娶了船掌柜肚子里怀着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孩子的女儿,他顶下别人犯下的强奸罪入了监狱,认下了服刑期间他老婆跟别人怀上的另一个孩子。《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克制而简约的叙事提供了进入一种往事的调性。
王莫之《明天的烟》是一篇差点被错过的小说。一年前,王莫之把小说发到我的邮箱,“花城关注”一直没有合适的主题来处理。在这一年里,我忘记了告知处理结果,王莫之也没有打听处理结果。说这些,是因为这种年轻作家少有的疏淡。《明天的烟》仅仅两万多字,却写出时代的细史,以及许多人可以反观自身的个人记忆和微观精神史。蟹居又瘦又短的G路、石库门建筑二楼的“上古”文艺青年老姚。所谓上古的起点无非8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在“90后”自由撰稿人笔下的上古史,包括但不限于大学时代向比他大的学生买二手随身听和“拷带”;给音乐杂志的歌迷会内刊从国外杂志上扒乐坛动态;给正刊写专栏,在专栏里为欧美的摇滚巨星编译小传;在联谊大厦上班族的垃圾桶翻国外报刊的音乐资讯;在音乐杂志编辑部参与到90年代的夏天的文艺沙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1992年去广东沿海村批发打口磁带;毕业后有了自己的唱片店。时间回到现在,30年后,老姚在G路自己的黑胶唱片店每个周末复制着那一种文艺沙龙,同时复制的还有放肆的谈笑和冰啤酒。店铺以唱片聚起同类,街道以神秘聚合的文艺店铺呼唤友邻。这中间有一位是让他着迷的“90后”自由撰稿人,虽然不幸她爱着他的至交好友。老姚经历过沪上淮海路、福州路、文庙、音乐学院门口到处都是卖打口的地摊,马路上的音像店比书店还多的黄金时代,来到了购买进口唱片的海淘之路愈加艰难的现在。但是有些东西依旧存留,就像老姚的周末沙龙,就像书店联盟周末不断变幻主题的市集。一个女孩倒在了马路上,一种生活停顿。一个男人在唱片店第一次放起有歌词的唱片,一个男人在路边点上了一支烟。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时代仍在继续。
五、《凤凰读书》做过一个“六十年家国系列”专题。其中,关于“国家阅读史”有一篇《六十年语文课改与国家变迁》观察到:“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这篇六十年语文课改史举了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做例子: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有意思的是,时隔四十年,2019年11月出版的《鲤》,当期主题也是《我去二○○○年》。这一期张悦然、周嘉宁、杨庆祥、李静睿、魏思孝、毕赣、笛安、班宇、郑执等“80后”以随笔和小说打捞他们少年记忆的90年代。)不仅如此,课文篇目里也出现了《小猫钓鱼》《乌鸦喝水》等中外经典童话和寓言。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为什么要从教材改革说起?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即便生于改革开放时代之前,他们的学校教育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回归、复苏和重建之时。而且,20世纪70年代前期,我们从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等也能发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应该是他们和前辈作家完全不同的人生起点,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整个生命成长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阶段展开。
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林斤瀾、高晓声、陆文夫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麦家、东西、艾伟等,他们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书写改革开放时代都有过去时代的经验做参照系,所以,他们写改革开放时代,自然而然地也都从过去时代的历史逻辑向下生长。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这个文学代际,改革开放时代几乎和他们的精神史等长,虽然他们也偶尔回溯,比如弋舟的《随园》,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朱雀》《北鸢》,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张悦然的《茧》,默音的《甲马》……这些小说都涉及在家族世系的传递上识别和再认“我是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青年作家的小说有一些把时间标记得特别清楚,而且有的时间跟时代都对应得特别紧,比如路内的《雾行者》、周嘉宁的《基本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逍遥游》、七堇年的《平生欢》、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和《鲛在水中央》、张玲玲的《嫉妒》,等等,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年轻作家正在命名他们自己生焉在焉的改革开放时代。进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而来的当代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时间开始了。文学如何处理包括90年代在内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经验?对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而言,他们每个人的小编年史正在汇流到他们共时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长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期待改革开放时代儿女们的文学好路和新路。
2021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