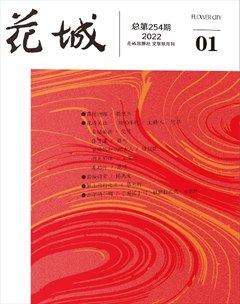1
老姚梦见自己在淘碟。一大堆爵士尖货,那些伟大的鼓吹艺术家,深藏不露的自由斗士,黑皮肤与金色的英文字母放声高歌——然后他醒了。还行,没有变形,他躺在那张本色的藤椅里,还尿颤似的抖了一下。眼角怎么湿了,手摸上去,又是雨珠一颗,仿佛逃逸的乐符。窗外,一支隐形的乐团正在天上大发神经。

嘎吱嘎吱,是门外的木质楼梯在响。这是一栋老式的石库门建筑,为老姚以及数千张唱片提供住宿的是二楼。老姚玩黑胶比较早,十几年前花二三十块钱淘的二手货现在基本上都能卖到三位数,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收藏向公众开放,门上挂着“无伴奏”的店招,那三个醉醺醺的汉字是由本市的摇滚明星陆晨题写的。此刻,门口来了一个陌生人,他的目光刚刚离开那幅字,正要往屋里进发——满眼的黑胶唱片,使得那把原本握着的折伞迫不及待地要往门沿上靠。雨珠顺着绛红色的伞布往下滴,拖泥带水的黑皮鞋正在入侵。
“是卖黑胶的无伴奏吗?”陌生人欣喜地亮了一嗓子。
“你搞错了,这里不卖黑胶。”老姚低着脑袋对那双黑皮鞋说,仿佛那是什么尖货。
“我看这里写着无伴奏。”
“地方没错,但是功能不对。”在老姚的坚持之下,一阵清风将“无伴奏”定义为私人的音乐沙龙。
“对外开放吗?”陌生人随口问起。从他进屋以来,参观的步伐还没有停过。挺正气的屋子,有20多平方米,多数墙面都被唱片架覆盖了,只在靠窗的位置留了一些民居的迹象,挂着空调,摆了一套音响。藤椅、折叠椅、茶几啊、办公桌什么的,全都失去了家具应有的味道,倒像是柔道馆的道具,随心所欲地填充、摇摆着。
“只对朋友开放,”老姚挪来一把椅子,“不过我们可以坐下来先聊聊。”
陌生人东张张,西望望,还像野兽觅食似的,最后是几排电影原声的专辑让他静了一会儿。他搬了几句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话,老姚认为,这些关于“无伴奏”的介绍纯属谣言。“卢恪约我来的,他应该快到了吧。”陌生人不过是回头这么一说,老姚不响了。卢恪这个名字在他身上起了一些波浪,好比在海淘的过程中遇到了心仪的目标。水面不断上涨,已然淹没了他的嘴唇。
“据说这里的唱片都是纯音乐,没有歌词。”
“没有歌词是我收碟的原则,”老姚又活了过来,“别看我们这里有许多古典唱片,但是没有一张是歌剧,连弥撒都没有。”
可是,在功放的上面明明摆着一个例外。
“那是贡品。”老姚如此解释。
“怎么沒拆啊!”
“开玩笑,给观音供一个啃过的水果啊?”老姚笑了。误会啊,纯属误会,一切的误会要等到卢恪来了才能解开。可恨的卢恪,那个前著名记者,现在沦落到和老姚一起开网约车的中年糨糊桶,他现身之后还预警似的把大门当木鱼敲,倚墙而站,笑得那么淫邪。他把鞋子脱了,问题是,“无伴奏”并不提供拖鞋。
两天后,“无伴奏”迎来了周六的例行派对。卢恪冷不丁地起了一个高调:“我事先跟他打过招呼,他倒好,对人家不冷不热,就像大闸蟹吐泡泡,一副死腔。”大家也学大闸蟹,把笑声当泡泡那样吐出来。“好好好,”老姚起身招呼,“大闸蟹帮你们买啤酒去。”
在座的都是老姚的朋友,多数都穿着鞋,有几位对他的毛病比较熟悉,有时还像自来水似的在圈内编他的段子。譬如那句:“请你尊重我,就像尊重人有信仰。”搭配他的照片做成表情包。他的信仰就是“无伴奏”不欢迎歌词,仿佛一切基于文字的编织都是革命的叛徒。从实体唱片的层面,肃清的工作被他贯彻得极为彻底,即便有漏网,也是从新朋友的手机里刚刚逃脱,届时,老姚必定会礼貌地迎上去:“麻烦出去接电话。”他从来不把顾客当上帝。他的另一句金句是:“这里没有上帝,只有规矩。”大家惊恐地联想到上帝已死,随后无不表示理解。毕竟,这里是老姚的地盘,大家吃他的,喝他的,听他的唱片,一切似乎变得习惯而自然。如果谁的手机铃声不巧是一首歌,那么在踏入“无伴奏”的领土之前,会像进剧场那样,识相地先把手机调至静音。
“再带包花生米上来。”卢恪向窗外新出现的老姚打手势。梧桐树厚密的叶子遮不住正在横穿G路的老姚,他进了斜对面的烟杂店,因为回头答话时带了脾气,差点绊了一跤。他不喜欢花生米的叫法,让他想起白茅岭、提篮桥之类的地方。这个男人固守着某种传统,跟烟杂店的老板说:“拿包长生果。”对方心领神会,好比情报员接头。还有500毫升的罐装啤酒,不点名,只报数字,像今晚这等规模的派对,一般会提两大塑料袋回来。对此,朋友们颇有微词。有一次,同住G路、在76号开书店的那位仁兄忍不住开了口,他建议老姚网购啤酒,非但省钱,还省力。老姚拒绝了。76号为此跷了两个大拇哥,赞美老姚不像上海人。76号今晚缺席,在五角场摆书摊。整条G路是由老弄堂、老洋房构成的,东躲西藏了七家独立书店,主题不同,店主清一色都是沪漂。他们自组了某个江湖联盟,加上各路外援,每月选一个周末,与那些赏识他们的机构合办各种名目的文艺市集。老姚和“无伴奏”一直都在受邀之列,始终拒绝参与。
“声音别太响。”说话时老姚刚回到“无伴奏”,他先是掩上房门,再指挥卢恪拉拢窗帘,只差把音响关了,全部藏进柜子里用棉被捂得紧紧的。朋友们笑他电视剧看多了。他们与老姚虽然都是旧相识,在“无伴奏”却是新客。
“太响楼下的老太会报警的。”老姚把酒饮和小食交给卢恪,请他帮着分发。三年前的故事也有分享的必要。当时“无伴奏”应该说是试营业,也是今晚这样的聚会,没放音乐都惊动了派出所。一开始大家完全蒙了,老姚说,屋里安静得就像冷库,一大堆黄鱼带鱼鲳鱼,眼珠子瞪得老大。好在是虚惊一场。“老派”离开时没留下半句话,后来却使出一记回马枪,连珠炮似的报地址,多少号后门几零几,反复确认是后门吗?因为这一带的门牌号有前后之分。
“地址对的,”老姚说,“啥情况啊,警察先生?”
“有人投诉你们扰民。”
听故事的基本上哑了。
“后来他一看我供的这张黑胶,”老姚禁不住拍了大腿一下,得意地指指功放,“马上逢凶化吉。”
“开啥国际玩笑。”
“千真万确啊,”老姚拉响了易拉罐,“人家讲了,也是她的歌迷,就差对她鞠一躬了。”
众人议论,或者说是调查,有谁不是她的歌迷。
“老姚,你进点她的黑胶卖卖蛮好。”
“开啥国际玩笑!”老姚喝口啤酒压压惊,仿佛是神灵遭到亵渎。
“最近是不是生意特别好啊,我看架子上空掉不少。”
“不谈了!不谈了!再下去就要碟荒了。今天早上又收到传票,叫我去机场补税。”老姚抱怨道。他所谓的机场位于迎宾八路,是一个令“海淘客”胆寒的相关部门,通常货物被扣下了,就会收到一封“告客户书”:
尊敬的客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6、47规定……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我,”老姚讷讷起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做代购的。”理由是这些海淘来的唱片无一例外会被他拆了把玩,短则几周,长则数月,才考虑是否摆进“无伴奏”。在判决之前,新进的唱片全都关押在隔壁的卧室。
“他们是一手代购,你是二手代购。”
整间屋子为了这句话而争鸣。F女士,掌管着一家只卖外版画册的民营书店,她吃花生必要将外面那层红衣剥干净。“去年我们店里也碰着过的,”她嚷嚷道,“讲接到投诉,怀疑我们卖淫秽出版物。”茶几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她,被她擂得砰砰响。“我就拿进货的单子还有发票给他们看,全部都是‘中图’正规渠道。”警报解除了。“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得罪过人,要么就是生意太好,同行眼红了。”女士把店里的生意渲染得极惨。她思来想去,想起了那个因为手脚不干净而被她辞退的小青年。
“那你们的书到底有问题不啦?”
“摄影集呀,你们懂的。”
“生意太好的确是个问题,蓝木头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听死亡金属的?”
“对的,大自鸣钟搬掉之前他就在淘宝卖原版CD,老朋友里,他算是混得比较好的。我跟他也有五六年没碰头了,上个礼拜看演出的時候碰着了,听他讲起被淘宝封店的事情。”
“他的店也被封掉了?”老姚插了一嘴,“我记得他有证的呀。”
“淘宝讲他的证是假的,五年哦,过了五年才讲有问题,但是人家有本事呀,又办了一张。”
“怎么搞定的?”
“不晓得,他不肯讲。”
大家揣测这张证该怎么办,似乎总得先开一家公司,然后以法人的名义去有关部门申报。这个谜一般的话题持续发酵了十几分钟,最后得出了一个臭烘烘的结论——蓝木头的证是假的,或者说是在外地办的。有人为蓝木头预设了一种可能,就像卢恪的前妻那样,后者呢,几年前因为一场官司进了松江的女子监狱。
“还可以,前两日刚刚去看过。”卢恪感谢大家的关心。照他的意思,等前妻刑满释放了,便是他俩复婚的好日子。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话题,压得大家埋头喝啤酒、剥花生,零食还挺受欢迎的。卢恪后来下楼是因为酒不够喝了,他自己也是想换口气。当晚的聚会持续到凌晨,“无伴奏”没有因此多卖出一张唱片,反倒收进了一堆文物。那位捐赠者将近散局才如释重负。“送给我也没用啊。”老姚回绝道,却还是挑了一张打开:带缺口的碟片离开基座,光线照亮了内圈的编码。大家忘了老姚还有这手绝活,但凡正版CD,他瞄一眼IFPI之后的那串编码就能判断这张CD出自哪条生产线。
“L043,”老姚默念道,“百代公司MFG的老美版啊。”
“我还以为你在看有没有打到歌呢。”捐赠者笑笑说。二十多年前,他还是穷学生,这些被美帝国主义当毒垃圾处理到中国的打口CD都是他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帮帮忙,”他显然心意已决,“摆在我家里只有积灰,在你店里也许还有意义。”
“我家里也有一些老古董,下趟带给你。”
“好了,拿我此地当垃圾桶了。”在让步之前,老姚觉得有些话虽然不中听,但必须讲。他送大家下楼。一伙人全像做贼似的,因为老姚说了,底楼的老太容易惊醒。只有楼梯全然不给面子,嘎吱嘎吱地唱反调,路越往下走越是乌漆麻黑,还有人踢到了铁锅。这一下子,倒像是踩了地雷,浪花般的笑声将他们推到马路上。
夜已深,几只野猫忙着叫春,好些手指正在划手机。有人提议同样是叫网约车,这个钱应该让卢恪和老姚来赚。卢恪今夜是骑共享单车来的,因为来“无伴奏”怎么可能不喝酒。“就算开了也没用啊。”他说现在的系统不像以前,以前司机可以挑三拣四,现在是系统派单。
“哦,对的,老酒吃过了。”
“好了,”老姚领导似的招招手,“大家早点回去,早点休息吧。”此话一出,就连说的人自己都不信。回去之后,还要清扫,还要洗澡,老姚明白,还有一大堆的烦心事正等着他呢。
2
G路一年四季都是那么幽雅。它是混血的,仿佛东方女性在美国成家,海归之后却习惯蒙着黑纱。这条路又瘦又短,树枝似的斜着往上长,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只有一条单车道,或许是因为先天不足,公交车全都对它视而不见。街边的人气还行,开了不少平价的西餐厅、咖啡馆以及面包房,到了周末,老外最喜欢过来吃早午餐,把桌椅都挪到了店门之外。
在一个晴暖的周日,阳光透过枝叶,撞上了老姚卧室的窗帘。整整一天,“无伴奏”的主人都在为海淘的未来而烦恼,除了吃饭就没有出过家门,要等到次日的上午,等早高峰有所缓和,他才专程驾车去机场赎那个新近被扣的包裹。其实只是四张黑胶,金额和体积应该说是毫不起眼,要说特别,就是承担了一定的演习功能,看看当商品数量降到个位数、消费金额控制在100美金以内,海关是否会给他换一盏绿灯。
老姚想起五年前,当时整箱整箱地订购也没见到被扣啊。当然,那时的中美关系要比现在缓和得多。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一度跌到六出头那么一丁点儿,亚马逊美国为了拓展市场,突然化身圣诞老人,推出两美金起步、三天直达中国内地的试水政策。还有一个域名里有三匹骆驼的价格追踪器,给老姚在亚马逊美国淘特价黑胶提供了大量情报。那段日子何其潇洒啊,风风火火了几个月,然后呢,他挂职的报社解散了,亚马逊的新政突然叫停。他用遣散费换了一辆帕萨特,加入了网约车的队伍。“无伴奏”就是那时期在他的脑海里逐步构建起来的——偌大的上海滩,不该连一家像样的唱片店都没有。
好花不常开啊——老姚突然很想听邓丽君。趁着吃红灯,他在手机上选播了那首歌,整个人被开场暖意满满的弦乐包裹起来。每周,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是在驾驶座上度过的,在“无伴奏”以外的区域,他不会再为音乐设置任何门槛,歌词也不再忌讳,他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和古典,偶尔也听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民族音乐,这类唱片在“无伴奏”设有专柜,是大家眼里的新丝绸之路。
时间成本太高,今天甚至连一个搭顺风车的都没捞到,老姚估算这半天停工的损失,足够等下交税金了。他被一种无力感攫住了,苦于没有更好的进货渠道。要知道,“无伴奏”可是最讲规矩的地方,它的门槛太高了,能进来的音乐,国内基本上不会引进,换言之,过于依赖进口。国内偶尔也会发行几张能让老姚抬一下眼皮子的专辑,几乎都是CD,而CD现在毫无人气。在上周六之前,他已经很久没碰过CD了。
车子停在迎宾八路。鼓足勇气,老姚迈过那扇大门,在咨询台取申报单,笔却远在另一头。还好老姚自带了黑色水笔,填单子的当口,腿脚还惦记着抢号,不光是他,这简直成了老江湖的通病。等待补税的队伍绵延不绝,让人想起某些三甲医院。老姚翻了翻手中的号码,决定先找个座位。墙上挂着许多LED屏幕,提醒叫到号的可以去相关的窗口预检,还用“欢迎光临”四个红字安抚他们的神经。抱怨的声音大多集中在会被征多少税,还要等多久。有些人自称是从周边省市来的。补税为什么要挪到这鬼地方?“远得要死”。说上海话的大多怀念以前在武定路的日子。
“朋友,”坐在隔壁的把脑袋伸过来,“你是不是做代购的啊?”这位男青年见老姚装聋作哑,补充道:“上次也碰到你,真巧。”还问老姚是不是也在淘宝上开店。“没有,我开专车的。”老姚说,扭头想结束这段攀扯。“现在代购不好做啊,”男青年突发感想,“哎,开专车怎么样?”他打听具体的收入,似乎想改行。“还可以,最近有点补贴——”老姚正说着,一位女士推着载满包裹的小车经过。另一边,缴完税等待领件的几乎是全体起立。有人扯了嗓子叫唤:“麻烦,那只箱子是我的,对的,对的,就是那只,轻点,轻点。”
老姚清了清喉咙,一口浓痰吐在纸巾里。
“你试过网上申报吗?”男青年又问。
“每单多收50块,还不一定成功。”老姚说。
“你看我们干脆开个公司吧,专门帮大家申报,再送件上门。”男青年像煞有介事地提议。这完全是一种倒退啊,老姚心里的火气快要炸了,这种事情以前只是转运公司业务范围的一小块,根本不值一提。那时候,老姚经常在北美的网站下单,通常买满99美金就能享受北美地区的包邮,货物免费寄到老姚选用的转运公司,封箱再从美国发往上海。转运要比平价的直邮贵,但是老姚宁愿兜圈子,因为黑胶太娇嫩,外面多包一个纸板箱,就像给开摩托车的加了一身护具。天晓得啊,那些转运公司从上个月起统统跳票,打电话给老姚,说以后包裹入境将由顾客自行报关。简直是晴天霹雳。老姚一想到自己未来要在G路以及机场之间来回折腾,吓得改用直邮。他以为这样,最不济,包裹应该不会被扣。可眼下这单不仅被扣了,所有黑胶,光是封套就有不同程度的折损。鸡飞蛋打已经不足以形容老姚此刻的灰暗心情。整个归途,车上仿佛坐着四个伤骨科病人,容不下其他乘客,好几次吃红灯,老姚拍方向盘,痛下决心,要与海淘划清界限。
下午休息是老姚的临时决定。车子停在离G路不算近的小区。他抱着四位伤残人士,回家的路如此沉重,经过常光顾的那家面馆,他打算先回家安置妥当,再考虑果腹的问题。在淘碟的圈子,像他这样力求完美、对唱片品相吹毛求疵的也被称为“品相王子”。有一次,卢恪忍不住将了他一军:“看你那么宝贝,怎么舍得让别人翻来翻去。”“有啥办法呢?”老姚反问,“平常朋友过来玩,总归要翻要听的,所以每张黑胶要套自封袋,再多备几包湿纸巾喽。”说完,他抽出一张湿纸巾让卢恪擦手。他们刚刚吃过糖炒栗子。
还有别的进货渠道吗?难道以后真要因噎废食?那天下午,老姚身陷藤椅,为这个外交级的难题犯愁。大约3点出头,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随后是房门,吱呀呀被一位秀丽的女子推开。比起老姚,新进来的林辰更像是刚睡醒的模样。她搬一把椅子坐下。“拉窗帘的时候看到你气呼呼地回来。”字句就像一阵烟,从她的嘴里悠悠散开,仿佛她新掏的那支烟已经点燃。“又通宵啦?”老姚轉过头来问。见她不吭声,改口道:“稿子写完了?”他一连发射了两枚空炮,决定缓一缓,从地上的塑料袋里翻出一罐啤酒,举到林辰的面前。林辰摇摇头,吐口烟,许久之后思忖道:“楼下的提拉米苏不新鲜,大概是昨天卖剩下的。”茶几上有一本策兰的诗集,她随手翻几页。“98号的,”老姚叨了一句,“昨天喝醉了,想要自杀,说把心爱的诗人托付给我了。”那罐啤酒后来与黑封皮的诗集靠得很近。老姚呆呆地望着碟架上的空位;林辰转向窗外,两棵梧桐树,一前一后,就像绿灰相间的马赛克,模糊了她的家。
那是一年前,林辰从浦东的公寓搬到对面的那户单间。她和G路的绝大多数文化从业者一样没有正职。几家杂志社联合供养她。作为一个“90后”自由撰稿人,她虽然经常拖稿,但对待工作极为热忱,每月总有一两篇文章送印,都是特稿,短的五六千字,长的万余字。或许是因为这项技能,G路的书店联盟赏识她,换句话说,在好些店主的内心,她与“无伴奏”同属G路的文化圈。有人戏称她为“圈花”。他们将她视作自己人还有一个原因,她时常会去各家书店借烟,一次只借四支,多了不要,说是戒烟。很多店主对这种亲昵的行为有自己的理解。她借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店主们无不表露出某种遗憾,倒不是遗憾对方烟瘾久经考验,而是一些更抽象的情绪,诚如98号的诗人所言:“搞了半天,她也问你们借啊!”
受此打击,诗人不禁吟诵起来:
七天的烟你问七个人借
白日的情意留待深夜抽
皮鞭无情,蜡烛翻脸
无伴奏的冰块爱听迪斯科
那次大会在“无伴奏”可以说是隆重召开。挨批的老姚对于迪斯科的闯入表示抗议,因为电子舞曲的唱片在“无伴奏”所占的比例极小,他也不记得自己为林辰放过这种玩意儿。“修辞,就是一个修辞。”诗人嚷嚷道,吊着脖子喝啤酒。犹如在讲坛上,他振臂一呼:“你不觉得她特别冷艳吗?就是那种会在迪厅像块冰一样坐着的怪物。”老姚不响。群众便继续提审,因为“无伴奏”明明只有酒,而滴酒不沾的林辰却很喜欢过来坐坐。“因为她想戒烟吧,”老姚笑着给出解释,“你们那么热情,她去你们店里待久了,一根接一根嘛,更加戒不掉了。”群众觉得,此话虽然牵强,却不失智慧,老姚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猜不透林辰的心思,仿佛那是一组气象万千的朦胧诗。大会胜利闭幕,全票通过:林辰是一位真诚的戒烟斗士,证据便是她不挑烟,再烂的牌子都借。据有幸去过她家的诗人透露,在她的书桌上,笔记本电脑旁边的烟灰缸里,躺着许多只抽了几口的香烟,仿佛烧了一半的尸体。
想到这儿,老姚将视线迫降在林辰的脸上。那是他愿意花几个小时去描摹的景物,以至于他最近对画家这个职业有一点嫉妒。女模特儿的烟就快抽完了。老姚觉得自己有必要创造一个话题,便抱怨起新来的黑胶。那些受了外伤的唱片有幸得到林辰的检阅。她看中那套《黑暗骑士》的电影原声,要试听。老姚让她稍等,起身去找剪刀。
真是一门手艺:先用刀尖戳唱片塑封的右下角,将那层透明的薄膜顶起,轻轻地,一点点,顺势,往上划,通常,划到黑胶能够取出就行了,具有防护功能的塑封并不剥离。就在老姚开启这个具有考古趣味的发现之旅的当口,林辰的手机响了,接听之后主要是被电话那头训斥。起初,老姚还会停下手来观察她的脸部变化,等他把新到的四张唱片像厨师对付河豚那样料理干净,用加厚款的自封袋逐一套好,那通电话还在咆哮。其间,林辰也据理力争,态度却很谦和。
“又被骂了。”挂断电话后她如此自嘲。
“稿子没给人家确认过吧。”老姚说。
“这个案子我整整跟了两个月,一开始我很同情受害者的家属,后来去了被告家里,慢慢地,怎么说呢,很多想法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