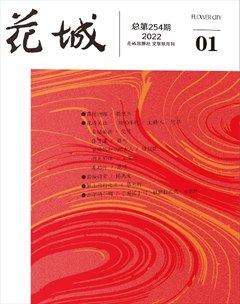上午十点的月亮
余静远 译
我第一次听说那幅地图,是从一个老师那里。这并不是他应该告诉我们的知识,但我觉得他有时对要做的事感到厌倦,就会转向其他话题。他是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且素有博学的名声,但他并不是我们正式的老师。他的名字是马林·哈桑·阿卜达拉。最近,他搬到隔壁,租住在我们邻居阿卜杜拉曼叔叔和法特玛小姐①楼下的一间房里。我们是出于尊敬才称阿卜杜拉曼夫妇为叔叔和阿姨的。他们没有子女,住在房子的上面两层,房子底层就空着。阿卜杜拉曼叔叔也是一位老师,但地位更高。他在一所英文授课的中学教书,还在坎帕拉②的麦克雷雷大学学习过。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欧洲人,与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做同事,让阿卜杜拉曼叔叔有了某种魅力。他与马林·哈桑肯定更早的时候就彼此认识了,也许年轻的时候还一起念过大学呢。
去马林·哈桑那儿学习,是母亲的主意。我们对额外的补课没有明显的需求。我们没缺过课,也没掉过队。小孩缺课掉队的情况会时常发生,比如,陪着父母去拜访亲戚啦,或者生病啦。那时的小孩生病可不是几天的事,而是一病就好几个月,等回到学校时,已比所有的人都落后一大截了——所有的人,除了那些顽固抵制学习任何东西,并将此视为荣誉和名声的人。父母对我们的事业也未有过那种令人生畏、需要持续训练的理想,不像学校那几个印度男孩的父母,早早就将他们送去额外培训班,期盼着他们以后成为医生或律师,或者数学方面的天才。
父母从未想过我们要如此荣耀,可他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学习。弟弟哈吉毫不费力就能做到学业出色,至少老师们都喜欢他、夸奖他,他也有很多朋友。哈吉比我低一年级,老师们却督促我向他学习,脑子灵光点,而不是鞭策他以我为榜样,学习我的勤奋。我是一个辛勤认真、做事慢吞吞的人,什么事情都需要解释得清楚明白,且每走一步都犹豫不决。人们有时纳闷我们俩谁才是哥哥。
至于妹妹兰达,她才刚开始上学,当她听说我们要去法特玛小姐家补课时,她也要求参加,在她还是个婴儿时,法特玛小姐就宠着她,是她最喜欢的阿姨。
我不清楚父亲对下午去补课这事儿是怎么想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要我睁大眼睛,更善于观察,保持自己的机智。又是那套我在学校必须忍受的陈词滥调。你必须对这个世界更加警觉,他告诉我。但他可能并不指望马林·哈桑教我如何做到这一点。总之,我不再琢磨我们为什么被送到马林·哈桑那儿了。我猜,母亲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能够展现她作为一个母亲对我们教育的关心。父亲并不总是像她那么有热情,甚至抱怨过我们从学校带回家的有些知识一点用都没有。学习英文摇篮曲或听那些贪婪的探险者吹嘘到底对谁有用呢?母亲认为,学校就是知识,虽然她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有自己的看法。英语和算术是有用的,学好了它们,我们就能继续念中学了。总之呢,我们隔壁住了一个老师,据说他读过的书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人读的书都要多,而且,他还有时间。
在成为我们老师之前,我就认识马林·哈桑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但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问我他是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他的名字。我还知道,他有时会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弹奏乌德琴①。有一年,父亲给我们买了节日②音乐会的门票。音乐让父亲头疼,而且塔拉布③歌曲中爱情的痛苦让他感到难为情,他就没去。马林·哈桑那晚就在管弦乐队中,与其他的音乐家一样,他身着黑西装,系着领结,穿着一套在别的时候不会有人穿的服装。这种着装模仿了埃及管弦音乐的表演,他们穿成这样来表达新潮。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埃及管弦音乐表演团体都对塔拉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林·哈桑身上有一种严肃的东西。他孤僻,疑心重,说话时声音透着尖刻,却尽量不去冒犯他人。走路时他眼眸低垂,跟人打招呼时拘谨,甚至稍稍有些急躁。这与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们会不停地跟人打招呼,会为了握个手而横穿马路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会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笑。傍晚的时候,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交谈、争辩、闲聊,与世界接轨。白天凉爽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大街上,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此,出行时最好避开某些街道。与别的男人不一样,马林·哈桑不大声说话,也不夸张地大笑。父亲也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这种粗野有失体统,父亲从未对任何人任何事提高过嗓门。他最爱的就是在咖啡馆里消磨数小时谈论政治,马林·哈桑有时也会经过咖啡馆,逗留一阵,喝上一杯咖啡,然后离开。
现在,当我回忆起他,并试着描述他时,我想起了这些细节。当他搬到隔壁房子里时,我没怎么注意。人们经常那么做,租下底楼的一间房独自生活。或许是他们在镇上工作,家人住在乡下;或许是家里空间有限,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各种堂表兄弟姐妹太多,空气中充斥着斗嘴和责骂;或许是其他复杂的原因使他们独自生活,为了更自由地呼吸,或为了以一种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
我估计,有人告诉过父亲,要他负责相关事宜,且在酬劳上与母亲达成一致。像往常一样,在这件事上,他们也许有过争执。母亲是众所周知的软心肠。邻居和亲戚只要讲到他们的不幸,母亲就会哭成泪人,然后就把不该送的、送不起的东西都送了出去:她最好的肯加衣裙④、她的珠宝、我们的晚餐。父亲的反应在恼怒和难以置信的大笑间波动,可母亲就是控制不住。我一开始没意识到,后来我就想,这额外的补课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好事,对马林·哈桑是不是也一样是好事呢。无论如何,某个下午,我们去上课了。
上课的房间在房子的前面。房间有两扇上了锁、从地板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的窗户,一扇在正前方,另一扇在侧边。两扇窗户的百叶窗都大开着,午后的光线流泻进房间。房间有四把靠墙放着的硬木椅子,一张摆在侧边窗户下的小书桌,我们到的时候,马林·哈桑正坐在书桌上面。房间更像是政府办公室,而不是起居生活的空间,极简,毫无装饰,混凝土地面光秃秃的,没有垫子,没有毛毯。乌德琴靠墙放在架子上。
我曾经很喜欢新学年与新老师见面时的忐忑不安,可是马林·哈桑低垂的目光和短短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既悲伤又令人望而生畏。第一次上课,我心情沉重,在房间的门槛处踢掉了凉鞋。我们被要求带上学校的练习册,马林·哈桑将我们安置在房间不同的角落里,他简要地看了看我们的练习册,然后给我们布置不同的习题,我们努力做题时,他就守在我们旁边。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犹疑,就像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一样。我们互相间不说话,也几乎没有眼神交流。这种紧张的情况持续了三节课——我们两周去一次——第四次到的时候,我们发现百叶窗放下来了一半,遮住了午后的光線。进门处还铺着一张小羊绒毯。也许强烈的光线和光秃的地板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不敢反抗,当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很顺从,完全被震慑住了,他才让氛围柔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