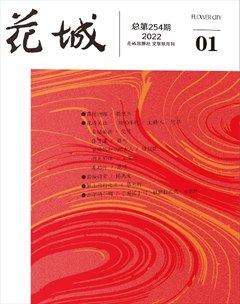访谈选自《英国穆斯林小说:当代作家访谈录》(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访谈集的作者是英国约克大学全球文学教授克莱尔·钱伯斯(Claire Chambers)。这个集子里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出自伊斯兰教信仰或文化背景,旅居英国,用英语创作,小说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受访者之一。采访话题涉及古尔纳早年从事写作的经历,文学创作主题,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对东非社会的反思,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家身份的定位,等。古尔纳强调文学写作的复杂性,不愿意将自己归入某种理论立场或流派,他的批判矛头不仅对外朝向前宗主国的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话语,更是对准了多民族、多种族地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思想偏见与社会隔阂。古尔纳尤其强调要警惕关于非洲性的本质主义话语,认为非洲人在既有的历史事实面前,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应当具有广阔的世界意识,以包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各种文化影响。
钱伯斯(以下简称“钱”):你能先从你写作中的迁徙和流离主题谈起吗?
古尔纳(以下简称“古”):我对移民流动不居的状态非常感兴趣。我对它有兴趣,并非因为它是远在天边的反常现象,而是因为它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当代世界的主导经验。我认为这种经验就是居住在一处,但在别处却有着自己的想象生活,甚至幻想生活。对那些只曾在自己国家境内迁徙的人来说,这也是可能的:你可以居住在伦敦,但在格拉斯哥过你想象中的生活。《离别的记忆》是我相当年轻那会儿写的,我试图描写主人公想离开的挫败感,只不过我当时并不想透露过多个人兴趣给读者。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孤立感,即使身在故乡也会产生的孤独感。不同地点、不同时代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赋予迁徙境况某种悲剧性。这种令人痛心的维度是不可避免的,它关乎失去,关乎遗憾:有些事情未完成,没做好,却难以补救。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常在这片区域四处翻找,目的是将移民经历的不同维度戏剧化,获得更深的理解。
钱:你关于迁徙、丧失,以及想象生活的论说令人想起萨尔曼·拉什迪《想象的故土》中的一句话:“过去是家园,却是失落的家园,位于失落的城里,位于失落时间的迷雾里。”这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描述你与桑给巴尔的关系?
古:拉什迪14岁就离开了印度,而我差不多18岁离开了桑给巴尔,所以他想象中的故土会比我的更加模糊。他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我想说,他14岁离开孟买相对富足的生活,进入英国公立学校,与我以成年非法移民的身份离开桑给巴尔,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桑给巴尔都是恐怖之地。我以为自己知道英国会有多么不同,但到了当地后的体验比我预期的更强烈。而且,我來得不是时候,那是1967—1968年,当时伊诺克·鲍威尔等人正在煽动关于“种族”的狂热情绪。移民问题似乎令人人惊惧。根据新闻报纸,伊迪·阿明①开始驱逐亚裔乌干达人,或强迫他们离开,因此,对数十万来到英国的外国人感到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很长时间思路才开始清晰起来。尽管我有自己的困难,但仍要应对将他人抛在身后的负罪感,因为我知道身处桑给巴尔有多么艰难。一旦开始不间断地思考,我就想看看关于桑给巴尔,自己还能记住多少,理解多少。这不是浅显的练习,而是需要全身心参与,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记不得了,但不得不虚构出来。当时的写作主要关于曾经的生活经历,“人们试图回忆过去”是我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还有一些问题一直盘踞我的内心,包括如何在不疏远读者的情况下书写悲剧,当然,还包括在一种语言和文化里如何再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沉默一直困扰着我。因此,最主要的活动不是回忆,而是与方法和形式有关的问题:你要讲述多少?你要压制多少?我能想到的任何读者,不管是英国人、毛利人还是非洲人,都会对我的读者有望知道的种种抱有期待:我希望人人都能读到我写的东西。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因,无疑对拉什迪也是一样,所以这一切不仅仅与记忆有关。
钱:既然提到了伊诺克·鲍威尔,你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你在20世纪60年代抵达英国的经历以及遭遇种族主义的早期经历?这些经历在以英国为重要背景的书中得到深入表现,比如《崇拜的沉默》和《朝圣者之路》。
古:我对很多关于种族主义的小说和电影都很熟悉,但我在想象中将它定位在某些地方,比如南非和美国各处。然而,到达英国时,我惊讶地发现种族主义是生活如此重要的部分,与它的相遇如此难以预料,又如此接连不断。种族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言语侮辱;通常它意味着更微妙的东西,比如侮辱的表情。很难解释这类反应有多么普遍、常见,多么始终如一。距离赋予你驳斥它的能力,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经常遇到人们在大街上对你大喊大叫,在教室里、工作岗位上、公共交通工具上辱骂你,它会让你疲惫不堪。
钱:你一直在使用过去时,可见,种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或改变了?
古:我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说不准。我想,这类事情有一些会落到你头上,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控制自己,如何或何时发怒。也许今天,一个身无分文的陌生人,来自不同的文化,就像当初的我一样笨拙,语言技能同样生涩,他仍然至少会经历一些我曾遭受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人朝你扔东西,紧拽你的衬衫或推搡你。但是,当人们的语调、言语或手势流露出怨恨、嘲笑或轻蔑时,我是知道的。我现在没有遇到这种暴力,但不相信它已经消失了。它还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延续着。
钱:回到拉什迪,你认为“《撒旦诗篇》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待穆斯林的方式的转折点?从1989年起,宗教和文化,与肤色相比,是否在种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了更显要的位置?
古: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过去文化和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肤色。有人会听到“巴基佬”这样的侮辱性词汇,但那些人谈论的不是“穆斯林”。我认为你是对的,“拉什迪事件”改变了这一点,尽管这可能只是这些问题上的第一次风波。由于2001年对美国的袭击和反恐战争,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无处不在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前,穆斯林“令人惊恐”,或是“恐怖分子”,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敌人”。这使得西方人将穆斯林视为危险和不稳定的人群时,毫无愧疚感。各种图片和新闻报道持续汇聚,不可避免地——即使以含蓄的方式——把穆斯林,显然激进的穆斯林——描绘成狂热或极端一族。这使得世人毫不顾忌地说出“他们又来这一出了”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