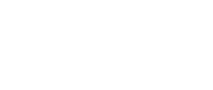1
黎明将近,天色由青入蓝,缀着疏星。
脚下,雪细如粉,头灯一照,闪动微观的虹,仿佛一层钻石粉末。雪鞋笨重,像踩着一双塑料船,走起来得两脚分开,一步一迈。
“看我们像不像两个圆规在走路?”
况子白了我一眼,“屁!”
我踹了他一脚,突然感到自由,没有女人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雪鞋走起来夸啦夸啦作响,登山包与滑雪板发出轻微而规律的摩擦声,脚下一停,就耳聋般寂静。眼前是最后一段陡坡,仰望:松树一根根陡立,剑指青天。况子把雪鞋后跟的搭扣撑起来,开始爬坡,我也照做了。一到户外,他总是喜欢做先锋,做领攀,给人开路,但那真不是走第一个那么简单,他每一步都要用体重压上去,一脚一坑,深雪吃进膝盖,像是在海水里迈步。
我跟了五十米,热得要炸。羽绒服里,汗水从腋窝滴下,沿着两肋滑,奇痒难忍。从领口里我闻到自己热烘烘的臭汗,想起每次打完球回家,桃子先是冲向我,又刹住,怔怔地盯住我,捂着鼻子,跑开。桃子妈的背影在厨房,一枚轻而冷的声音飘过来:快去洗。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想起这个,心里发紧。我卸下包,一把脱掉外套,只剩最后一件速干短袖。
“狗日的你显摆肌肉吗,冻死你。”况子又来了。
“关你屁事。”我干脆把短袖扒了下来,狠狠一拧,热汗滴在雪上,融出几个小坑。重新背上登山包的时候,背带像粗糙的冰块摩擦肩膀,鸡皮疙瘩一阵,虚脱般爽快。
不知何時天已发亮,我关掉头灯。剩下那段攀爬没花多久。登顶那一刻,太阳蹦了出来,云缝间横着几杠金光。天地澄明,远处的城市一片黯淡,像条大黑狗似的趴在山脚下睡。站在这高处,我俩忍不住号叫起来,野兽般快乐,大口呼吸,想把双肺漂染成一副天蓝色的帆。
风吹来,终于冷。我穿回衣服,拿出能量棒,喝水。况子在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看朝阳。四野白茫茫,粉雪雪道洁净无痕,又陡又窄,像一卷突然失手的卫生纸,一泻到底。世界化作一整山的海洛因,让人无法拒绝的上瘾。
喝完水,我俩眼神儿一碰:上。
2
德语里有个单词是Fernweh,指的是“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的思乡之情”。我心里那个地方是西伯利亚。读过一本书,《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法国记者、探险家西尔万·泰松写的,记录自己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小木屋里的半年生活。开篇,泰松描写他为隐居生活采购物资的时候,去到了超市,茫然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心中再次涌现对现代生活的厌恶:“十五个品种的番茄酱——这就是我想要逃离的世界。”
我不想用“逃离”这个词,我可是专门奔西伯利亚来的。从北京飞伊尔库茨克,两千六百公里,航班三个小时。从伊尔库茨克开到贝加尔湖,两百六十公里,却整整要花八个小时。车站破烂得仿佛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苏联风,一眼穿越回到童年县城。我查好了贝加尔湖的俄语怎样拼写,一笔一画描在纸上,去窗口买票。
几辆旧依维柯停在后院,车上没人,司机正在捯饬车尾行李舱,见了我,指了指副驾驶座位,竖起手指比出三,用力晃了晃。我不明白,也不想理会,就径直上车,选了个靠窗的座位。
车子出了站,却进城挨家挨户接人。韩国情侣,日本小子……各自站在旅馆门口,等车来接,搞半天只有我大老远跑到车站来……我感觉沮丧,一头贴在玻璃上,盯着外面的乘客。每人都有个大箱子,轮子陷进雪地,拖不动,撂在地上装傻。司机骂骂咧咧地把箱子拎起来,猛塞进后舱,依然朝着每个人比画数字三,依然没有人理会。
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人总算坐满了。出了城,车速快了起来,车窗上的水汽迅速结冰,比毛玻璃还毛玻璃,视野变成白内障。我这才明白过来:只有挡风玻璃不结冰,多交三百卢布,可以坐在副驾驶,看风景。但真正坐那座位的,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只能坐那儿,而且没见交钱。
我懊悔不迭,掏出纸巾擦窗,这才发现那不是雾水,是冰,纸巾擦半天,完全没用。一想到剩下八个小时就要这么白内障下去,我烦躁极了。睡不着,眼睛越过座位中间的走道,盯着挡风玻璃看——路面像一条黑胶带,把左右两半雪景草草粘起来,勉强凑成一张画面。色调硬冷,景色重复得几近静止——类似于早期拙劣的电子游戏背景,用简陋的相对位移来表示玩家在前进。
一阵刺啦刺啦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我回头看:众人东倒西歪昏睡,只有一个姑娘醒着,用一张银行卡刮车窗,冰屑纷纷掉落,玻璃上被生生刮出一块透明的、闪动着雪景的“相框”。阳光透进来,照亮她的睫毛和瞳孔,蜂蜜色的光晕。她大概二十多岁,亚洲脸,身旁的大概就是男友,时不时从对方耳朵里摘下音乐来听,俩人头凑在一起。我嗓子里涌出一股甜到齁似的酸闷,无端想象这姑娘和男朋友的种种画面,他们刚好上的那个月一连七天不下床的样子,结婚了以后是什么样子,有了孩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吵架,他们的分手。桃子妈在产房里挣扎的情景突然就又从黑箱里蹿出来了,撕心裂肺,号得我发软。当时我被巨大的焦虑和空白碾压,心脏堵在喉口,无法呼吸,伸手想安慰她,她却一把拽着我胳膊咬,疼得我身子一蜷,头撞在一个什么设备的角上。
没过几分钟,我再回头时,车窗“相框”又结了冰,风景消失。那姑娘像是决心要把风景从冰层中解救出来一般,又刮。孜孜不倦,车窗结冰多快,她就刮多快;好像非让这幅黑白照片在玻璃上保持显影不可。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说实话,那声音的确刺耳,惹得其他乘客纷纷侧目,而她男朋友就把那些目光顶回去,转头护着那姑娘,露出一种纵容的笑。
我被那刮玻璃的声音磨得莫名烦躁,越发觉得不可忍受……真想让她别刮了,拳头不自觉在捏紧……不,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七年后那个男友(要是还没分手的话)估计也会和我一样烦躁。用不了七年,三年吧。也可能一年。
不能再随便这么发火了……我努力放松拳头,闭上眼睛,想深呼吸,却只吸到车厢里的暖气,复杂的香臭抵消,混成一种闷人的浑浊。想来我跟桃子妈刚恋爱那会儿也新鲜过,好像也挺开心的,但具体是什么我忘了。婚礼特别累,吵了十吨架。临闹洞房前一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吹气球,分装巧克力糖。气枪给朋友了,我拿嘴吹,腮帮子酸,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尾,困得快要融化了。那一刻我特别想说要不咱们别结了,别弄了,何必呢,都走吧,让我睡个好觉。
婚礼况子没来,根本联系不上。挺遗憾,没来也好,以他那张嘴,估计我只有被拿来开涮的份儿。据说当天我困得在婚车上直打呵欠,闹洞房的时候整个人出神,反应慢半拍;幸好大家一通胡闹,像葱姜蒜辣子炝炒腐肉,什么味儿都掩盖过去了。司仪的话筒嗡嗡作响,不停啸叫,我站在台上差点打呵欠,拼命忍着不张嘴,眼泪一下子就憋出来了,大家都以为我是感动。
来客们动筷子了,我们开始挨桌敬酒,一桌接一桌起立坐下起立坐下。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人类发明这些破事儿来折磨自己有什么好处。我横了心把自己迅速灌醉,所以空腹一上来就猛喝,迫切躺平。大酒让我难受了三天,也被桃子妈数落了三天,说我整个人横着被抬上床,就直接吐枕头上,吐了两三天,不省人事,还哭,丢下一堆客人不管。我说行了行了都是我不好,反正没有下次了。
3
我知道贝加尔湖很大,但当况子说它有整个荷兰,或者整个比利时那么大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暗地里不相信。想Google一下,但手机没网。到了湖岸,信号就时有时无了。一片白茫茫中依稀冒出些破房顶,道路纯靠车辙辨认。我心想,到了盛夏,湖畔一定是尘土连天吧,路面连沥青都没铺。
村里跑着许多同款伏尔加牌面包车,纯苏联风格,灰色,老古董。柴油味儿呛人,人坐在里面抖得像全身都被上了抢救室除颤器。轮胎磨得没了纹路,但对付大雪游刃有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路上我就从没见俄罗斯人用雪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