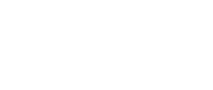一
作为一位作家的陈忠实,他的“自我”的觉醒,当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工作面临一个难题。
1976年3月,他在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无畏》,这篇小说给三十四岁的陈忠实带来了短暂的荣耀,但是紧接着,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变,“四人帮”覆灭,政治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因为这篇小说,陈忠实受到追查。尽管事后经多方查明,这篇小说的写作与“四人帮”毫无瓜葛,但因为事情在一段时间内被炒得沸沸扬扬,陈忠实还是受到了严重影响,被免掉了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副主任的职务也摇摇欲坠。
辞职,还是被免,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选择题。
1978年,陈忠实三十六岁,人生差不多过半。顾后瞻前,来路艰难,去路茫茫。他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进行了分析和谋划,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还是离开基层行政部门,放弃仕途,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从而皈依文学,真正全身心地进入文学领域。6月,他这个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在基本搞完灞河八里长的河堤工程之后,觉得已给家乡留了一份纪念物,7月他就申请调动工作。组织上经研究,安排他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抉择。从此,他告别仕途,转身成为作家,并且一步一步迈向他的文学远方。没有这次多少有点无奈的选择,陈忠实也许仍然蹒跚而行于那个荆棘之途,辽阔的《白鹿原》未必能进入他的视野。
算起来,到这一年,陈忠实已经在文学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了二十载。从1958年他十六岁时第一次在《西安日报》发表短诗《钢、粮颂》,到1965、1966年间在《西安晚报》发表快板词、散文和小故事,再到1973年至1976年间每年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其间既有处女作面世的快乐与憧憬,也有忽然不能写作、不敢写作的惊魂与疑问,还有短篇处女作《接班以后》被改编成电影、《无畏》登上国家大刊头条的春风得意与其后忽然面临的审查、撤职,陈忠实悲欣交集,文学、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以及種种疑问也缠绕着陈忠实,历经少年、青年,如今迫近中年,他必须重新思考,也必须选择。
仕途与文学,何去何从?
陈忠实出身于贫寒的农家,此前一直在农村的泥土中摸爬滚打,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仕途也是最实际的,而文学,多少有些虚幻,作为业余爱好,作为生活的点缀,倒也不失风雅,但要以之安身立命,不能不说有些冒险。更何况,最近的一次,陈忠实就是因为小说《无畏》而栽了跟头。文学可以“无畏”,现实令人生畏。
1978年,是一个历史悄然转变的年头。乍暖还寒,阴晴不定,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灞河落日,长夜寒星,陈忠实徘徊于灞河长堤,游走于白鹿原畔,南眺群山,西望长安,对自己的后半生重新丈量。
其实,1977年末,他就已敏锐地感受到新时代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到来的气息。这一年冬天,陈忠实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河堤,住在距河水不过五十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这个工房是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他和指挥部的同志就住在这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做垫子的集体床铺。大会战紧张而繁忙,陈忠实一天到晚奔忙在工地上。冬去春来,1978年到来了。站在灞河河堤会战工地四望,川原积雪融化,河面寒冰解冻,春汛汹汹。紧张的施工之余,陈忠实在麦秸铺上读了《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两篇短篇小说。第一篇是《窗口》,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作者莫伸,陕西业余作者,时为西安铁路局宝鸡东站装卸工人;第二篇是《班主任》,刊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小说栏头条,作者刘心武,北京业余作者,时为中学教师。莫伸比陈忠实年轻,刘心武与陈忠实同龄,两人都是当时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这两篇小说影响都很大,陈忠实读了,有三重心理感受:一是小说都很优美;二是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写作,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三是感到很振奋。特别是读了《班主任》,他的感受更复杂,也想得更多。当他阅读这篇万把字的小说时,竟然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陈忠实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文学的巨大风险。但他是真爱文学的,他对真正的文学也有感知力,真正的文学在表现生活和写人的过程中,那种对于现实和生活的思想穿透力量和强大的艺术感动力量,他也是有深切体会的。他本来是在麦秸铺上躺着阅读的,读罢却再也躺不住了。他在初春的河堤上走来走去,心中如春潮翻腾。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在陈忠实看来,《班主任》犹如春天的第一只燕子,衔来了文学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春的消息,寒冰开始“解冻”,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陈忠实望着灞河奔涌向前的春潮,明确地意识到,他的人生之路也应该重新调整了。
1978年10月,陈忠实开始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上班。这个时期的西安郊区含西安市城三区之外东南西北所有辖区,郊区政府所在地在西安南郊的小寨。郊区文化馆驻地也在小寨,其中一处办公地全是平房,在后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旁,院子里长满荒草。陈忠实图清静,就选择了这里。他从图书馆借来刚刚解禁的各种中外小说,从书店也买了一些刚刚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其中一些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他在破屋里从早读到晚,读到后来,兴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这是陈忠实一生中最专注最集中的一次阅读,历时三个月,他为此提前做了时间上的精心规划和安排。这也是他在认识到“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之后,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必要的艺术提高。陈忠实从《班主任》发表后得到的热烈反响中,清晰地感知到了文学创作复归艺术自身规律的趋势。他在这个时期冷静地反思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从喜欢文学的少年时期到能发表习作的青年时期,他整个都浸泡在“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之中,而“十七年文学”及其经验,此刻亟须认真反思了。尽管赵树理、刘绍棠、柳青等他喜欢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有迷人之处,但文学要跟上时代,特别是要走在时代的前沿甚至超越时代,写作者就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剥一层皮甚至几层皮。他认为,自己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而这个反思和提高的过程,最为得力的手段莫过于阅读。阅读对象很明确,那就是外国作家作品。与世界文学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这样才有可能排除意识里潜存的非文学因素,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深化、自我提升,是一个作家更新蝶变最为有效的途径。陈忠实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剥离”。剥腐离旧,“剥离”而后“寻找”,“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二
自1976年4月写成《无畏》(5月20日在《人民文学》第3期刊出),到1978年10月写出短篇小说《南北寨》,两年又半,除去三篇应景之作,陈忠实没有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一直处在痛苦和深刻的反省之中。与同时代从生活底层走出来的作家,如路遥、邹志安等人一样,陈忠实尽管当时还未踏入真正的文学之门,但他内心视文学为神圣事业;他对文学的追求左冲右突,因为时代的局限不得其门而入,但他却有圣徒的精神和意志。因此,当八十年代的精神曙光照亮古老的中国大地,他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他奋力向前,追赶时代,一方面要跟上时代,另一方面还要超越时代,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必讳言,陈忠实出身普通农家,只读了高中,早年受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颇深,就真正的文学创作而言,可以说他先天有所不足。陈忠实当年同时具有三个社会角色: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作家/业余作者。陈忠实说他时常陷于三种角色的“纠缠”中。分田到户后,他有疑虑,直至亲眼看到自家地里打下了多得出乎意料的麦子,这一夜他睡在打麦场上,却睡不着了,听着乡亲们面对丰收喜悦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①三种角色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视角不同:农民,是生活者;农村基层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者;作家/业余作者,则要对生活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更要有思想的穿透性和前瞻性。坦率地说,八十年代以前的陈忠实,思想者素质还相当薄弱。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对作家的思想者素质极其看重。对照陈忠实自述的在八十年代引起他产生“剥离”意识的生活現象,诸如原本看不顺眼的穿西服、着喇叭裤等世相,他当年要“剥离”的,第一是狭隘的农民的精神视野,或者说,不能仅仅以传统农业文明的意识看取生活,一个现代作家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都市视角和现代文明意识;第二要“剥离”的是政策执行者角色,这个角色是被动的和被支配的,容不得有自己的个性,特别是有自己的思考;第三,要“剥离”非文学的和伪文学的“文学观念”;第四,还要“剥离”诸如“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几十年来因袭下来的观念,这些是比生活世相“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旧观念可谓根深蒂固,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净尽的。无论如何,应该说陈忠实还是比较早地意识到“剥离”这个问题,而且“自觉”到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剥离”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觉今是而昨非”,这对很多人特别是作家来说是很难的。
一般的作家似乎只有“寻找”的过程,没有也不需要经历这个“剥离”过程。陈忠实为什么要“剥离”?从背景和经历看,陈忠实走上文学道路,先是因为自己的课余、业余爱好,后是因为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关文艺机构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而他受当时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早期创作大体上是沿着“讲话”的方向和“政策”的指导往前走的。这种创作,在当时的陈忠实看来,是因为喜爱文学而过一把“文字瘾”。他从模仿自己喜爱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政策的传声筒,要一变而成为具有独立思想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不经过“剥离”就不能脱胎换骨。“剥离”是一种思想上的“脱胎换骨”,某种程度也是情感上的“洗心革面”。陈忠实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② “艺术表述的能力”与文学禀赋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有关,而“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则无疑与作家的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有关。而这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的培育,对陈忠实个人来说,就非得经历“剥离”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可。陈忠实反思,他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里写了四篇小说,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和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息,当时颇得好评,《接班以后》还被改编为电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篇小说致命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用别人评价,陈忠实自己都看得很清楚——问题在思想,那是别人的思想、时代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自己只不过做了一回传声筒。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确实是一个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从过去的时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精神和心理上“剥离”与不“剥离”,对其后来创作格局与发展的作用,效果还真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作家,在五十年代写过一些颇获好评的歌颂“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文学作品,到了八十年代,面对时移世变,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还停留在当时的基点上,而且对新的东西一时还不习惯,接受不了,对现实失语,也就对历史和未来失语,很难再进行新的创作,只好写一写艺术技巧谈之类的文章。这说明,不是任谁都能“剥离”的,也不是任谁都愿意“剥离”的,更不是任谁都有这个必须“剥离”的思想自觉的。当然,“剥离”不“剥离”,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自觉和自愿选择,绝对不是所有作家都必须要走的一条必由之路。笔者和陈忠实闲谈得知,陈忠实对于有的作家在新时代面前不能适应和无法适应、思想和创作陷入进退两难,看得很清楚,他以这些作家为镜,反思,自审,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剥离”很有必要。
“剥离”不是完全放弃,而是坚持中有所更新,类似于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扬弃”。比如对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84年,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上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讨论和争论,就对他极有启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坚持,但现实主义必须丰富和更新,要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此后,陈忠实开始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位陕西作家是他的文学前辈,当年写农村题材获得全国声誉而且影响甚大,陈忠实视二人为自己创作上的老师。但是到了1984年,当他自觉地回顾甚至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接着说:“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