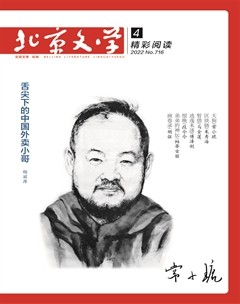晚上八点还出来吃自助火锅的女人,要么自暴自弃身材不打算要了,要么还精瘦,没到要死要活嚷着减肥的时候。李小梅属于后者,她三十八岁,该发福的年纪了,幸运的是偏偏不胖,吃啥都敢敞开肚皮,嘴巴享受了,肠胃也争气,能尽最大努力排泄出去,不给身体积攒多余的油脂。所以傍晚八点在宾馆前台办完入住,她拎着包直奔餐厅,先喂饱肚子再去房间。
餐厅是宾馆自带的,餐费可以在房费里结,按照规定标准,她作为科级干部在省城住一晚最高报销上限三百五十元。今晚运气好,还有普通标间,房费离三百五还差几十,足够她吃顿晚饭。晚饭只有自助火锅,还好她挺喜欢吃火锅的。
自助大厅里几乎满座了。八九根方形大柱子撑起来的空间里,几十张火锅桌子不远不近距离恰当地摆开。桌面上已经升腾着团团热气,气息迷蒙,桌椅似乎都是活的,无数的木腿在蠕蠕地乱动。细看,自然不是桌椅动,是桌前和椅子上的人。人坐的站的走的,吃的喝的交谈的,形态各异,吃相热火。李小梅目光满场游,找心仪的空座。最好一个人坐张桌子。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和某个同性拼桌。没有同性,异性也可以。最不理想的是,和某个家庭或者一群狐朋狗友挤一张桌子。这种情况的话她就等于落单了,像一个并不合卯的楔子,被硬生生塞进了别人围拢起来的一个空间。自然是不受欢迎的,要么自己别扭,要么别人别扭。尤其那种家庭聚餐式的一桌人,加进去一个外人,纯粹就是破坏人家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会搞得像个插足的第三者一样不受欢迎。
目光游走,绕过一桌又一桌,问了几个有空缺的桌子,都被告知已经有人。她有些累,似乎被这样热烘烘的蒸汽熏着,肠胃被饥饿感唤醒了,迫不及待地想拥有一个座位,坐下来往嘴里填塞一些食物。终于锁定一张空桌,六座的,只在边角上坐了位老妇人。李小梅无比欢喜,迎着老妇人笑,把包放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哎,有人哩!”老妇人一个手伸出来摆着,神色间透着说不清的意味,“俺们一家子!”
李小梅赶紧走人,似乎不走就要被裹挟进一个陌生家庭的某种凌乱和排斥气氛当中去。老妇人一听口音就是北边川区人。李小梅是从南部山区来的,说不清为什么,她听到北边口音就心里紧张。老妇人的调门又快又高,增强了一种嫌弃的效果。
李小梅有种和人吵架落了下风落荒而逃的仓皇。她又在桌椅和人流间辗转了几步,心里忽然很沮丧,滋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念头里甚至夹杂了一丝委屈,一些跟谁赌气的冲动,没座,没合适的座,那就不吃了,一顿不吃也饿不死人!
活了半辈子了,每天忙碌的事情,不就是忙着为自己找座儿吗?找一个可以暂时停止脚步,坐下来歇歇,吃口热饭喝口热汤的座儿;找一个可以搁置身体,喘口气,缓释一下疲劳的座儿。小时候在家里,一家亲情骨肉之间何尝不是彼此的座儿,尤其孩提时代,依靠着父母亲情的座儿才有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后来拼命念书,找的是一个可以挣取工资换取衣食的座儿。有些座是长远,有些则是短暂。她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座,让她安身,完成一顿晚饭,所以这个座儿短暂、临时,却为什么非得希望这临时和短暂也能尽可能地完美?人生真是处处都有自己为自己预设的苛刻和责难!
被一种奇怪的情绪牵引,她真的向门口走去。门左是厅内就餐区,门右是后厨区。她目光里衔着越来越浓郁的热雾,忍着心里的不甘——人就是这样奇怪,这顿饭不吃的话,也不会十分地饿,可来了却吃不成,空着肚子离开,这感觉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好像亏欠的不仅仅是一顿火锅,还有更多的遗憾。满眼都是敞开了大吃大喝的同类,高级动物在用低级动物的尸体和植物的果实枝叶及油脂填塞自己的胃口,样子贪婪、丑陋、残忍。她不敢细想,用流行语讲,这件事细思极恐。在恐惧面前,人只有一个愿望,渴望融入,和眼前大快朵颐的同类站到一起,成为他们队伍里的一员。只有这样了才能暂时忘却某种道德的谴责。她迅速降低了要求,只要有个座儿就行,和谁拼桌都一样。
标准降下来,选择余地就宽了。她看到有空位。是个老头独坐。还有个胖子独坐。她没选,转身又往里走,远远看到最靠后厨那里有座。那里是出锅口,人流多。她本来不想去,看到一个小伙子已经坐下了,在点锅,要一个麻辣锅。李小梅断定他一个人。四个座,目前只坐他一个,她走向那个卡桌。最合适的位置是他对面。相对而坐,距离恰当,互不干扰,各吃各的。刚刚好。果然,他只抬头看了李小梅一眼,没有说这桌已经有人的话。
李小梅放下包,点了锅,去拿菜。菜品挺丰富的,看着也新鲜。面对两排摆满了食材的架子,李小梅忽然恍惚,拿什么,吃什么,什么是自己需要的,面前一下子出现太多的选择余地,选择本身反倒成了难题。她想到了七岁时候的一个生日。那时候她还在一个叫桃花咀的山村里做村姑。小村姑盼啊盼,盼来了自己的生日。按情理,这天她可以跟大人提一个要求,让他们无条件兑现。这一天母亲把她带到了人间,她是应该被宠爱一次的,既是母难日,也是她本人的纪念日。她提出要吃一个煮鸡蛋。这要求放在今天的话,还算一个要求吗?
李小梅的目光在一堆蛋类上踟蹰,据说这是鹌鹑蛋。吃火锅惯用鹌鹑蛋,没见过用鸡蛋鹅蛋鸭蛋的。如今的人,都吃得饱,轻易不会尝到挨饿的滋味。也就没人会蠢乎乎煮一个大肥鸡鸭鹅蛋蘸着芝麻酱吃吧,都吃得讲究了,精巧、细致。比如蛋类,就选的是这小巧玲珑的鹌鹑蛋。在她的童年当中,尚不知道世上有鹌鹑蛋。那一天她一心渴望吃到一枚煮鸡蛋。她跟着母亲转出转进,从麦场到院子,从院子到厨房,母亲忙完了农活儿又忙着做饭,出出进进,一刻不停,她小小的身影陪伴着母亲,她嘴里嘟嘟囔囔提着一个要求,鸡蛋,鸡蛋,妈我要一个煮鸡蛋。直到晚饭结束,上炕睡觉,她都没得到一枚煮熟的鸡蛋。因为她家那只母鸡那天没下蛋。她家里也没有储存的鸡蛋。七岁的生日就那么过去了。一个空荡荡的日子,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其余的生日都得到了满足。被满足的生日反倒没什么记忆了,只有那一个有遗憾的日子,成了最难忘的。
人就是这么有意思吧。她轻轻笑笑,捡了几枚蛋。鹌鹑该有多小呢?下出了这样让人心疼的蛋。一枚蛋原本该是一个生命,一只小鹌鹑。但填了人的口腹,人就是这样残忍。她懷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走回桌子。
对面的青年刚拿了菜回来,他的锅开了。他一口气下了四盘肉:两盘牛肉、两盘羊肉。牛肉红,羊肉白,肉一下去,沸腾而起的蒸汽里有了荤腥感。是个好男人。李小梅淡漠地想。男人就应该能吃肉,在肉面前不怯场。她有个大口吃肉的男人。他就宣称过,不吃肉的男人不是真男人,似乎雄性的符号,由胃囊里每次能塞进去的动物尸体来衡量。李小梅和他吃自助火锅的话,每次都有罪恶感,因为他一个人吃掉的是三四个人的肉量,还必须是精瘦的牛羊肉。如果仔细算账的话,他连李小梅这份价也给吃回来了。老板躲在后面哭呢。李小梅心里这样调侃他。李小梅不吃牛羊肉,她啃鸭爪鸡爪,吃点鸡胗,再煮点海鲜,看似忙碌不停,其实吃进肚子的肉量不多。
这家店有一款香辣鸭爪,她吃了一次就忘不了了。只要来,首先必吃。她端了满满一碟鸭爪,一坐下就赶紧啃起来。又辣又香,烂熟到松软的胶质,挂在薄脆的骨节上,口舌都不用使劲,靠口腔软组织吸吮,那层胶质就纷纷滑落,犒劳着触觉和味觉,滑向食道,跑向胃囊。美味到让人有犯罪感,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罪恶感是如此享受。得抓紧吃,争取再拿一盘。是拼桌,又是陌生人,用不着维护形象,更没必要矜持,她就是个消灭起鸭爪爪没节操的女汉子,雌性饕餮之徒。该庆幸在没桌的那一刻没有真的打了退堂鼓,一顿火锅不想吃没什么,错过了这盘香辣享受多可惜。目光无意扫到了对面,看见对面的人也在啃爪子。锅里的热浪在咕嘟咕嘟翻腾,肉从浅粉变成深棕,又变成褐色,形状从舒展的片,缩皱成团、串、疙瘩,一锅奶白的汤因为血沫子显得浑浊——让人兴奋欢快的那种浑浊。你得承认,人是有嗜血欲望的,只不过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是用道德感和社会公责压制了这层欲望。或者,用既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遮掩自己的残忍。杀了动物,把尸体吃出各种花样。这由整体到肢解,由生到熟的过程,难道不是一个嗜血残忍的过程?
有一天宇宙中某一个种类的动物,忽然强大起来,反过来以人类为食物,它们把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挂在肉架子上,开膛扒肚剔骨切块,煮炒煎炸涮,孜然花椒大料精盐酱油醋,它们把人皮熬胶,人血煮粉,人肉切片,人胃入药,最后把脑袋敲开拿馒头蘸热脑浆吃……李小梅差点吐出来。怎么能有这样恶心的念头呢?自己不也是一个肉食者。
为了惩罚自己既吃肉又可怜同情被自己吃肉的动物,她恶狠狠撅着鸭爪骨。对面的男人有点女气,他居然也啃鸭爪爪。他虽然煮了一锅肉,却还是啃爪爪。看来不是真男人,是个细皮嫩肉的小男人。她有些微微的醉意。前台有啤酒免费提供,她不喝酒,她喝了一罐果啤。一小罐果啤,她就想醉。她为自己忽然滋生的矫情好笑。她就淡淡地俏皮地笑着,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借着一直升腾四散的蒸汽,她眯缝了几次眼睛,看清楚了,確定没见过,不认识。却还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是他长得大众吧,和时代很契合的外貌。与茫茫人海很协调,融入其中,气氛融洽。就这样。
餐厅里挤满了人。回头看窗外,夜色早就被各色灯火取代。餐厅的灯光不是纯粹的明亮,被你轻易不能察觉的花式装饰了。有些温馨,有些暧昧,好像在为人类共同在这里犯罪而作掩饰。她记得儿子爱看的动画片里有一家狼,先生灰太狼,为了讨好太太红太狼,动不动来个烛光晚餐,准备吃掉刚抓来的某一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