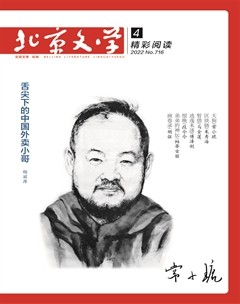那天黄昏他在彩虹湾海滩新建的栈道上跑步。雨后初晴,一道彩虹如约而至般横跨在一碧如洗的海空中。空气本来就新鲜,现在加上了一点紫荆花的香气,就更好闻了。栈道上有许多人跑步,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啊,他太喜欢这座海岛城市了。
手机响。他站住。还是那个用伪装的娇声掩饰自己实际年龄的女客服,提醒他一直等待的快递到了。海湾距离他家所在的小区不远,他回话说马上回去,五分钟就到。结果不到四分半钟他就跑回了小区楼下的单元门前,却没有她/它。再打电话说她/它已经自己乘电梯上了楼。他没有多想就进门上了十八楼。她果然就站在他家门前等着他呢,一身很休闲的夏日女装,用心地化了妆。最初他吃了一惊,以为她就是这个季节来海岛度假的女子,走错门了才出现在这里。但忽然就想起来了:她就是它!
“啊,你就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他说,有点语无伦次,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和不适应瞬间出现在了脸上。“不过你好像是有名字的,你叫……”
“安娜、安吉尔、安妮、美智子,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翠花。电视里常喊一句:‘翠花,上酸菜!’那也是我!”她/它用一种这些天来他已经熟悉的腔调笑着回答,笑容里有一点媚。
不过对于这一层他也不会感到惊奇啦。一直和他联系的这家“幸福伴侣”服务公司的客服也许和她一样是个女性机器人,跟眼下这个她/它共用一个公司通用的故作年轻且有一点嗲的女声。
都是被一本名叫《区块链》的书闹的。书的作者是他的一位同学,书写得艰难,出得更不容易,所以书能够成功出版并意外地成了畅销书让作者感到十分兴奋,加上他们俩的关系,在大学宿舍里睡上下铺,不寄一本给他分享自己的智力成果和运气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能全怪老狐——应当叫老胡,但叫惯了,就是作者本人——说实话他自己对区块链这个早就热起来的新词也有一点儿向往。区块链,区块链,听起来好像就很高大上一般,他虽然并不热衷于赶时髦,但这些时髦的名词开始影响到你的生活时当然还是要熟悉一下,不然自己的生活就可能陷于某种程度的不方便啦。早就是信息时代了,对于区块链这样的新词,连同它标志的人类新的生命活动,你可以置之不理,却不能不懂得,那就信息不对称,麻烦大了。
他用一个星期天时间读完了那本书,只感觉到了失望。放下书后他最后一次向窗外眺望,以便让疲劳的眼睛休息一下。那时就想到了:什么区块链,还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其实不是,人类社会本身早就是区块链式的了。按照老狐在书上的描述,从科技层面看,区块链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等一众科学和技术问题。从应用视角简单来说,区块链就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等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保证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为区块链创造信任奠定了基础。照着老狐的说话,区块链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因为它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点对点的信任、协作与行动。可难道这是什么新鲜事物吗?人类早就并且一直都在进行点对点的联络,最直观的是互联网,尤其是网购,早就是区块链式的了。这么个新名词,真的不算什么。
现在想起来,老狐的这本书还是改变了他的生活。区块链,区块链,有一阵子他醒着、梦中都在不知不觉念叨它,原因是对这本书的阅读也鼓励了他跃跃欲试地进入一种眼下可以称作“他自己的区块链”的生活,而这样一种在过去很少发生的“区块链式的冒险”居然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
一个月前下的单。当时就后悔,想取消订单。可是晚了一小时,对方的客服就用这个他逐渐熟悉的女声说,单已经下到工厂啦,产品按客户的特殊要求进入了生产线,即使要退单,也要等收到货后以“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方式取消此次网购。“放心吧先生,我们不会为难您的。这些天你可以再想一想,也许你又回心转意了呢,这可是敝公司本年度的最新产品呢。”还是那个假装年轻、有一点嗲和娇羞的女声,这样安慰他说。
而他又是那种天生的软心肠,好人,心想既然人家都为了他的冲动投入了原材料和各种劳动,又没有拒绝他退货的请求,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加上老狐书中真有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譬如 “你不加入区块链,你就没有进入今天的生活”。这话当然说得有点严重,但并不是说就没对他的心理产生作用。一个月后,他差不多都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她/它,就直接站到了自家的门前。
他本来想说一句“既然来了,就请进吧”。可是,鬼使神差一般,他说出了另一句话:
“我……这会儿还能退货吗?”
“当然。”那个仍然用一种客服女机器人的娇声——现在又加上了一直浮在年轻的脸颊上的笑容——同他说话的客人马上回答他道:“不过,既然我都到了你家门前了,出于待客之道,总还是应当让我进去坐一坐吧。大老远地从浙江来到这里,千山万水的,我也不容易呢。”
这哪里还是一个它,分明就是一个……一个……是那个一直在电话里同他联络的女客服本人的声音!
“很冒昧地问一句,如果唐突了请您原谅。”他咳嗽了一声,让自己镇静一些,“你真是一个——不,一位——能在一个家庭里承担起妻子的全部责任的最新型女性机器人吗?要不你是朋友们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是一个人?”
这话问得够蠢的,不过他不后悔。说完了就注意地盯住她,观察她的反应。无论科技发展到了何种地步,机器人和真人他应当还是能一眼就能从细枝末节处看出差别的。
她冲她嫣然一笑:“如果我是,你是欢迎呢,还是不欢迎呢?”她没有选择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却回头狡猾地将一个難题抛给了他。
“啊,如果你是,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刚才跟你说,有朋友跟我开玩笑,是我在试探你。事实上我网购一件女机器人做妻子的事,除了贵公司负责和我联络的那位客服——也许她还是一个机器人呢——在这座海岛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除非贵公司出于各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泄露了我的隐私。”
她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纯粹因为年轻才显得好看的笑容仍在。他觉得她走神了,这么想着,他更觉得他的猜测不错,她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眼下他也有工夫仔细地瞅她一眼了。一言以蔽之,是一位形象介于美和丑之间、却又两边都不靠的普通女子,刚才他觉得她年轻,是因为她可能刻意地化了妆,当然也不算老,但年龄过了三十应当没错。中等身材,有点腰但是不多。他想人们常以为女人好看全在一张脸上,错了,女人好不好看全在有没有腰。不过还好,她有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尽管她化了妆他仍然能看出来),五官也还算整齐,这解了他的谜:为什么一开始会觉得她显得年轻。就是这样一张圆圆的白净的娃娃脸,加上那一点腰,还有脸上始终挂着的青春的笑容,给她的整体形象加了分。
“我就是一个假机器女人,真女人,您就不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坐一下吗?我刚才说过了,走了这么远,千山万水,还过了海,车马劳顿,我真的很累,腿都站不住了。”
其实他不想开门,这是一个骗局——虽然他不怕,手段恶劣而笨拙,显得可笑,没有技术含量——更不想让这个想都想不到的骗局继续往下发展,但订货时他是付了全款给这个“幸福伴侣”公司的。如果她是个活人,甚至——他已经在这么想了——她就是那个每天用一种虚假的娇声骗她的女客服乃至于女老板本人,他还是需要和她坐下来谈一谈退款问题的。
老狐——他又想起了他的那个同学,和他写的那本倒霉的书,现在他认为都是他和这本书闹得他一时昏了头。等事情都过去了,他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那位同学,痛骂他一顿,搞的是什么?让他原本好好的生活平生出这么一番波澜,上当受骗都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太丢人。
加倍索赔就算了。他不是一个喜欢在这种事情上较真的男人。一边走过去用指纹开门锁,他一边顺着刚才的思路想下去。还有一种情况呢,她既不是“幸福伴侣”公司那么知名的企业的女客服,更不是公司的女老板,最有可能是某个小地方自愿加盟的分销商,而他也可能是她的头一个客户。
门开了。他尽可能最大幅度地让门敞开着,回头看她道:“进来吧,骗子。”
她有点自知有错似的、羞羞答答地低头笑着走进门,忽然抬头瞧他一眼,笑容再次自然地浮现在眼眉间,问:
“咱家在哪儿换鞋?”
进门就是玄关。身后放鞋的柜子被他挡住了。他让开,让她看得见。但她使用的那个词儿——咱家——让他警惕。她/它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人还没进门,就冒充起一家人来了。
“好漂亮的家具。”她欢喜地叫起来,真到了自己的新家一样,“这么小巧的玄关鞋柜,阿拉那儿就勿。”
当年在内陆城市就职,公司有个家在浙东沿海地区的同事,他知道“勿”大致就是无、不、没有的意思,阿拉嘛上海人也说,这个他懂。
她不用手就麻利地褪掉了脚上那双显然是新买的带着银白色配饰的小皮鞋,赤着脚走进了他刚刚擦洗得一尘不染的客厅。他的收入有限,这间出租公寓面积不大,但客厅不小。她就那样赤着脚在显得宽敞的客厅地面上走来走去,满心满眼都是欢喜。
“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一看就是在等我来,想在头一天给我一个好印象。”她说。不等他回答,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了一聲“哎呀”,“侬瞧阿拉全忘掉了,今天是阿拉上门来做媳妇的头一天,我们应当算是新婚。公司免费赠送了两张大双喜字,让阿拉带了来。侬不用忙,阿拉这会儿自己来贴。哎对了,我们成亲不用侬花销得太多,它本来就是阿拉和侬两个人的事体,我们自己悄悄地庆祝一下就得啦。”
他眼睁睁地看着她一边自说自话,一边真的从随身带的小巧的白色仿麂皮坤包里取出了两张大红喜字,还是那种背面带胶的,取下塑料膜直接粘到墙上就行。她自作主张,一张贴在厅里,谁都看得到的地方,一张直接贴到了公寓仅有的一间卧室的门上。然后回头,拍拍手笑道:
“好看伐?真是一团喜气。其实我还带来了婚纱呢,在那个行李箱里。”
现在他才回头看到进门时她随手拉进来的那个粉色的大大的行李箱。它就安静地直立在她方才随手关上的屋门的后面,仿佛也是一个活物,如果主人不欢迎,随时准备转身自动走出门去似的。
“啊,请吧。”他让自己平静。不,其实他觉得一直都还算平静,“我们坐下来谈谈。”
她有点拘谨地在他对面的单人小沙发上斜侧着坐下来,目光从下向上乜视着他。看得出来,她其实是有点怕他——怕他说出那句立马将她赶出家门的话。
“你看啊,无论你叫安娜、安吉尔、安妮还是美智子、翠花,什么都成,我不知道你身份证上的名字,不过这会儿我也不想知道了。”一边说他一边重新走回去重新打开屋门,目的就是让它能够大敞着,“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原因,这个我也不想知道,但是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眼下我们之间只剩下一个问题,说‘退货退款’就显得不好听了,其实就一件事,你回去就把钱给我打回来,这件事就过去了。你看这样处理行吗?”
“行。”她很痛快地回答,一边就站起来,笑容消失了,目光幽怨地看他一眼,并且也不说家乡话了(现在他想起来那是宁波话)。“可是今天也太晚了,我没有带钱的功能,银行也不给机器人发信用卡,没有主人携带酒店也不让我住进去。好歹你这里也宽敞,你这个人是透明的,我一眼就能看透,你也没有一颗冷酷无情的心。我本来是欢天喜地来做你的妻子,可是你瞧,我成了一个流落远方无家可归的女子了。”
“打住。可以了。让你处在这种不幸的境遇里,我深表同情,但应当承担责任的那个人不是我。尽管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伪装成一个机器人而且接了我的单,但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也并不想为它给我带来的麻烦追究什么人的责任。”他没有往下说自己当初为什么要下一个这样的订单,啊,他一直都认为自己在当今社会里是个保守的人,他先是从红尘滚滚的内陆一线城市搬到这座海岛,接着又从一家日进斗金的证券公司自愿转行,进了城郊接合部的一所普通中学当物理教师,要的都仅仅是自己想要的那一种恬淡、没有太多世俗和心理压力的人生。当然,哪怕是到了岛上后,他也不是没有遇上过心仪或者心仪于他的姑娘,但是一想到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结婚都要买房子、置车子,婚前婚后一应的鸡零狗碎,他那个心情就没有了。“我还是长话短说吧,眼下我们之间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善后。你要是身上真的没带钱我可以送你去附近的酒店住一晚,明天你就可以回家乡去。你甚至都可以不把我的货款退给我,但你知道我只是一名中学老师,收入不高,那笔钱是我几年来的全部积蓄。”
“既然你为我花光了全部的钱,那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留下来呢?我不想冒犯你,可是对你来说,我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真女人,还是个可以承担起妻子责任的女机器人真有很大差别吗?再说我一个女孩子,尽管长得不像七仙女,可你也不是董永呀,你就花那么一点钱,我就凭空而降地到了你家里,你差不多就算是白捡了一个媳妇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