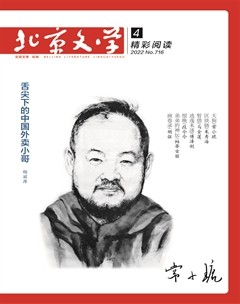一
五十多岁的晏瑞丹,不显胖,短发,端庄,干练。她退休时,距她老公退休还有半年,本来说好,等老公贺天顺退休后,再举家迁往省城,而晏瑞丹改变主意,迫不及待,提出带母亲先到省城。贺天顺嘀咕,不就半年时间吗,咋就这么急?
晏瑞丹一脸愁容地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在这里,她用了“忍受”这个词,可想而知,她的忍耐到了极限。
在别人看来,晏瑞丹的苦恼,芝麻大点事,不就是不习惯关河一带的习俗吗,怎么不能忍受了?贺天顺认为老婆矫情,而从省城嫁到关河的晏瑞丹,自有她的苦衷,其他不说,单就赶人亲的事,就让她头疼了三十年。
赶人亲,是关河一带的习俗。关河县地处峡谷,县城在悬崖上,因没平地建房,所以县城很小,人口也不多,不管红白喜事,只要告示往几个路口一贴,全县城人都知道。不论哪家哪户,只要“出事”,人们都会上门送礼钱,两百三百不等,五百一千不限,没底线,也不封顶,除了特殊关系,一般礼钱在三五百之间,按市场经济的话说,这是时下行情。单看这个数字,并不大,而问题是,这样的事,几乎每周就有一次,像晏瑞丹这样的工薪阶层,倒没啥,毕竟每月几千元收入,没有收入的百姓就难了。
下河街的李在贵,有名的困难户,家徒四壁都说不上,压根儿没四壁,租房过日子。早年娶妻生女,因为穷,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女,那以后,他没再娶,有人说他不是不想娶,而是娶不起。他赡老哺幼,老母的病,把他拖穷了,时不时住院,打针吃药都要钱,女儿二十一岁时,远嫁外地,剩下他和老娘过日子。日子好像不是用来过的,而是用来背的,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体形弯曲,身子骨越来越小,风霜雪雨一把刀,他被刻成一副木讷表情,即使置身热闹和感天动地的场面,他也没表情,更不言语。
当时,晏瑞丹在镇民政所工作,负责发放低保。那次发低保时,李在贵倒干脆,左手进,右手出,赶了人亲。晏瑞丹问他:“把钱送出去了,怎么过日子?”李在贵叹了口,说:“不赶人亲,更难过日子。”经他进一步说明,她明白了他的苦衷,其实人人都有苦衷。所以是低保,就是保你每天吃上大白菜,并不保你赶人亲,而低保人家,再艰难,就是勒紧裤腰带,少吃两口,也要把人亲钱送出去。
赶人亲,成为关河著名的社会活动,是一张千丝万缕的网,谁要离开这张网,谁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话又说回来,谁家没个事啊,你不送人,人不送你,礼尚往来,才是生存的世道王法,所以,辛苦挣来的钱,主要不是用于生活,而是用于赶人亲。
日子久了,人们从中悟出一些道道,有人想方设法“办事”,可总不能今天娶亲明天死人吧?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脑筋一转,就从红白两事中,衍生出寿宴、生日宴、升学宴、当兵宴和店铺开张宴,如此种种,如雨后春笋。
酒席办在餐馆,也倒省事,而县城关河镇的风俗是自办。关河镇主要就一条大街,分上、中、下三段,憋着一泡尿就能来回,一支烟工夫就能走通街子。因找不到像样的平地,各种宴事,只能在大街上操办,这样的热闹隔三岔五,每次要吃上三天,整条街子像过节,人们相互帮忙,为了需要,还自发成立了助协会,购置了锅碗瓢盆和桌凳,为各种酒饭提供所需。
成立之初,李在贵在助协会帮忙,端碗洗菜刷盘子,样样都干,不时把碗掉到地上,负责人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家当,你砸了,我们靠什么维持?后来就有了规定,谁碎了碗谁赔,所以,李在贵每次可怜的一点报酬,都会被扣除一些。他经常发愣,也不随和,没人喜欢他木讷的样子。
或许李在贵并不愚钝,人情世故,全在他心里,世间万物,全在他眼中,难说,他心里住着一个活络的世界。
不久,李在贵的母亲病逝,为母亲办完后事,他就离开助协会,再没租房,住进关河边的岩洞,也再没赶人亲,彻底“淡出江湖,归隐山水”,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过上了清静的避世生活。
李在贵,地地道道的关河人,连他都怕的人亲事,何况外来媳妇晏瑞丹,她的恐惧,理所应当,她的逃避,理直气壮。而晏瑞丹都退休了,还等什么呢,一个字,逃,两个字,快逃,李在贵逃进岩洞,自己可以逃到省城呀,一样一样的。
二
关河县人,无论自由职业,还是退休职工,凡有能力的,即使没有能力的,筹款借钱也在所不惜,纷纷到省城买房,就像当年的有志之士,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有的是候鸟迁徙,有的是飞鸟归巢,总之,都不约而同选择城北片区。这个方位的选择,估计和乡情有关。关河县在省城以北,住这里,回乡方便,不必穿城过市,启程,便是回乡之路。
关河人囤聚的省城北,被人们俗称关城,一个关字,就连接了故乡。
晏瑞丹的房子,自然买在关城片区。半年后,她老公贺天顺退休,也自然落脚省城。毕竟,贺天顺是关河县县长,他的到来,在关城的江湖中,激起了一点波澜。彭东风设宴为他接风洗尘,总之,那天该到的都到了,全是关城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省城谋事的关河人,有关河籍的企业家,也有关河县退休的头头脑脑,名义上为贺天顺接风,实际上,彭东风顺便联络了社会关系。
彭东风是贺有顺的表侄,在生意场摸爬滚打多年,他眼睛不大,却眨着智慧,个子不高,却透着能量,他是道中人,这种场合,请谁不请谁,心中自然有数,满满三桌人,气氛沸腾。
那天,贺天顺一出现,众人起座,握手和寒暄必不可少,笑,自然或不自然地堆在每个人脸上。西装革履的他,浓眉大眼,国字形脸,透着浩然正气,并气宇轩昂,眉宇间荡着忧国忧民的思绪,熟悉他的人,都称这副面孔为关河县标志性表情,写着高大上的正能量。
仿佛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全中国的酒桌上,几乎都讲同样的话,祝福的话必不可少,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谢谢两字,谢谢栽培,谢谢关照,那晚也不例外,只因賀县长的到来,欢迎二字免不了成为热词,总之,都是受用的好话。
必要的礼节过后,人们的热情转到邱处长身上。邱处长一身西装,还打了领带,总是一脸儒雅和笑容。大家举着酒杯,轮番到他面前,各种祝词和套近乎的话,烫得灼人,欢迎贺县长的主题,由此变了调,贺县长心里略有不爽,不过,一定程度上,他也能理解,毕竟邱处长非同一般,虽说只是个处长,却神通广大。
饭局到了最后,大家才知道,邱处这伙计,带了私活,他从包里掏出一摞红纸卡,向大家一一发放,脸上也像红纸卡一样喜气,彭东风接过一看,原来是他女儿的结婚请柬,彭东风心里嘀咕,这老兄挑水带洗菜,啥都没落下。
大家再次围拢邱处,“恭喜”之声,像炮竹一样响起,酒气中浮起喜气,饭局绽出一个新高潮。
待气氛缓和下来,彭东风走近贺天顺,低声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去足疗和按摩。见贺天顺摇头,彭东风就说换一个地方休闲一下。贺天顺心想,初来乍到,熟悉一下环境也好,就换吧。邱处和大多数人称有事离去,贺天顺像个不谙世事的新人,跟彭东风来到关城休闲会所。会所设有餐饮、健身、足疗按摩、卡拉OK和棋牌室,项目多,环境也不错。老板姓齐,也是关河人。
贺天顺刚下车,齐老板迎上去握手,必不可少的寒暄后,齐老板带他们里里外外溜了一圈,指着闲置的健身器和按摩床椅,说,基本没人弄那些玩意儿,下一步调整格局,全部用于棋牌。说着,棋牌室就到了,只见灯火通明,麻将声和说话声,此起彼伏,全是关河县口音,像一锅爆炒的豆子,大多是贺天顺熟悉的面孔,恍惚间,他还以为在关河呢,他不便一一招呼,刚想绕开,就有人叫了一声贺县长,可能因为称呼特殊,忙碌的人们停下来,目光齐刷刷地聚到贺天顺身上。
“县长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大家欢迎。”
“贺县长来两圈,码长城,这是爱国呀,呵呵。”
贺天顺目不斜视,一身正气地向大家点头致意,说自己退了,已经不是县长了。“退了也是县长。”人们议论起来,贺天顺略有不自在,边走边说不打扰了,就离开了麻将室。彭东风感叹地说:“人之所需,供不应求啊,麻将室再扩大几倍,也会座无虚席,京剧、国画、中药和武术,跟我们的生活没关系,麻将才是真正的国粹,和我们的生活骨头连着筋,没有它,很多人活不成。”
齐老板笑着说:“彭总说得极是,有人整天在麻将室,其实他们玩得都不大,输赢一般一兩百元。只有几桌打得大一些,一天下来,输赢几千上万。”
几个人边说话,边拐进一个院落,吵闹声被隔在门处。院子不大,却清静,齐老板推开一间房门,里面只有一张自动麻将桌,却空无一人。齐老板说那是贵宾室,贵宾们不来也留着。彭东风凑近贺天顺耳边说,那是邱处和钱总他们的专桌,有人管这叫待遇。
“钱总?那个放高利贷发财的钱禄丰?”贺天顺问。
“正是,约了他,他在外地,他的钱九位数了,是关河人的超级偶像。”彭东风表情夸张地说。
贺天顺的国字脸,皱了一下眉头,说:“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他成为偶像是正常的,就连我都觉得他是个奇迹。”
如今的麻将,名义上是休闲,实际上就一个赌字,刚退下来的县长贺天顺,对这个字很敏感,他下意识地加快步子,齐老板跟随其后,边走边说:“刚才邱处来电说,钱总出差刚回来,他们在绿洲洗浴场,叫我过去,我哪走得开呀。”
邱处刚才不是说有急事吗,怎么桑拿去了?贺天顺心里嘀咕。看贺县长要走,齐老板送上一盒上等红茶,贺天顺谢过,却没收下。齐老板略有尴尬,脸上堆起笑:“贺县长慢走,改天来贵宾室休闲哈。”
贺天顺不会搓麻将,但他没说不来,而是说了一声谢谢。
那晚,贺天顺回到家,疲惫地倒在沙发上,自言自语,都退休了,怎么感觉比在任时更累?晏瑞丹哼哼了一声,对他说:“这才开了个头,等着吧,连锁反应,这次东风为你接风洗尘,下次就轮到其他人请你了。”
“东风是自己人,其他人就免了。”
“依我看,东风可以免,其他人不能免。”
晏瑞丹话中有话,贺天顺没去想,倒是他衣服口袋一角猩红,引起晏瑞丹的注意。她以为贺天顺收到的红包,掏出一看,才知道是一张派款单,邱处长女儿的结婚请柬。
条件反射,晏瑞丹对这样的红纸卡过于敏感,她一脸恐惧,叹了一口气,说:“我逃到哪儿,这张红色通缉令就追到哪儿,我真是无处可逃啊。”
“说话别夸张,不就是赶个人亲吗?说好了,到时你得去,请柬上写的可是全福。”
“你以为只有你有全福吗?我这里也有全福。”晏瑞丹“啪”的一声,把一张红纸卡拍到桌上,一脸愁容地说:“章显德妹子家的亲家哥的儿子结婚。”
“什么章显德,还妹子亲家哥,隔得远了点吧,如果分不了身,有些人亲就不一定去了。”贺天顺帮晏瑞丹排忧解难。
“什么隔得远了一点,人家帮过咱家,那年你老母亲晕倒在大街上,人家章显德妹子亲家哥背着老爷子上了医院。再说了,咱家儿子结婚,人家也赶了人亲的,还是个整数,这个人亲咋都得还。”
说到母亲,就触到贺天顺的痛处,他没再纠结什么章显德,还是章显德妹子亲家哥,赶忙进了母亲房间。老人已八十七高龄,身体不好,整天躺在床上,贺天顺一进屋,她眼睛亮了一下,看着自己儿子,目光平静。
三
那天,贺天顺往红包里放了八百元,随手装进衣服口袋,晏瑞丹说:“就完了?不写上自己名字,不等于白送了吗?”说的也是,贺天顺掏出红包,慎重地写上自己名字,每个动作都别扭,一个县长,疏于这些俗事。
彭东风开车接他们,先把晏瑞丹送到章显得妹子亲家哥的儿子喜宴,两人才赶到天龙酒店。邱处长站在酒店门口,贺天顺上去和他握手,并致恭喜,而恭喜两字说了多遍,他的红包也没送出。邱处尴尬地陪着他握手,贺天顺是在感到对方尴尬的情况下,掏出红包的,仿佛掏出一个炸药包,赶紧塞到邱处手里。
他被安排到第二排餐桌,刚坐下,就有人叫了一声贺县长,他侧身一看,是钱总,也就是那个关河人的心中偶像,还没走到跟前,他就伸手急切地走来,和贺天顺握手寒暄,他红光满面,一种气场也随之而来。贺天顺招呼钱总坐下,却被引路人挡住,钱总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被引到第一排中间的餐桌,一种气场也随之而去。钱总和那里的几个人一一握手,从他对那些人的称呼里,贺天顺知道那几人是厅级干部。很快,邱处走到那张餐桌旁,双手抱拳:“小女结婚,本是小事一桩,不该惊扰各位领导,但转念寻思,不让领导知道,领导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啊,就硬着头皮打扰各位了。”
邱处的语气,像是表示感谢,又像赔不是,总之笑容可掬,一脸儒雅。最后,他要钱总代他好好陪各位领导,而到贺天顺他们这一座时,邱处仍然一脸笑容,只简单说了两句就离去。所有一切,都让贺天顺心里不舒服,他称胃痛,叫彭东风送自己回家。
回到家,他没有开灯,也没开电视,靠在沙发上,点了一支云烟,烟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像夜色眨着眼。
晏瑞丹回来,开了灯,忙着换鞋,当她再抬头时,吓了一跳,怎么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待回过神来,她才发现是贺天顺。
她说:“你别吓我。”
他面无表情:“怎么我就吓着你了?”
她说:“这个时间,不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开电视,也不开灯,是人都会被吓着。”
贺天顺翻了一下身,说,“一惊一乍的,我才被你吓着了呢。”
啪的一声,晏瑞丹把一张红纸卡砸到茶几上,贺天顺又是一惊,瞟了一眼红纸卡,是一张店铺开张的请柬。晏瑞丹坐到沙发上,也没开电视,看着那张红纸卡说:“离开关河县,目的是逃避人亲,没想到逃到省城,这种事一桩接一桩,比关河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