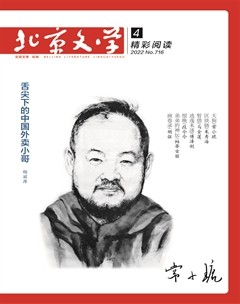1
灶上小火煮着鱼,鸟一般“咕咕”地叫唤。浓郁的香味从敞开的门缝里面蹿进来,冲淡了先前满屋子的鱼腥味。吴颂莲催促身后的金钩儿快点,她担心锅里的鱼烧煳了。操,不就是一条鱼么……金钩儿骂了一句粗,啪啪地往吴颂莲屁股上猛拍几掌,身下撞击的动作跟着愈加猛烈。像是为了尽快完事,吴颂莲恰到好处地呻唤两声,声音悠长而黏稠。金钩儿没有绷住,一声嗷叫,身下一泻千里。未及金钩儿完全委顿下来,吴颂莲便抽身下床,看着吴颂莲鞋子都来不及划拉,一丝不挂地晃着胸前两坨坠肉冲向灶房,金钩儿咧嘴笑。
鱼真是个好东西,这么多年,他也讲不清楚提了多少条鱼给吴颂莲。当然,那些鱼并没有多少落入吴颂莲的肚子,多半被吴颂莲的瘫子男人享用了。金钩儿甚至怀疑,也许就是那一碗碗鲜美的鱼肉鱼汤,才使得病入膏肓的瘫子能活到今天,而且有了越活越滋润的迹象。
将锅里的鱼扒拉出锅后,吴颂莲进屋勾了身子套衣穿袜,腰间松松垮垮的赘肉臃在一块儿,一圈叠一圈。
“吃点走吧,我还得去看看,晚了就没有了。”
这是在委婉地逐客,吴颂莲并不打算留他过夜。
“回不去了,窝被人占着。”金钩儿说。
“怎么,那姓程的又来了?你图个什么嘛。”
“别搞错,听老鬼讲,可是条大鱼。”
“我不管,反正不能留你,不能坏了规矩。”
大门被拉开又被“咔哒”关上,吴颂莲匆匆走了。都这个点,菜场被人丢弃的剩菜烂梗恐怕早被人拣完了,不过运气好的话还有些收获。
金钩儿很想趁兴奋劲还未完全消退,美美睡上一觉——这一段时间,和姓程的挤在逼仄生硬的船舱里,骨头都酸了——可楼下棺材铺闹腾得很,还噼里啪啦炸着鞭炮,搅得人睡意全无。他晓得是有人给跳江的那对恋人来抬棺材了,生前两人在一起遭到亲人强烈反对,死了,双方家长居然同意了合葬一块儿,这世间的事呀。金钩儿索性翻身起床冲了个凉,在阵阵鞭炮硝烟味中,就着满满一钵酸菜鱼干掉了小半碗干烧。吴颂莲烧鱼的手艺好得没得说,酸菜抢掉了鱼的腥味,浓稠鲜美的汤汁在经过充分熬煮后已经渗入到豆腐和酸菜中。
喝过酒,金钩儿捏起一根鱼刺慢悠悠地剔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手表,决定还是等吴颂莲回来。也许,这块看似普通却昂贵的表能让她改变主意。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对岸高楼的亮化灯次第亮起来,铺在江面荡出了迷离的水波,煞是好看。
灶台上搁着小碗鱼肉,丝丝缕缕冒着热气。金钩儿目光乜了一眼那扇终年紧闭的屋门,里面一片死寂,从进门起他就没有听到过任何响动。犹豫了片刻,他端起那碗鱼肉推开门,一股浓重的异味熏得他下意识地别过脸。屋里没开灯,借着江对面闪烁的灯光,金钩儿看见一个干瘦的人形儿半躺在床上,两三根管子从不同的方向伸向他的头部、腰部和手臂。觉察到有人进来,人形儿长长地呻唤了一声,像一声长长的拖着尾巴的叹息。
“吃——”
金钩儿瞟了一眼床上的男人,凑近了,吐出一个字。
男人缓缓移过头,金钩儿撞上了两道恶狠的锥子般的目光。他心里一凛,慌忙拔了腿,疾疾地退出。
打他认识吴颂莲起,她的男人就在床上躺着。那个时候,男人还能动一动,吴頌莲经常推着男人下到江边散步或擦洗身子,撑船的金钩儿碰着了,偶尔会伸手帮一把,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
那几年,吴颂莲在青草桥头槐树下摆了一个摊子,修鞋、钉扣、浆洗、缝补,夏天还兼着卖凉粉苦茶冰饮,鱼市街的街坊,江边的“漂佬”,念着女人的不易,情愿多走几脚路,也要将生意送到桥头。吴颂莲晓得众人的好,收费自然也就比别家矮了一截。生意虽好,但钱赚不下几个。也搞不清楚是哪一年,吴颂莲学会收拾自个儿了,不再出摊了,大家再看她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青草桥头怜惜的目光。
久等不见人回,金钩儿摸出手表,一阵金属的冰凉经由手指传至全身。他将表搁饭桌上,想想,担心这表落入别的男人手中,便又揣回兜里,如此两三回,金钩儿还是决定把表留下。
门外,楼梯响。
吴颂莲拎着沉甸甸的一袋东西回来。金钩儿抢上去,将袋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地上,几把小青菜、三四根苦瓜、一扎泛黄的长豆角,几颗滴溜溜滚向墙角的土豆。
金钩儿有些不是滋味,递过毛巾说:“这东西要不了几个钱,不好看。”吴颂莲眉眼没抬,淡淡地说:“要好看早饿死了,你们男人,几个靠得住?”金钩儿酸水直冒,心里虽然有些不快,但脸上依然堆笑道:“可别这么说,我们都快二十年的老夫老妻了。”吴颂莲“呸”的一声,起身,发现灶台上的小碗鱼肉不见了,转身问金钩儿。金钩儿有些得意地往紧闭的屋门努努嘴,吴颂莲猛然失色,快步冲进屋。屋里一片狼藉,碗碎成了几瓣,鱼肉和汤汁撒了一床一地。吴颂莲掰开男人毫无血色的嘴,左看看右看看,见没有异样,回身斥道:“你这样会害死他的。”金钩儿意识到自己大意了,辩解道:“我也是……他命硬着哩。”吴颂莲瞪了他一眼,呛道:“这么多刺,你试试?”金钩儿没料到吴颂莲这样堵他,一时噎得说不出话,黑着脸转身出门。吴颂莲抢出来说:“东西拿走。”金钩儿回转身,看见吴颂莲真是生气了,有心说两句软话,可脸上却挂不住,心里也不爽,一把抓起桌上的手表,“噔噔噔”地走了。
2
槽江是一条声名狼藉的河流,自古以来民风彪悍,匪患成灾,因渔业资源匮乏,渔民纠集打劫过往商船或收取“保护费”的事情时有发生,令商家无不胆战心惊。遇到明火执仗抢劫的还好一些,破财消灾好歹保住一条命。最恐怖的是水鬼,船行至险滩,突然从水底蹿出几个光头赤身的水鬼,船上的人未及回过神,便被明晃晃的长镰割了脚,或被渔网罩住拽入江中喂鱼。
金钩儿的祖父就是一名水鬼,水性了得,不比一百单八将里的阮氏兄弟差,据说能在水底憋半个时辰不换气。祖父不自己干,只替人接活,提取主家佣金(或以劫来钱财冲抵),同时恪守一条原则:图财不害命。祖父的传奇经历真假已无从考证,就连他的爹爹说起祖父也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明显带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有一点可以佐证的是,金钩儿依稀记得祖父常常从外面扛一些东西回来,那些东西祖父从来没让他们碰过,至于那些东西最终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后来,水运日渐式微,匪患销声匿迹,一江浊水重归了往日的平静。
行船跑马三分命,本地人少有在船上讨生活的,槽江沿岸,多是外地来的渔民,有的是夫妻船,有的拖家带口,更多的是像金钩儿这样的光棍。他们沿岸聚集一溜儿排开,终年漂在黄汤浊浪里讨生活,当地人习称“漂佬”。
金钩儿充其量只能算半个“漂佬”,鱼市街却人人识得他,都唤他金钩儿,晓得他打着鱼,替公家干着“钩尸”的营生,晓得他那把常年被江水和烧酒滋养的铁钩好生了得,钩过不少冤魂和亡灵。
跳江轻生者几乎月月都有几桩,每年夏秋两季——尤其是高考张榜后——是跳江高发季,水上派出所救生巡逻队日夜巡查,同时,他们还给金钩儿和另外两个渔民发了块编外人员的牌牌,并凭此每月到巡逻队领取一百八十元补贴。这点碎钱金钩儿瞧不上,也只够四五天的酒钱,好在还有别的生钱的门道——索取感谢费。钩上来的不管是有一口气的“活尸”,还是没气的“死尸”,有人来认领,少不了索些钱财,当然最后他也只分得一小指头,大头则被巡逻队队长老鬼拿去了,这是水上行规。
程多宝就是金钩儿钩上来的“活尸”,被钩上来时人已经不行了,一通按压,程多宝突然坐起来,犹如噩梦中惊起。他盯着金钩儿,半晌不说话,旋即爬起来,用手掩面,跑了,留下一串慌乱的水脚印。金钩儿根本没防备,错愕间,忘了拔腿去追,眼睁睁望着一个矮小的背影一溜烟消失在夜色中。
三天后的清早,金钩儿收网归来,却见一人立在岸边,金钩儿以为是来买鱼的人,挥手说走吧走吧,那人却木然不动。金钩儿定睛细看,几分眼熟,四十来岁的男人,微胖,阔脸,头顶微秃,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颇有几分斯文相。那人看见邻船帘子响,慌忙跨上船钻进舱。金钩儿认出来了,正是几天前夜里逃跑的那个人。于是怒道:“还有脸找来?”那人也不答话,笑吟吟地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烧酒。看见酒,金钩儿的舌头就打卷了。那人自称程多宝,嘱咐把船开到僻静处说话。金钩儿照办,把船往江心开,程多宝双手叉腰站在船头四望,很像一副干部视察的派头。
“这一拆,不知又要喂饱多少人啰。”
程多宝说的是鱼市街的拆迁。鱼市街早先是个小渔村,后逐渐成为“漂佬”和城市外来人口落脚地,散落着大批的酒馆、杂货铺和车船店,清人有诗云:青草桥头酒百家。说的就是当年的盛况。随着城市“一江两岸”的规划,一直被视为这个城市牛皮癣的鱼市街面临拆迁开发。消息早两年就放出来了,只是一直未见动静。金钩儿并不关心这些,拆与建都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不管怎么折腾,总不能把江给填了,有江就不愁活路。
“听上去,老弟可是政府的人?”
“生意人,做点小买卖。”
“碰到什么解不开的结?……花花世界,有酒有女人。”
“活著不如死去,别以为我会对你感恩戴德,你可害苦了我。”
“被我救的人都这样说,不都活得好好的。”
“我也想活,但有人要我必须死,我死了他们就安生了。”
“落水那夜,我看见了桥上那些家伙。”
“是的,还得劳烦你弄死我,他们见我活着,还是一死,且连累他人。”
“把你弄死我就得坐监,要死自己跳嘛,碍我何事。”
“当然碍你。如果你没救我,我这会儿早死了。”
金钩儿噎了半晌,觉得好没道理,便冷了脸,掉头回转。
“你不弄死我那我只得在你这儿避避,我出不了门哇。”
程多宝这句话虽被呼呼的江风吹散,但金钩儿依然听得真切,看来还真被赖上了。
果然,一连好几天,程多宝赖在船上哪儿也不去,金钩儿管吃管喝,一天倒贴不少饭菜钱。看金钩儿脸色越来越难看,程多宝[典][见]着脸说:“出门急,没带够钱,若不嫌弃,这块表送给您,老哥权当行善。”说完撸下表递给金钩儿。金钩儿不屑地哼唧一声,像自己这种看日光吃饭干活的粗人,戴个明晃晃的表岂不惹人笑话。
突然多了个人,睡觉也是个问题,船舱本来就逼仄,还堆了一些杂物。金钩儿习惯了一个人睡,卷了被子横竖到天亮,可如今身边躺着个大活人,睡觉如挺尸,别提多别扭。更令人尴尬的是,金钩儿夜里总会睡过了,迷迷糊糊以为身边是吴颂莲,手也就跟着迷乱了。一块儿挤了几天,程多宝卷铺盖上岸搭板子睡。金钩儿清早起来看着刺猬一般蜷缩在岸上的程多宝,心里居然生出一丝歉意,但很快,这点歉意被程多宝一句话给冲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