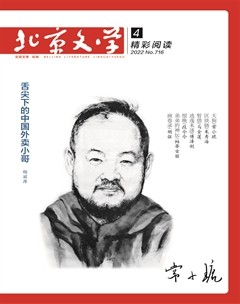重症监护室家属探视区,一个中年女子躬身趴在椅背上,两只手掌撑住脑袋号啕大哭。几个穿橘红色背心的志愿者追过来问我:“您是死者家属吗?”那一刻,我的身子一下子失重,恍惚间魂像是要飘出去了。
那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子,她的弟弟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几个志愿者误以为我是死者家属,围过来问我是否需要服务。这个误会似乎在暗示我,弟弟离死亡只有一墙之隔,我离成为“死者家属”也近在咫尺。
一
弟弟住院那天正好中秋,我和妹妹各自从长江、香江边赶来,在弟弟的病床前团聚。弟弟发着高烧,瞪着发红的眼睛,显得莫名的亢奋:“我从天花板上往下看着病床上的那个人,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喘气,很虚弱。一群护士围住他,医生拿着榔头和扳手,在敲打他的身体,那个身体硬邦邦的,我知道躺着的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他才46岁,我替他难过,他活不到47岁了。”
弟弟满口胡言乱语,在他的意识中,进医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茶师傅邱二槐,他给大成说:“邱师傅病得很重,你马上把他送到医院。”说完又给邱师傅打电话:“邱师傅,你病得很重,回不了老家了,中秋节你要在医院病床上过了,我让朋友马上接你去住院。”
他床头的病历卡上明明写着:司拉英,男,46岁,重症肺炎引发脓毒血症。他已经无法分辨,中秋节躺在医院病床上过节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值班医生叫我去看电脑里弟弟的肺部影像,他不断拖动鼠标,想从肺片上找到一点黑色的空隙,最后失望地说:“你看他的肺,昨天还有点黑色分布,今天早上已经全白了,没有空隙了,连肺部最顶端的边角都白了。”
“我弟弟还能坚持几天?”
“靠把氧气压缩到肺部呼吸,病人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左右。”
医院取肺泡盥洗液去检验,需要实施全麻,医生允许我和弟媳妇去探视,“有什么话先想好,拣重要的跟病人说。”
弟弟躺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和弟媳妇戴着口罩,被允许站在五米之外跟他说话。弟弟在说话,却没有声音,口型像在叫妈妈。我很诧异,因为母亲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到大,绝口不叫的就是妈妈。
我问弟媳妇:“他在说啥?”
弟媳妇有点难过地撇了一下嘴,“他对我和宝宝都没有话要说,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大哥,让我们把马尔照顾好。”
他最后要交代的竟然是他哥马尔……
弟弟照顾患有精神双向障碍的他哥十几年,为他送饭、洗衣服、打扫住处。马尔到哪里都跟邻居吵闹不休,住不了几天就被房东赶走。弟弟一个月要帮他搬几次家,他四处托朋友求情为他租房子。马尔病情严重的时候,半晚上能打一百次电话,到了凌晨两三点弟弟才睡,后来不等到凌晨两三点,他就无法入睡,总担心哥哥来电话,这已经成了他的生物钟。
弟弟戴着氧气罩,眼睛朝我们这边瞪着,等着我们回应他。我怕他听不清我说话,伸着两根手指做出一个V的造型。他很费力地朝这边看了一眼,用手指艰难地做出OK的手势,这个动作很缓慢,像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弟弟在中山做了四年柑普茶,每年做完茶都累倒,进医院住上大半个月,他把那些小馒头一样的小青柑看得比命还要紧,发着高烧淋着雨,还要去给茶打伞撑雨布。现在他和家人赖以生存的“茶馒头”,在茶厂里静静地躺着,等着他起来。
在茶厂,我把弟弟的嘱咐告诉马尔时,马尔用维吾尔语哭喊着:“我弟弟要死了,我弟弟要死了!”他用母语哭喊,是想避周围人的耳朵,他是对着我和妹妹哭诉。即使他疯癫,也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就要失去自己的亲弟弟,茶厂要失去主人了。仿佛在粤语的地界,这样说话就能瞒过死神。
妹妹背着马尔说:“姐姐,我们都是吃尕娃蒸的馒头长大的,我们活着,怎么能看着他走。我想来想去,这话只有你听到,说实在的,马尔活着是件麻烦事,尕娃照顾了他十几年,换一个马尔走了,还没这么难受,四个男孩儿里面,最舍不得的就是尕娃了,谁走他不要走。”妹妹一直习惯叫弟弟的乳名。
二
弟弟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四天清早,我去探视,医生笑着对我说:“你弟弟想吃馒头了。”
弟弟好转后,第一个想吃的就是馒头,这个消息让我喜极而泣。
我们小时候,父亲忙地里的活儿,母亲疯疯癫癫,我们一家吃的馒头,都是二弟在炕上蒸的,“哥哥在炕上蒸馒头”,三弟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话。家里人纠正说,“馒头蒸在锅里,不是炕上。”二弟人小,够不着案板,其实是在炕上揉好了面,再放到锅里蒸。
在广东中山,他依然喜欢蒸馒头,任何时候问他,吃什么?他的回答都是馒头、面条。这次进了医院才检测出他对大米和玉米过敏。童年每天吃玉米糊、玉米饼,每次吃完饭弟弟都喊肚子疼。父亲让他趴在炕上“暖肚子”,他每天吃了饭就蜷缩在炕上,像个小馒头。
弟弟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媳妇买馒头,“要是早知道我对大米过敏,就不该走出老沙湾大梁坡,在广东不得不天天吃大米,胃都吃坏了。”弟弟说这话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脖子上、鼻孔里插着管子,靠管子里的氧气和液体维持呼吸和营养。
他很想自己吃饭,十几天没有吃东西,他的胃已经接受不了任何食物。他晚饭吃了几口馒头,晚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喘口气都费很大的劲,他说,“我连吃馒头的力气都没了。”
他脖子左侧有个血肉模糊的洞眼,里面插着一根塑料管子,管子穿在一个白色盒子下面进入弟弟的颈动脉,那里用巴掌大的透明胶固定着,小盒子两只小耳用羊肠线与皮肤缝在一起。方形盒子下面伸出的那根管子,又被分离成三股,连着三个玻璃针管,分别用来注射身体需要的各种液体。那串针管像弟弟的耳朵上挂下来的沉甸甸的玻璃耳坠,随着弟弟的脉搏晃动。
晚上,我租了张简易帆布床,睡在弟弟病床边。弟弟刚从死亡线上回来,我在他病床边陪着,想给他最大的安全感。弟弟对着我笑笑,露出满意的表情,表情还跟儿时一起睡在大炕上一样纯真。
我小心翼翼地摸摸弟弟脖子上吊着的三根针管,问他疼不疼,难受不难受?他闭着眼睛,憋了半天,大概好久不说话,忘记怎么说话了,说出来的话很反常,“有些东西,就像一个贝壳,把它洗干净了,里边的肉还是臭的,不如干脆扔了。”
过了半个月,医生把弟弟脖子上的插管拔了,露出三只洞眼像三只眼睛,血汪汪地冒着泡。过了几天,三个洞眼结了血痂,看着像是三只大苍蝇,我总想用手去抠它。弟弟说,“对付伤疤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忘了它,它就不见了。”
半夜我牙疼,他也说,“你忘了它,痛就消失了。”对待疼痛,他选择了遗忘。这让我觉得他属于忘性比记性好的那一种人,要么就是疼怕了,过了临界点,已经麻木了。
三
我坐在弟弟的病床边,假装用力掰一掰他粘连的脚趾,做出想把它们掰开的样子,掰完问他疼不疼。他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用舌头与牙齿弹出了一个“啧”,这是小时候的习惯,表示对我说的话持否定意见。
“啧”,这个回答再恰当不过了,疼和不疼,只有他说了算。
弟弟出生没几个月,就被精神分裂的母亲当成柴火,把头塞进熊熊燃烧的灶火里;刚刚会走路,又撞翻了我正在灶火上烫熟的一铁勺子滚油,他的两个脚趾至今像鸭蹼一样粘连在一起,为了不露出丑丑的脚趾,他一年到头都穿皮鞋。
被我烫了脚那天,我背着他去西瓜地里。他整整一个夏天都哭闹着要去西瓜地,父亲让我留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管好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忠于职守的我,平时忙于家务,根本抽不出身子,带他去西瓜地。那天下午,为了止住他的哭,我只有背着他走了两公里的路,去运河边的西瓜地里吃西瓜。他不能下地,这一路弟弟一直忍住哭乖乖地趴在我的背上,似乎去盼望已久的西瓜地能让他忘记疼痛,也许他那个时候就在练习如何忘掉疼痛。
我不知道那一天,天是怎么黑的,父亲的鞭子是怎么落在我身上的。我只记得,之后连着半个月,我每天早上背着弟弟去两公里外的大队卫生所,找谢医生换药,弟弟的脚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我看到谢医生用镊子镊掉弟弟的脚指甲,从弟弟的脚趾间镊出一豆豆小白蛆。
弟弟长大后出落成了一个帅小伙,读了石河子师范学校,我知道因为家贫和自卑,他错过了那个年龄最纯真的一段爱情。娶现在这个媳妇时,他想听我帮他选择,一个是外地来中山打工的小姑娘,一个是离过婚的广西女人。我说,选离过婚的女人懂得珍惜家庭,年龄大点会过日子、会照顾人。他听了我的建议,娶了广西女人,却没说起女人还带着一个女儿。
男孩子中他排行老二,总是穿从哥哥身上继承下来的旧衣服,等哥哥马尔出去打工,他开始继承父亲身上脱下来的旧衣服。他去石河子师范学校上学,穿的就是父亲去世后脱下来的衣服,衣服大大的,像一个灯罩套在他身上,下面是短短的一截裤子,他像一豆苦难的火苗,怎么也冲不出笼罩着他命运的灯罩。
医生拔掉他脖子上那些插管后没几天,弟弟就开始焦躁不安,担心医药费昂贵,催着医生快点让他出院。医院抽了血,他等不及验血结果就闹着让我带他回家。他一遍遍叹气:“哎,要命啊,一個月没有吃饭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求求你,回家弄点饭吃吧。”他脖子上刚刚拔掉管子的三个洞眼还糊着血痂。我不忍看弟弟那副枯槁的样子,像是一个乞丐在对着我乞讨。
我拗不过他,扶着他逃出医院,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他揽进车里,他的身体轻轻的,像个小孩。出租车上,他媳妇打来电话,说她去新疆餐馆买羊肉,要八十多元一斤。他一听,脸上呈现出惊喜,“我住院一个多月出来,羊肉涨到八十多元一斤啦!”
他与那家餐馆老板通话,餐馆老板认识他,答应七十元一斤卖给他。
这个电话让弟弟兴奋得发癫,他闹着要下车,说要去洗个头、理个发,“姐,我一个多月没有洗头了。”
“进重症监护室前,医生帮你洗过。”
“你一个月不洗头试试,都臭了。”
“你脖子上的插管刚拔下来,伤口还带着血,沾水会感染伤口。”
“我要快点出院,没想到羊肉价格那么好,开个羊肉档,可能是条活路。”弟弟开始掐指算利润,越算越癫狂,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在受医院救治的病人,忘了才从死亡线上下来,他病床床头还挂着“重症”“禁食”“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