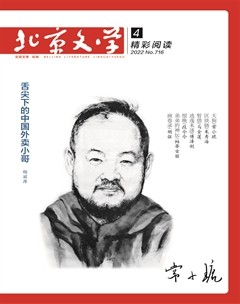一
我家这个小院子是将近一百年的祖屋,爷爷用卖猪仔的钱攒起来建造的。爷爷上山后,我爸爸和小叔分家,分居左右厢房。小叔也五十不到就走了,小婶把房子卖给插队返城的蔡家夫妻,顶着压力改嫁了。
而我所要关注的,便是这位蔡家夫妇的女人,她是先变成寡妇,再变成阿婆,从中年一直熬到老年。人事消亡,院子跟着就衰败了。院子里不种花,也不种其他的植物。只在夏末的时候,蔡阿婆在角落里铺上泥土,拌入沙子,再撒上几把萝卜种子,有白萝卜、胡萝卜和青萝卜。
“唉,这日子过得比萝卜还寡淡。”蔡阿婆常常这么说。
疫情暴发后,巷子被封了,蔡阿婆家的菜没几天就吃完了,庆幸还有萝卜可以填肚子。沙土的表层被萝卜根须撑开一道道裂缝。她伸着小铲子,一铲子一铲子地挖下去,灰尘一阵阵地扬起来。她的喉咙忍不住发痒,想要咳嗽,又怕被人听见,就缩着脖子,把咳嗽声咽了下去。不一会儿,她拔出一个杨花萝卜,只有婴儿拳头那么大。
“再小的萝卜也得有个坑哪!”
她嘟囔着,吐一口痰在上面擦去泥土,整个扔进嘴里咬了起来。她经常说,萝卜就是穷人吃的菜,我们都是萝卜人。“哎哟,生吃萝卜最爽快!吃完放一个大响屁,这一天闷的气就顺了!”
一只流浪母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她的脚边来回地蹭,还不时地抬起脸朝她“喵喵”叫,讨好她。她不耐烦起来,一脚踢过去,破口大骂:“死猫滚开!浑身都是跳蚤,脏死了!”母猫发出一声惨叫,一下子蹿得老远,消失了。
蔡阿婆的两只干瘪的乳房布袋一样垂下来,在胸前剧烈地挣扎、跳动。她低着头继续挖开一层又一层的沙土。每个萝卜都规规矩矩地待在自己的坑里,一个紧挨着一个,默默地生长着。
二
这个冬天的傍晚,天黑得特别早,巷子里一片沉寂,静得可怕。突然,拴在铁拉门后面的土狗点点狂吠起来,蔡阿婆厉声喝止,它不依不饶地叫个不停。一条锦鲤不知什么时候从鱼缸里跳出来,掉在地上不停地挣扎,打出一个又一个规整的圆圈,来回扭着身体,已经救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隔壁传来吵架声。吵架的双方,是蔡阿婆和他的儿子阿树。
蔡阿婆这会儿应该在厨房里切萝卜,砧板剁得“咚咚”响,一边和儿子阿树隔着墙吵架,手和嘴一起动,一刻不停。她当年插队去了洞头县,嫁给闽南移民后裔家庭,学会了讲一口洋泾浜闽南话,吵起架来温州土话、闽南话和普通话掺杂着一起上。大家都听不懂他们吵些什么,就觉得说话像快进式拉锯,越来越快,每一下都在锯耳朵。
蔡阿婆每天闷了、烦了,照样拿阿树出气,母子俩总是说不上一两句话就开吵。丧夫后,她就把全部的精力都耗在吵架上,只要认识的人,全都吵过架,从巷口吵到巷尾,整条巷子都吵遍了。就阿树和她最亲近,她每天没事找事可劲地找阿树的茬,天天从早到晚吵到不可开交。不过,吵归吵,母子俩却不闹别扭,打断骨头连着筋,这就是亲情。蔡阿婆从骨子里散發出强烈的母性,把阿树照顾得无微不至,同样也是远近出名的。
她平常都选择晴天,把刚挖出来的新鲜的萝卜切丁,加五六勺盐腌制五六个小时,待萝卜变软后,挤出水分,用清水冲洗,放入干净的布口袋里,压上石头,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