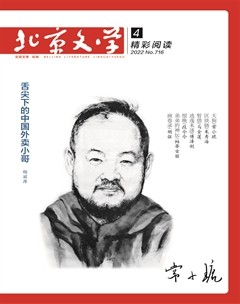一、草木农事
梭罗在《野果》里谈道:“对于我们来说,本土所生所长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比别人那里生长的意义更重大。”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童年的百草园或百宝箱,被各种熟悉亲切的名字和小物件塞满。也有人去专门做了功课,我身边的很多作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植物学家,可以不借助“形色”识别就叫出很多花草树木的名字。我的“百草园”不在老家的房前屋后,而在广袤的田野山林之间。我对花草树木的了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们散落各处,安静地等着被人发现、靠近,进而与人们的生活和个体的成长产生各种交集。对于我而言,那些熟悉久远的一草一木、野菜野果,带给我的远不止童年的回忆和乐趣,还有相关农事与情感的链接。一些金子般的细节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反复捞起、擦拭,闪着柔和动人的光泽。一切都是对来处与往事的唤醒,一切都成为亲切的怀念与永远的乡愁。
我的家乡在重庆山区,不多的水田和大片的山地里种植的主要是水稻、小麦、玉米、红薯之类的粮食作物。不像湖北农村的平原丘陵地带,物产要丰饶得多。在我婆婆家一望无垠的田野里,我才见识了棉花、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样貌。山区坡坡坎坎,土壤贫瘠,耕地又少,出产的粮食只能勉强果腹,不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要想更好地维持生计,人们除了到县城打些零工,也就只能求诸山野了。听奶奶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还很幼小,只能把麻树根磨成粉冲给他吃,帮他熬过饥荒。麻树根就是蓖麻的根,多长于田间地头,叶子宽大呈掌形,结的籽可以榨油。后来母亲还专门辟出一小块地种苎麻,可以长到半人多高,茎秆与叶柄上布满白色硬毛,叶片的边缘是锯齿形,割麻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不要被划到。苎麻的茎皮剥下来,可以做成麻绳或绩布。
所以我童年熟识的草木,主要在于其实用价值和经济意义。猪草接触得最多,因为喂猪是多年来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方式。山里人爱吃腊肉,每个农户一年至少要养大两三头猪,一头作为年猪,其余的用来售卖。那时候养猪也不喂饲料,都是从土地中求取,是地道的有机食材。强调的恰恰是稀缺的,虽然那时候还没有 “土猪”“土鸡”这样的叫法,可是土生土养的家禽家畜、瓜果蔬菜遍地都是。
随着时节的变化,猪们的食物也有一个逐步进阶的过程。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把晒干的红薯藤打成碎粉,在大铁锅兑水煮了再加上一瓢苞谷面,拌了给它们吃。它们也喜欢吃叶片毛乎乎的构树叶。我家屋后的山墙上就长了一棵构树,红色的球形果实(又称为“楮实子”)一颗颗砸掉在地上,据说是可以吃的,但是也从来没想着去捡起来尝尝,许是在内心里要跟猪的吃食划清界限吧。如果小猪从圈里跑出来,会主动站在构树枝下,伸着脖子去啃食那些灰绿的构树叶。
更多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放学之后提着竹筐奔跑在田野山地之间,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猪草”,俗称“扯猪草”。它们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占据耕地中央,只能在田地的边边角角和一垄一垄的农作物边缘见缝插针地野生野长,一簇簇一蓬蓬,细细嫩嫩,很容易就被拔起来了。扯回去的猪草洗干净后切碎在开水里滚了兑上点苞谷面,是猪们最喜爱的时鲜野味。这些猪草有着各种形象而稀奇古怪的名儿:“鹅儿肠”“藤藤草”“吹火筒”“锯锯藤”“红花草”等,以致我多年后在武汉的公园里看到角角落落到处生长着一丛丛嫩绿且无人问津时会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好多猪草啊!”
也不是什么野草猪都可以吃的,要学会仔细辨认,尤其在这些猪草中会夹杂一种叫作“癞子草”的植物,学名“猫眼草”。红色的茎秆,叶子是一簇簇绿色的小圆片,确实像一双双摇曳的猫眼睛。大人告诉我们这种草有毒,猪是不能吃的,一定要把它分拣出来。
到了冬天,田野里成排种植的一种绿油油的、茎厚叶肥的牛皮菜是猪们尤其喜欢的东西,近乎“加餐养膘”。也似乎是为了把人们从一年操持猪食的辛劳中解脱出来,留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和欢度春节。那时候猪圈里养着的是等着在新一年育肥出栏的“架子猪”,食不在多而在于精。正月里人们只需在合家团聚、走亲串友或打牌闲聊的间隙,到田里去掰下一篮子牛皮菜,就够小猪们吃上一天了。牛皮菜肉乎乎的茎还可以去筋焯水了凉拌着人自己吃,也算是贫乏年代的独特美味。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养蚕也曾经在山区风靡一时。一棵棵桑树挺立在坡地周围,等着被一茬茬摘掉桑叶又一茬茬长出新叶,为蚕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吃食。蚕种都是到大队提前预订好的,一粒粒黑色的蚕卵盛在一个两面蒙着薄薄白纱布的小木框子里,摇之沙沙作响。蚕卵放置几天后慢慢爬出黑色的小虫,像小蚂蚁,所以叫“蚁蚕”。这时候就把一片嫩嫩的桑叶覆盖其上,让蚁蚕慢慢爬上去便于分拣,然后再一天天长成白色带花纹的肉虫。摘桑叶喂蚕成了我和妹妹学业之外的另一功课。根据蚕的不同成长阶段,桑叶摘的位置和喂食方式都有所不同:先从桑树枝尖上开始摘,因为幼蚕只能吃嫩叶,长大后的熟蚕就连末端的老桑叶也嚼得动;喂蚁蚕时需要把桑叶剪得细碎,成年后是整片的桑叶一张张铺在装满蚕的簸箕里,“蚕上山”的那几天就可以直接大把大把地撒上一层了。
摘桑叶时会有白色的汁液溅到手上,干了后会变成褐色的斑点。不过这是可以洗掉的,不像大人挖红薯时要我们去掰掉连接红薯的茎藤,沾上的汁浆好几天都洗不掉。摘桑叶的时候我们小孩也会摘紫红色的桑葚吃,但是不会觉得有多么稀奇好吃,也不敢多吃,因为大人们告诫过桑葚吃多了是会中毒的,而且要吃母猪的猪食才能解毒,想想就直摆头。现在看来,应该是大人怕我们不专心于摘桑叶的一种嚇唬吧!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和妹妹戴着遮阳帽正在坡上热汗长流地摘桑叶,母亲忽然跑来叫我们回去。原来是照相的人来到我们村里,母亲决定为姐妹俩照一张合影。这让我瞥见一向注重实际的母亲也会心生浪漫的念头,因为之前家里所有的照片就只有父亲当兵时带回的一本相册,记录着他的军旅生涯。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母亲把我们从劳动中解脱出来,遮阳帽成了即时的道具,我和妹妹戴着帽子站在凳子上,上穿一样的白衬衣,下穿一样的的确良碎花裙子,一脸稚气而严肃地望着镜头。这张最初的照片后来我上大学后在家中的老柜子里还翻见过,现在也不知散落到哪个角落里了。
成年后的蚕养在一个个圆形的簸箕里,体量跟食量与日俱增,吃起桑叶来沙沙有声,我们一天要喂两三次,每天晚上还要给它们作大扫除。把一只只肥大的蚕腾到空的簸箕里,再倒掉剩下的蚕沙和光秃秃的桑叶梗。等到蚕们身体发亮的时候拣到稻草扎捆的“山上”开始吐丝结茧,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雀跃,这一阶段的养蚕劳作终于要结束啦!去蚕茧站卖茧也是有趣的经历。大人们排队等着收茧、查看茧色、确定价格和上秤称重,孩子们就可以在院子里的黄桷树下玩耍乘凉。等得时间长了,母亲会给我们一些零钱,去买几个地瓜来吃。地瓜就是豆薯,又叫凉薯,把皮剥掉了吃,肉质松脆,汁多味甜,既可解渴又可暂时充饥。凉薯属于蔬菜中茎菜类的地下茎,在武汉的店里也经常看到,受了儿时味觉的蛊惑,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买来当水果生吃。
二、药草与根茎
母亲年轻时是一名乡村赤脚医生,自然会识不少药草,行医方面听说也很受当地人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