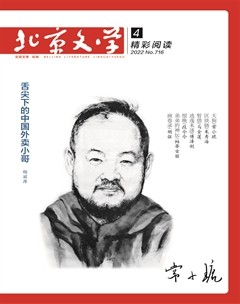1
夜幕降临,远处的树木、近处的园子淹没在无边的夜色里。夜风由远及近地袭来,四周发出嗖嗖的响声。收割了一下午稻谷的五额娘在暮色中缓缓起身。
时光充当着收割者的角色,几十年过去,五额娘年已近八十。眼前的这亩田,她种了近四十年。村子里几次重新分配,这亩田最后还是分到了她手上。仿佛冥冥之中的缘分。她把这块地当成了儿子般细心呵护着。相比于此刻土地的寂静,几十年前故乡的土地上人员密集,打谷机发出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
三楼的仓库里堆满了她这些年种田打回来的稻谷。五额娘的儿子昌平外出打工前,本想把家里的自留地租给村子里卖豆腐的老王种西瓜,但五额娘坚决不同意儿子把地给别人家种,她独自把这四亩多的自留地都包揽了下来。
五额娘不想把自家的地拱手让给人种,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1992年夏天,五额娘的丈夫祥瑞叔赶着家里的那头大黄牛,冒着毛毛细雨在地里犁田。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稻谷刚刚入仓,村里的人正准备着种下秋的秧苗,连绵的细雨笼罩着整个村庄。祥瑞叔一直忙到黄昏时分才赶着牛上岸。细雨中,他戴着斗笠,牵着牛慢慢往家的方向走,雨水淋湿了他的衣。
雨水一直连绵不停地下着,半个月后,农忙接近尾声,祥瑞叔却突然发高烧,浑身无力,脸色苍白。他的右脚底已经肿得发胀,血红色变成了青紫色。原来,那日下午他去犁田时一脚踩在一根生锈的铁钉上,回到家他没放在心上,只随意地在渗着些微血丝的脚底抹了一点消炎药。生銹的铁钉死神般慢慢在他体内安营扎寨下来。“伤口未及时处理引发破伤风,时日不多了。”在乡镇医院苍白的病房里,穿着白大褂的老医生摇头对五额娘说道。这一幕深深嵌入五娘的骨里,无法淡忘。一周后,祥瑞叔看着站在病床前这三个还未成婚的孩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祥瑞叔去世这件事在村子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村里人茶余饭后议论纷纷,言语间满是同情和惋惜之情。当时的我还只有八岁,如今多年过去,也模糊地记得这件事情。即使后来在重新分田的过程中,这亩地分给了别人耕种,五额娘也想尽办法,把这亩地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有些村里人不太愿意更换,但听了五额娘的遭遇后,纷纷表示了理解。
收割完稻谷,喘息了一阵,她又继续在地里种油菜。
村里有些人家没米吃了,都去五额娘家买稻谷,然后拿到镇上的舂米坊去碾米。没油吃了,他们也去她那里买几十斤油菜籽榨油吃。2003年,我母亲身患子宫内膜癌之后不能干重活,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家里的那三亩地就一直给隔壁乡的一户人家种。到了年底,种我家地的那户人家会送四包晾干的稻谷来给我家作为感谢。随着时间的推移,镇上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年底的那四包稻谷免了才有人愿意接手种。家里往年积存的稻谷吃了不到三年就吃完了,母亲就在姑妈家或者五额娘家买稻谷。每次去五额娘家买稻谷,她总会以低于他人的价格卖给母亲。
五额娘把卖米卖油得来的钱存进银行。农忙过后,五额娘就重新把全部心思放在了菜园子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偌大的菜园子里种满辣椒、豆角、玉米、空心菜、四季豆和西瓜。碰上赶集的日子,天麻麻亮,她就起床了,踏着晨露去园子里采摘蔬菜,挑到集上去卖。
2
到了年根,往日寂静的屋子里ー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不时有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村里人去五娘家里买稻谷。“还是你家老太婆好啊,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不仅不要花你的钱,还能给你挣钱。”邻居说道。听着这些话,昌平心底还是高兴。这些年,他母亲不仅给他带大了两个女儿,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稻谷满仓。
年后,喧闹的村庄顿时又变得寂静起来。晨曦时分,昌平和他老婆九妹各自提了半袋子大米踏上了前往异乡的火车。
每次回家,他们夫妻俩总要带一两包家里的米,这是乡愁。他们在东莞一家五金厂上班,昌平做的是仓管的职位,他老婆九妹在流水线上班。他们在这个工业区待了近十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但这里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租住在城市狭小的出租屋里,家里新盖起来的三层新房却常年空置着。寸金寸土的城市没有他们的土地,他们老家的稻田却时刻面临着荒芜的危险。他们是城市的寄居者,这里终究不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