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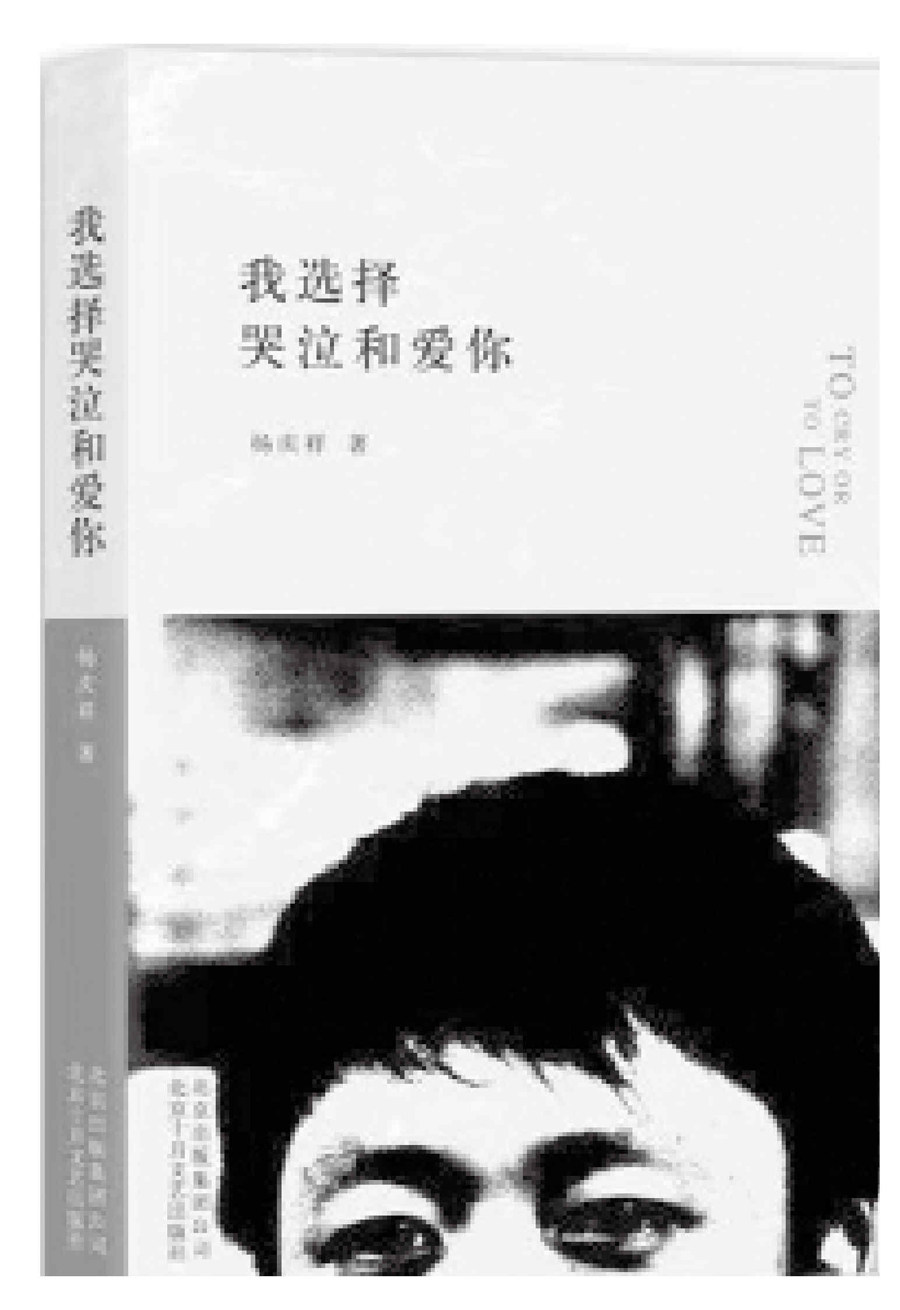
1
读完杨庆祥最新的诗集《世界等于零》,轻轻地放在案上。封面上的那两行诗句:“我来过又走了/世界等于零”,还紧紧地盯着我,凝视着我。我也死死地盯着它,凝视着这本诗集的封面。封面上,那片淡蓝得有些发绿的天空中,与一朵大白云所对峙的右上方,大大的,黄色的,竖排的,五个紧紧连挨的字,“世界等于零”。我知道,这是这本诗集的名字。但是,我总是在怀疑,犹疑不定,后来质疑,世界能等于零吗?
好多了不起的人,包括那些智者、高僧和大德者,都喜欢告诉世人说,要学会清零,要一切从零开始,抱着虚无、空静的心灵去读书念经,去阅世阅人,去面对世界、面对生活与现实。这可能吗?我来过了,我见过的一切,我读过的一切,能清零吗?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除非我的精神生命或者物质生命结束或新开始一次,“我来过又走了/世界等于零”。
这样看来,“世界等于零”,可能是一句箴言,也可能是一句召唤,还可能是一句描述。
但是,我觉得,“世界等于零”,首先是一种描述。真如杨庆祥所说:“零不是无,零是无限的可能,在某一个看似‘无’的地方滋生出无穷尽的可能,这个可能里包括自我、世界、色相和观念。”由此,进一步他又谈到了文学和诗歌,说:“我個人的看法,文学和诗歌,是在原始巫术仪式丧失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零’。或者说,当‘零’被具体化为一个阿拉伯数字序号,而丧失了其哲学内涵后,‘零’的重新仪式化被落实到了诗歌里面。所有的诗歌写作都可以说是‘从零到零’。从零起始,意思是指诗歌的起源不可确定,到零结束,意思是指诗歌的意义永远无法穷尽。真正的诗歌就在这两个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测量的曲线,这个曲线的长度与诗歌的生命力成正比。” (《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170页)由此可见,这可能就是我们去阅读和理解杨庆祥诗歌的一把独特而“私人化”的钥匙。
这样看来,“世界等于零”,仿佛就是一句箴言了,是否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诗歌写作的“秘要”:“道是什么?道就是零。”“零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零既是开始,又是倍加,又是无限地大——乃至于无穷。”(同上)
2
但是,我读完这本诗集后,还是觉得,《世界等于零》,首先是一种描述,是对现在世界生活的一种个人化的描述,是一种极端“私人化”的描述,是对“包括自我、世界、色相和观念”的描述。和他的上一本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一样,都是对他的现存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化下的客观描述。从这116首诗中,或者说从这116块时光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大学青年教授、青年评论家的另一副面孔:感性、敏感、细腻,或者说,多情、感伤、颓废、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这可能就是他作为当代青年诗人的一种面孔。我喜欢他这种诗人的面孔。他不像那些更多的当代诗人,总是在仰起面孔,叙述着那些遥远的历史、民族与古老的不生动的故事,抒发着关于世界、宇宙与国家的那些大而无当的情怀。从他们的这些虚无缥缈的诗意中,读不到当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的人间烟火的具体生活,感觉不到当下人们世俗生活中具体的喜怒哀乐。正如杨庆祥以耳语的私密形式,偷偷告诉我们的真话:“我珍爱三种人:/吻我的,陪我哭的,给我买马卡龙的//我厌弃三种人:/撒谎且不脸红的,假笑的,和所有人打成一片的”(《我珍爱三种人》,同上,第0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