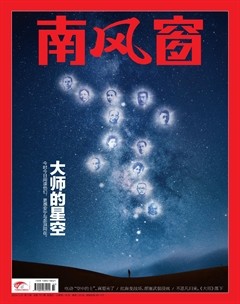1月的南方,田野里经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远方的丘陵,被漫山遍野的两三米高甘蔗遮挡了视线。
冬雨淅淅沥沥。在广西来宾,却是农忙的季节。中国人饭桌上白砂糖的原料—甘蔗,每年在11月成熟,收割季最长能持续至次年“五一”。于是,在我的想象里,理所当然地,田野上应该到处是人。
走了很远,我才遇到了刘金贵,贵州人。在小雨浇打过的潮湿土壤上,他一屁股坐在一捆甘蔗上。也许是雨天,他的全身和脸,都是暗的。只有抽烟的时候,紧皱的眉头才稍微平下来,眼睛也亮了。
他做着当地蔗农公认的最苦、最重的活—收割甘蔗。一根甘蔗轻则5斤,重有10斤,刘金贵要把它们连根斩断,弓腰搬到一起。
这些用于榨糖的广西甘蔗,还要再经过刘金贵的砍刀。
一刀、两刀下去,顶端的蔗叶与茎节分离后,他再徒手把四周的蔗叶拔掉。最后,将多根光秃秃的、符合榨糖标准的甘蔗,用小绳子捆在一起。
一扎、两扎,刘金贵计算过,等地面上整齐摆满了20扎,甘蔗便大约重1吨。他能拿到130元。
这样的体力活日复一日。就像候鸟一样,刘金贵会在甘蔗完成收割的4月离开,“第二年我们(指他和妻子)还过来”。
他们是广西独有的“桂漂”。每年冬天,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刘金贵”们,有的坐大巴,有的骑摩托,一路向东。他们要赶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甘蔗田,当砍工。
这里,是中国甜蜜事业所在地,生产了全中国约三分之二的蔗糖,养活了2000余万广西人的生计。
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地,一座2002年成立的年轻城市,是广西来宾。当地人都说,20多年前,来宾(县)从柳州地区单独分出,成为地级市时,很大原因就是发达的蔗糖业。
如今,还是因为糖,这座号称“天下来宾,来者上宾”的城市,走到了机遇与挑战并重的历史岔路口。
劳作的人
很长时间,来宾市并不被外界熟知,连许多广西人都不清楚它的方位。只有说到桂中、柳州旁边的城市时,许多人才恍然大悟。更多人能记起的是,2010年许,来宾因传销产业甚嚣尘上,在自治区内有“传销重灾区”的称号。
但现在走进这座城市,你很快会被甜蜜产业说服。行驶在主城区兴宾区的任意高速、国道、省道上,两旁目之所及的地方是绿油油的、深不可测的甘蔗地。人真实地置身在两三米高的甘蔗茎秆间,有一种自觉渺小的震撼。
就像来宾过去未受瞩目一样,守在土地的蔗农也长期沉默。正是农民在长久的埋头与沉默劳作间,来宾单个城市的产糖量,占全国食糖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成片的甘蔗地上,头发花白的张信初是少数干活不喜欢沉默的农民。他已经56岁,说话总是不自然地露出一排门牙。漫步在兴宾区王瓜村的乡道上,是张信初爽朗的笑声持续不断,令我最终闻声找到了他们。
他没离开过,在这片土地种了快30年甘蔗。
得知我来自广东,他表现出了惊讶,提高了嗓门。
“你是广东的,跑到我们广西来?”
在这位农夫的世界里,若是年轻人,都会倒着流动—从广西漂到广东谋生。留下来种甘蔗的,都是中老年人。
刺骨的冬雨季,一不小心,甘蔗会生眼斑病、褐条病、黑穗病……受潮的甘蔗若在地里未及时收走,内部可能发黑,糖分受损。总之,普通的甘蔗也像人一样,有着娇贵的身体与尊严。
“现在是打工挣钱的年代了,”张信初露着门牙说,“打工赚得多,工资才高咧。” 他的儿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多年前,张信初的两个儿子都不约而同地,跑到了深圳打工。
而对于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事业”,朴素的农民只有经验上的判断。
“就一个,肥放得越多,甘蔗长得越好。”张信初又露出了牙齿。
当地人都清楚,与甘蔗表面的刚硬不同,这是一个较难打理的经济作物。要想甘蔗种得好,一年至少要施两次肥,去两次虫害。
比起这些,张信初时刻还要担心“天公不作美”。 甘蔗怕低温、多雨,也怕干旱。就像这个刺骨的冬雨季,一不小心,甘蔗会生眼斑病、褐条病、黑穗病……受潮的甘蔗若在地里未及时收走,内部可能发黑,糖分受损。总之,普通的甘蔗也像人一样,有着娇贵的身体与尊严。
哪怕辛苦了一年,终于來到甘蔗成熟时,农民也在为如何收割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