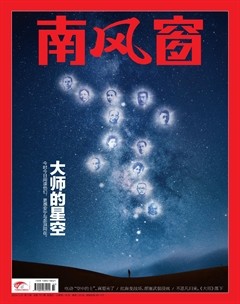1919年,在康奈尔大学当物理讲师的赵元任,把电池的正负极放在舌头上,给自己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不是刻意去模拟某种震颤,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只是想“亲口尝尝电伏特的滋味”。
“尝尝滋味”,大概是赵元任掠过人生的一景一幕时,顶愿意做的事情。生在一个世界格局纷繁复杂的时代,又曾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肩负着“开眼看世界”的种种期许,赵元任身上一度被戴上许多顶沉重的高帽。
在后来者的追忆中,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是蜚聲国际的结构主义大师,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曾任哈佛、耶鲁、伯克利等名校教授,涉猎范围从物理、天文至哲学、音乐,无一不及。在整理档案时,他的外孙黄家林曾说:“我想象不出来,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能做这么多事。”
赵元任不是诸多紧拧眉头的大师中的一员。身在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他更多被纯粹的知识吸引。他深知日子的“滋味儿”是尝的,很难说的。赵元任一生所做之事,无过于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将种种难以言说之物,或以相片,或以文字,或以曲调,一一记录下来。
他的一生,被详细而琐碎地留在了20多万件影像与文字材料中,除学术成果外,还有成年后便不间断的照片、记载了70余年的日记。在这些浩瀚的材料下,赵元任似乎在轻松地微笑。
“好玩儿。”他说。
于忙乱中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写过一本小传,记录赵元任一家的后半生,名为《赵记杂家》。赵元任将其翻译为“Family of Chao’s”,取“Chao’s”既可以看作“赵”的音译,又可看作“chaos”(混乱)。赵元任素喜欢用双关逗人一乐,而这“赵氏”的另一重含义,也隐隐装点了他的人生底色。
1892年,赵元任出生于天津。由于祖父为官,频换差事,在他人生的头十年,赵元任随着家人几乎每两年换一处居所,辗转在磁州、祁州、保定、冀州和常州之间。直到祖父过世,赵元任一家回到家乡常州,才相对长久地定居在一处。
尽管当时的赵元任尚未懂事,但有语言天资的他,很小便喜欢琢磨各地的方言,也在其中琢磨“平常日子”的滋味。单是祖父这一大家子人中,便有说京话、常州话、保定话、山东话等各地方言的。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赵元任很早便感知到语言与身份的联系。
彼时,赵家几个孩子尚未完全掌握发音方法,像“天、全、面”等字,只能发成“贴、瘸、灭”音。小时候的赵元任看见有猫儿偷吃面,也只能大叫“猫雌我的灭”(猫吃我的面)。
但有一日,赵元任比家里哥哥姐姐先开窍,忽然学会了前鼻音的发音方法。他将这发音方式告诉哥哥,却没得到想象中的赞许。因这种说话方式,和照顾孩子的保定人周妈的口音相似,赵元任哥哥回他:“别学那些老妈子说的那种话!”
这种方言和身份的关联并不是固定的。日后回忆起来,赵元任反想起友人傅斯年的口音。因其一家是搬到北京的山东聊城人,家中佣人说话多为北京话。当傅斯年在读书时学会说北京话时,家里人也笑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赵元任推测,许是这一笑,让傅斯年即使在已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国音的时期,仍爱用“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方言说话。
与更宽广的世界产生联结的新语言,迅捷切入赵元任的生活中。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赵元任这类世家子弟,开始走入新式学堂。这个阶段前后,因私塾老师、祖父、父母的接连过世,赵元任于1906年到常州本地的溪山小学读书,随后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正式翻开新的一页。彼时,晚清一批知识分子已开始望向世界,不少国人开始反思自身文化传统,试图在对比中搭建桥梁。1898年,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马氏文通》比照着拉丁语的语法写就,借拉丁语的语法结构,讲述中国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赵元任比家里哥哥姐姐先开窍,忽然学会了前鼻音的发音方法。却没得到想象中的赞许。因这种说话方式,和照顾孩子的保定人周妈的口音相似。
在南京读书的赵元任接触了这本书,同时师从美国老师学习英语、物理,并选修了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