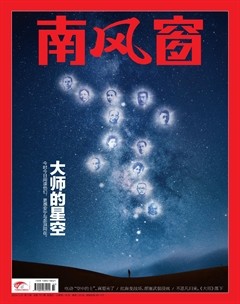一名融合了东方典雅气韵和西式自由气质的女性,把自己瘦削的身子安放在一张大绘画桌面前,不停地写写画画。
她是林徽因,共和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师。
从不被允许以宾大建筑学学士身份毕业,到归国后与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为守护中国古建筑而冒着战火与危险四处奔走,晚年被重疾缠身时坚持在床榻上完成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那短短51年的一生,大半献于中国建筑。
她以娇小瘦弱的身躯,搭建中国建筑学早期的理论骨架,为战时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撑起了保护罩,也将那“一身诗意千瀑寻”的文艺造诣与刚强坚韧、高洁硬铮的人格,熔铸进中国建筑的雕梁画栋。
在北京八宝山,“中国近代建筑之父”、陪伴林徽因共度大半生的丈夫梁思成,亲手为发妻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迟到100年的毕业典礼
1924年夏,宾大校园里,林徽因总穿浅色中式上衣、深色长裙,活跃在课堂和社交活动上。“她的慕求者之多有如过江之鲫”,但学业才是她心中最重的分量,她总能在作业评比中脱颖而出。
不过林徽因在宾大时,因其女性身份受到了入读建筑系的限制。
原因在今日看来无疑是无稽之谈—建筑系学生需要在夜间作图,“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
这种性别限制,在那时是常见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在1936年前往美国深造,却被密歇根大学“不许女性走学生会大门”的规定劝退,最后改道前往加州大学。
但当时林徽因一身孤胆。对她作出限制的,只是一所机构不合理的规定,而非建筑学的知识。虽然建筑是静止的,但一木一石、一梁一柱所呈现的知识是流动的,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看待建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凭着对建筑的热爱,林徽因迂回地选择了入读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直到毕业,林徽因取得了建筑系的61个学分—在如今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副教授林中杰看来,“这足以证明,和建筑系最优秀的学生比,林徽因毫不逊色”。
2022年,“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在宾大举办。一众建筑学者在回顾这批中国近代建筑师海外求学之路时发现,“除了个别退学的学生,林徽因是这些人里唯一没拿到建筑学位的”。
为了修正这个错误,2023年10月1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发布消息:“在明年5月18日的毕业典礼上,将向林徽因—这位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性建筑学家,颁发迟到的建筑学学士学位。”这场毕业典礼,迟到了100年。
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说,“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错误”,而错误的起点,在于林徽因的女性身份。这场针对性别的偏见,在林徽因诞辰120周年,终于被纠正。
但对于公众来说,长期以来,这位民国才女,她的外貌与性情,她那《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诗篇以及文学家的身份,甚至是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民国大师真真假假的感情传闻,比她作为共和国首位女性建筑师、她对中国建筑学术的贡献,更被人熟知。
这种对外表的肤浅关注,为性格直爽的林徽因所反感。好友金岳霖曾记载过一则轶事,他夸赞林徽因为“林下美人”,但遭到了她的责骂:“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
女性要做的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对林徽因来说,文学只是爱好,建筑师的事业,才是她终身热爱、终身奉献的“一项神圣事业”。
民族觉醒
林徽因对建筑的热爱与学问,始自一次与父亲林长民在欧洲的游历。
1920年,此时已辞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派赴欧洲访问考察。在林长民外出公干时,林徽因总跟着作为建筑师的女房东外出写生。
建筑(architecture),不只是房子(home)或建筑物(building),而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林徽因对建筑的热情,归国后直接影响了“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的梁思成。
2023年10月1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发布消息:“在明年5月18日的毕业典礼上,将向林徽因—这位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性建筑学家,颁发迟到的建筑学学士学位。”
1924年6月初,两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宾大留学。虽说当时的美利坚大陆上,有林徽因“所喜欢的民主精神”,但她心系的,始终是中国大地上长久伫立却正在摇摇欲坠的古建筑,还有那个撕裂破碎的家国山河。
在接受当地一家媒体访问时,林徽因谈及了当时国内建筑艺术研究冷清,但又迫切希望跟上世界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