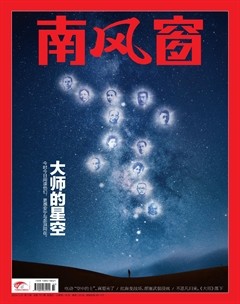《我的真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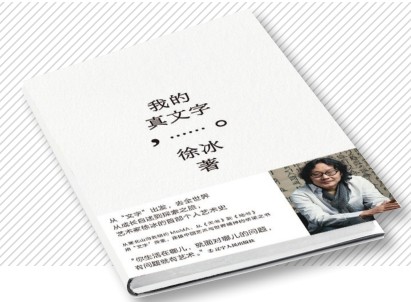
单看徐冰作品,总会不自觉地想到现象学、符号学云云理论,愈想愈复杂。刚开始,是作品本身带来的震撼和这种意识游走的兴奋,而后却逐渐深陷于复杂而深刻的思索,在“过度思考”中怠倦了。
到如今,“徐冰”似乎也成为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概念,任社论言说,愈加陌生,留下一片模糊而抽象的雾霭。而在《我的真文字》中,并不透过艺术品,而是从文字上了解他,阅读徐冰的随笔,他与人通往的信件,这又让“徐冰”本身清晰亲切起来。
徐冰的作品被抛入社会,解读层出不穷,最终似乎只是被固定成当代艺术词典中的“徐冰”词条而已。但这种现象也是有趣的,其中有许多层“真”“伪”的圈套:徐冰这个符号概念的指向,与徐冰本人所指的不同;观众审视中对徐冰作品的抽象印象,作品本身的呈现以及其原本的创作意图之间的交织;他在艺术创作语言中的表达,与通过文字、口述传达的表述之间的重叠与分离……
如此说来,不可直接把“阅读艺术作品”等同于“阅读徐冰”。这些艺术作品在环境中已然“自行”生长出了新的意义,将对作品的评判直接归结到艺术家本人身上,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现在对他作品的印象,甚至直接的观看,都已与他本人当下的存在隔了数层关系,甚至作品当下的存在语境与艺术家本人也是有些脱节的。
评价作品没问题,但又因它们已被深深烙上了造物者某一生命阶段的痕迹,艺术家必须对它们负责,二者不可避免地被连接在一起—这着实有些像父母与孩子的复杂关系。在此,私密性尚存的文字或许更适合用来了解他本人。
“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徐冰的文字有一种谦逊的自明,他诚恳地相信着自己能做的艺术,也洞察着四周向他的作品、向他投来的目光。大概可以这么说:在这本书中,他对自己东西的批判比任何人都要猛烈。确实没太够有学问考究的,有的作品的确是不成熟的,许多东西只不过是想做,且做了,最终做成了—这已弥足珍贵,这些细节也都在他的这本 《我的真文字》中一一说道。
知青经历对徐冰影响颇深:在杏树下读“毛选”,享受自我克制的同时读一读有关文艺的论述;他为老乡们演示书法、设计黑板报,参与共同创作的刊物字体设计,诸如此类,被他记在《愚昧作为一种养料》的随笔中。
徐冰就读央美期间,有老师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