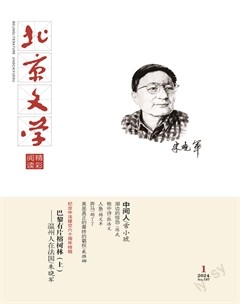1
我是在小区便道上见到庞大萍的。
我开始没有认出她来。她也没有认出我。我们两人目光对视一下。我发觉这个即将和我擦肩而过的女人既陌生又面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激发了休眠已久的大脑深处的某根神经。于是再看她。她也再次看我,眼神疑惑而闪烁。闪烁的眼神我见多了,疑惑的眼神当然也有,一直保持疑惑的眼神不多见。我深感奇怪,朝她一笑道:“我们认识……”
我的话里原本不是省略号,应该是问号或惊叹号。但,此时,只有省略号更合适。
她说:“你是不是阿昆?”
我说:“是啊。你是?”
她脸红了(四十多岁的女人还脸红,更是稀有),笑也不自然地说:“我是庞大萍啊……”
庞大萍?天啊,我们三十年没有见面了。我心里迅速计算着,1997年,到现在,二十六年。二十六年可不算短,离三十年也没有几年了。这么久了,我还能发现她面熟,她还是眼神疑惑乃至一脸疑惑,时间这把杀猪刀,还没有把岁月的遗痕彻底斩断,还留下挥之不去的久违的记忆。不知为什么,我心头悚然一惊,瞬间回到1997年春天。
遥远的1997年清晰地再现了——那年春天特别寒冷,二月末,一个衣着单薄、精神抖擞的女孩坐在电脑前快速打字,手速非常快,快到我眼睛都跟不上她手指的移动。而她的手又异常漂亮,圆润、白皙、细长,手面上还有几个可爱的小肉坑。我被她的手和手速惊到了。当她发现我一直在看她时,她也抬眼看我,就在眨眼之间,她手指至少又敲出十个汉字,电脑屏幕上的汉字在飞速地移动。可能是我怪异的表情引起她的反感吧,她用疑惑的眼神仿佛在问,干吗这么夸张?我迅速收敛我的失态,从她身边往厂长室走去。我感觉那疑惑的眼神还在身后一直追着我。
当厂长吴天领着我再来到她身边时,她又疑惑地看我一眼。
“介绍一下,”吴天擤一下鼻子,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响,然后才说,“陈昆,我们印厂新客户。庞大萍,最擅长排版——其他员工手里都有事,你们报纸就由庞大萍来排。萍,带点心。”吴厂长的一句“萍”,可见其亲密程度,“带点心”,也不像是一个厂长对下属的工作安排,仿佛是家居生活的日常用语。我还发现,吴天在互相介绍我们时,一双大手还似有若无地搭在庞大萍的肩膀上,在说话过程中,至少轻轻拍打了两次。他们是什么关系?吴天是个精干的年轻人,跟我年龄相仿,有可能还小。庞大萍看样子只有二十岁,甚至更年轻。他们是什么关系?夫妻?不像;恋人?有可能。
这便是庞大萍和吴天给我最初的印象。
“你怎么在这里?”庞大萍说,疑惑的眼神穿越二十六年,并且脚步也停了下来。
我也停下来,和她对视着。如前所述,她疑惑的眼神不是需要疑惑时才疑惑,而是成为她器官的一部分,一直疑惑着,就像她幽深的浅蓝色的眼白一样,让人联想到忧郁、怨艾一类悲情的词汇。这么多年了,这种表情居然一直没变。我赶忙说:“我住在这里。”我努力平静着自己欢快的心跳(事后我也深感奇怪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让语气自然一些。
“哈,这么巧,我也住这里……”像她当年的汉字录入速度一样,她语速也很快。
但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大约十岁的样子。小女孩喊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庞大萍显然听清了,她急不可待地朝我身后挥手,就是朝那个小女孩挥手,又对我说:“先去啦。有机会聊。”
我站在原地看她。她小跑几步,牵着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向小区大门快速走去。她背影还是那么熟悉,发型也没变,短发,随着急速的脚步而飘动。行进中,她扭回头看我。她发现我也在看她时,又跟我挥手。她挥手的幅度很小,像她眼神一样疑惑着。我也跟她挥着手。我感到我挥动的手臂有点滞涩——我坦白,当年我们在工作上成为合作者时,我很快就爱上了庞大萍,她也知道我爱她并对我有好感。但我们的爱情在萌芽阶段,就被扼杀了,“凶手”正是厂长吴天。
2
在苍梧书斋茶社里,我向书斋主人胡小妮咨询一些茶艺培训的事。她是个很斯文的85后女孩,漂亮又知性,开了多年茶社,也卖茶叶并兼做茶艺培训,据说,还是个摄影艺术家。对最后一个头衔,我心生怀疑,手机时代了,谁都能利用手机功能,拍出精美绝伦的照片来。摄影还敢称艺术家的,不是愚蠢,就是厚颜无耻。我是经朋友小米粒介绍来向胡小妮请教茶事的。小米粒是年轻的心血管方面的医生,交往甚广。由于我和她父亲是好朋友,知道我退休回到本地定居后,她承诺当我的私人保健医生(我知道这是开玩笑),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就是在吃饭时,我向她透露了退休后的打算,其中之一,就是学学茶道,便于重新结交一些朋友,为下半生的退休生活做好铺垫。可能是女孩子之间相互了解吧,她就把她的好朋友胡小妮介绍给我认识了。
清明刚过,春茶正好,我一邊听胡小妮讲茶经,一边慢品她冲泡的云雾茶,并欣赏她冲泡时的各道程序。但是,说真话,我在品茶时,走心了。我脑子里一直想着刚才在小区里偶遇的庞大萍,想象着她如今的生活,想着她还能记得我,想着既然同住一个小区,说不定以后还会见面。而她肯定早就结婚了,和谁结婚?吴天吗?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儿应该是她女儿吧?二胎?有可能,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适婚年龄来推测,她的孩子不应该才十岁左右,至少二十岁。于是记忆的河流再次泛滥,当年编辑企业报时的许多往事开始呈现。
二十六年前,我二十九岁,是一家药企的普通工人。企业入驻开发区以后,规模迅速扩张,已经成长为市里同行业第一。企业非常重视文化,要办一张文化报。领导知道我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又在厂办做过多年新闻报道,就任命我为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如前所述,我第一次看到庞大萍时,是在开发区激光照排印刷厂里,她正在激光照排室(简称电脑房)练习五笔输入法。我当时少见多怪,被她输入汉字时的手速惊到了。
第二天,吴天电话通知我来校对时,我就坐在庞大萍隔壁的另一个隔断里,我发现,庞大萍只要有空闲,就练习五笔输入法。她的五笔输入法已经够牛了,为啥还要练?这个疑问很快就解开了——她突然站起来,朝我笑。她的行为让我受宠若惊,也傻傻地朝她笑。她笑得很好看,未开口脸先红地轻声道:“老师,能不能把你现在不校的稿子再给我一篇?我要练练字,下周到市里参加汉字输入比赛,用手写的稿子练习能提高头脑反应速度和手速。”
怪不得,原来她要参加汉字输入比赛,所以才敬业地加练。我就找出我为副刊写的一首四十多行的爱情诗和一篇散文给她了。我一边校对,一边听她练字时敲击键盘的声音。在整个电脑房里,有十几台电脑分布在一个个隔断里,能够让电脑键盘发出美妙声音的,只有她。这个感觉非常好,仿佛她敲击的不是我的诗,而是在朗诵我的诗——她用心语在朗诵,并通过键盘发出动听的声音。我分心了、分神了,还有一点点感动。我站起来,看她打字,朝她微笑。她停下,嘻嘻地回应着:“啥事?你的诗和散文已经打过一遍了,这是第二遍……不不不,算上昨天的录入这是第三遍。”
我惊讶道:“这速度太快了。”
她说:“不算快,我都担心拿不到名次呢,领导可是对我寄予很大希望的。”
她说的领导,就是吴天吗?我对吴天印象极其不好,虽然昨天是第一次见面,可他的撮鼻子,还有一双手总是拍打庞大萍,让我厌恶。撮鼻子是他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毛病,在别人的肩上或胳膊上拍拍打打,算什么呢?人品坏。但是他是庞大萍的领导,也是印刷厂的领导,这就没有办法了,印象再不好,也要跟他合作——整个开发区,只有这一家印刷厂,还是全市最先进的印刷厂,领导也认可这家企业,我没得选。
“你怕领导失望?”我说。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领导不值得你为他拼命。
她听出来我这句话的潜台词,脸红了。
我又重点夸她道:“你这么厉害,肯定能得奖的。”
她露出了羞涩之情。我被她这种单纯和可爱所感染,就这么看着她,心里也跟着美好起来。这样的状态几乎是处在定格或静止中,周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站着,居高临下看她;她坐着,仰着脸回应,微笑、羞涩,还略有点惊慌。
就在这时候,吴天突然出现了,一点预兆都没有,吴天简直就是从天而降。按说吴天从电脑房那边的厂长室走过来,至少有十几米的距离,又是一个大活人,我和庞大萍怎么会双双没有注意到他呢?当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现在我和庞大萍深情对视的现场了。就在我和庞大萍发现他已经置身现场的同时,他说话了,声音客气而严肃:“萍,你干你的活,好好工作,别打扰客户!”
他说别打扰客户,其实是正话反说,是说我打扰了庞大萍的工作。庞大萍的第一反应就是继续投入录入训练。我对吴天解释说:“我是在向小庞老师请教……”我本想说出具体请教什么的。但我反应还是迟钝了,“请教”后边一时没有想好。
“噢……”吴天看我没想好说辞,也给我面子,邀请道,“陈老师到我办公室喝茶来?”
那天有没有到吴天的办公室喝茶,忘了。我现在是在胡小妮的茶社喝茶,准备请教一些和茶相关的知识。
就在我心猿意馬、心神不定时,进来一个神气活现的人。因为心里正想着吴天,这个人一下子就变成吴天了。嚯,太神奇了,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让我在一天之内,同时巧遇两个二十六年前的熟人?
“你不是说下午来吗?”胡小妮对来者说,声音不高,口气是不悦的,并带着风骨,说完后才站起来,仿佛象征性地出于礼貌,并非真心实意地欢迎他。
我看到吴天瞥我一眼,很认生的样子。显然,他没有认出我来——莫非我认错啦?他不是吴天,或者说,不过是一个酷似吴天的人?再或者说,因为庞大萍,让我想到了吴天,看谁都是吴天了。不过吴天有个习惯性地擤鼻子的动作,下意识的,带点抽搐感。如果他一直没有擤鼻子,说明他不是吴天。如果擤鼻子,就是了。
来人很直接:“妮,我来跟你说个事。”
“有客人了……等会儿来吧。”胡小妮的表情平静,让对方等会儿来,其实就是逐客令。
来者称胡小妮为“妮”,这可是吴天惯常的语言习惯。就在这时,来者突然擤一下鼻子,发出“噗”的一声响——果然是吴天。吴天的另一个习惯性动作也出现了,即试图拍打或抚摸胡小妮的肩。胡小妮肩膀一闪,躲过去了。吴天被她躲肩的动作闪了一下,或者对她的躲肩不适应,霸道地说:“那好……我去茶室坐会儿,等你。你们先谈。”
吴天轻车熟路地走进一间茶室。这间茶室的门边,挂着刻有“春风”两个书法体的旧木牌,门窗里的窗帘布是手工的印花粗布,很有年代感,既可以起到窗帘的实用功能,又有装饰效果。
我感觉到他们很熟,至少曾经很熟,熟到不拘小节的程度。同时,从两人的对话和表情看,又说明他们之间有事儿了,这事儿还不小,而且,胡小妮应该知道吴天要“说个事”的事是什么事。果然,胡小妮看着被吴天带上的茶室的门,对我小声道:“对不起陈老师,等我一会儿……或随便看看,对了,谷雨包间有我新挂上去的十几幅摄影作品,你看看,提提意见——听小米粒说你是一个摄影家。我去一下,马上好。”
3
“谷雨”是苍梧书斋茶社最大的一间茶室,有一张老船木的巨型茶桌,可供二十人同时饮茶、教学或开会,装饰也别具一格,特别是墙壁上挂着的十几幅摄影作品,打眼一看,就非同凡响,所反映的都是鸟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主题,从拍摄的角度、光影和构图来看,都极其讲究,极具冲击力,非高手莫办。这些摄影作品和说明文字,都署名胡小妮。
她还真是个摄影家。我立即就惊叹了,联想到小米粒对她夸奖时我的不屑一顾,便很有些自惭形秽,觉得我以己度人,太武断太偏见了。
我在这些作品前慢慢欣赏,每一幅情态都不同,我被胡小妮的抓拍技巧所折服。其中一幅作品尤其出色,画面上有一只鸟(我叫不出名字),刚落到它的巢上,翅膀还在扇动,脚还没有落稳,尖尖长长的嘴里含着三条大小相当的青虫子,而巢里的四只刚出壳还没有长毛的雏鸟,同时张大着嘴,等着鸟妈妈的投喂。这幅作品让我震撼,特别是鸟妈妈焦急的身体语言和雏鸟夸张的与幼小身躯极不协调的超大嘴巴,都在强烈地昭示母性和母爱的伟大。同时建筑在五根笔直的青芦秆上的精致的鸟巢,那一根根纤毫毕现的金色的草丝和环环相扣的精密的工艺,要费多大的工夫和精确的计算啊。此外,我还被胡小妮所震惊,如此平视、动态的抓拍,如此清晰的近距离,都要付出相当大的辛劳和长久的等候才能做到,而且自己还要做好伪装,不能被鸟发现,太不容易啦。
这幅作品的名字也有意思,《三条虫子和四张嘴》。但是,我想了想,虽然完美诠释了画面,但似乎还不够味儿,应该有一个更妙的名字才能和这幅作品匹配。起个什么名字呢?我年轻时写过诗,这会儿也词穷了。
如前所述,我曾经也是摄影爱好者,拍过不少片子,甚至自认为水平很高。但是在胡小妮这几幅作品面前,还是相形见绌了。她用的是什么相机?我以前使用的只是普通相机,现在都是用手机拍。她的相机一定很高级吧?我这么想着,下意识地在茶室里环视一圈。我看到茶柜的底层,果然放着一架相机。凑近一看,隔着玻璃柜门,我认出了相机是佳能1DMarkI∨,而连着相机的镜头更是夸张地粗大。这哪里是镜头啊,简直就是一门大炮,是佳能400mm光圈F2.8定焦镜头。我认识这款,我一个摄影家朋友简称这款相机为佳能428。而镜头上,还罩着价格不菲的防雨套。从装备和作品看,胡小妮不仅是一名出类拔萃的茶艺师,还是一位不俗的摄影家。我觉得我找对人了。我不仅可以跟她学茶艺,还可以和她探讨摄影。如果可能,还可以和她的影友们一起出去搞创作,说不定也能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来。
正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像是东西摔碎的声音。没错,应该是某种瓷器,清脆而尖锐。我担心是茶台(酒吧叫吧台,茶社就称茶台)那儿出事了,立即跑出来,看到的却是胡小妮从“春风”茶室里摔门而出,而且脸色铁青,神情愤怒。我立即确认刚才的声音,不是瓷器的摔碎声,而是胡小妮发出的尖叫声。
同时被惊吓到的,还有茶台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神情发呆地看着胡小妮。
胡小妮和吴天,在一间隐秘的茶室里谈话,突然发出异常的尖叫声,什么情况?
紧随胡小妮出来的,是吴天,他和来时一样,夹着一只黑色的小皮包,神情复杂,和来时的神气活现判若两人。他径直向门口走去。
从各自神态上看,他们之间肯定出问题了。
我是今天才认识胡小妮,不便多问。她当然也不会主动跟我说什么。她情绪受到很大影响,甚至都忽略了我的存在,手足无措般地坐到刚才和我聊天的那张茶桌前,一连喝了几杯茶。她这样的情绪不可能再谈什么了;即便勉强谈了,效果也不佳。我便谨慎地跟她打声招呼,准备告辞。未承想她抬手示意一下,说:“坐,过来坐,喝茶。”
我只好又过去坐在她对面了。她给我一杯茶,朝我一笑。我看出来,她给我递茶的手在微微战栗,有点像痉挛;她的笑里,也藏着某种艰涩,显然她还沉浸在某种情绪里没有走出来。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夸大其词地夸了一通她的摄影作品,说她的摄影作品是我见过的最有个性也是最好的作品,很感人、很治愈。并且还拿我的作品和她的作品进行比较,以贬低我的摄影技巧来衬托她的摄影技巧的高明。我的目的是转移话题,让她尽快从灰色、低落的情绪里走出来。但她还只是笑笑,情不由衷,对我的夸赞不置一词。那笑也毫无着落,不知散落到何处了。既然这样,我就什么也不说,陪她坐一会儿吧。
让我没想到的是,吴天又回来了。
吴天没有经过邀请,也没有得到胡小妮的同意,坐到了茶桌前,就在我身边。我确认他没有认出我来。我也确认,胡小妮对于他的回来还是得到了某种安慰。同时我还确认我再待下去就多余了,便正式告辞。我出门后还想,经过各自的冷静,也许他们接下来的交流会比刚才理智多了吧。但是,他们是什么关系呢?这个社会太复杂,人际关系也太复杂,凭我目前的认知,还无法想象出来。
4
回到小区,我走在小区的绿化道上,脚步迟疑着,朝各幢高楼上仰望。这是北京怀柔的高档小区,住宅有几种模式,高层、多层、排房、连排别墅、独栋别墅。高层是最低档的公寓房,就像我买的那种。其次是多层。排房、联排别墅和独栋别墅属于高端住宅,特别是独栋别墅,不是一般人能住得起的。我不知道庞大萍家住在什么区域。这些年了,她住什么档次的房子都有可能。只是早上没有问清她住哪幢楼,连联系方式也没有留,在这么大的一个小区里,要想和庞大萍再偶遇怕是不太容易。就算遇到了,我搬来三个月才遇到这一次,按照这个概率,至少还有三个月我们才能见到第二面。想到这里,心里便失落起来,说明我还是想再见到她的。
这个小区规划好,绿化好,管理好,附属设施好。我买的是二手房,不大,小两居,90多平。原房主是个90后女孩,因出国读书而转手卖给了我,又因是全款一次性付清,还优惠了不少。今年春节一过,我就搬了过来,到目前还都满意,内心已经决定,就在这里养老了。我当然还没有很老,但也不年轻了,刚刚成为退休人员。据说五十五岁也是个坎,不适合油腻了,也不适合拼搏了。从这时候开始,就要追求一种平静的生活,钓钓鱼啊,学学茶艺啊,重拾当年的理想做一名诗人啊,或者把我的摄影爱好再发扬光大啊。光靠茶艺,还支撑不了我的全部生活,像胡小妮那样做个业余摄影家,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我和胡小妮还没有深谈就被吴天给耽搁了。对于我来说,吴天就是个灾星、克星。当年就是他搅黄了我对庞大萍萌发的感情,难道我后半生的业余生活,也会坏在他的手里?这家伙,每次都是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
就在这时,胡小妮的电话来了。
胡小妮说:“真不好意思,刚才失态,叫你看了笑话——这个人是个神经病……你还在附近吗?我们还没怎么说话呢。你再过来吧,或者下午过来也行——下午有个小班,就是几个朋友来学茶。我听米医生说你退休了,想学茶,过来玩玩吧。对了,你刚才说也爱摄影……真是太好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聊摄影。”
胡小妮的话节奏很快,我都无法插嘴,这么快就处理好她和吴天之间的不快啦?感觉他们之间的问题挺大似的。但是从她的语气中,似乎是处理好了,不然,她不会约我下午和她见面——无论是学茶艺,还是谈摄影,都是我乐于接受的。
胡小妮所说的米医生,就是小米粒,她姓米,小米粒是她微信名。那个“神经病”当然是指吴天了。用神经病形容吴天,倒也贴切。可不是嘛,当年在印厂的时候,我就发现吴天一些诡异的行为。我们原先并不认识,是因为在筹备厂报出版时,我才到印刷厂和他接洽并认识的。这是新成立的厂,规模不大,领导班子人也不多,算上他本人,另有两个副厂长,一个从别的印刷厂挖来的懂印刷和设备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个副厂长分管财务和外联,吴天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电脑房。在我编厂报的短暂期间,和我直接打交道的,只有他和庞大萍两个人。出第一期报纸时,吴天就曾鬼祟地跟我说,别看庞大萍(这次他没称萍)年轻,她人小鬼大,手里抓着好几个男的在周旋,我怕她越滑越深,就把她招进厂里了。吴天的话我听明白了,至少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庞大萍在没有进厂之前,生活作风混乱;二是,他和庞大萍关系不一般,是他把庞大萍招进厂里委以重任的。当然还有别的意思,比如是在提醒我,甚至是在警示我,让我别打庞大萍的主意。因为我和庞大萍就汉字输入比赛进行短暂交流时被他看到了。我们厂报一月两期,从把稿子送到电脑房,到校对、核红、改版、调版、签付印,每期报纸要经历三四天时间。在这三四天里,和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庞大萍。按说这不过是一项普通的业务,第一次把我介绍给庞大萍之后,正常开展工作就是了。但是,每次我们出报时,吴天都对我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只要他在,就会时不时地来跟我打招呼,问上期报纸满不满意,给我送茶、添水,或问我需要什么,同时,又对庞大萍的工作提出严格要求。那些严格要求的话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关怀。即使这样,在此后半年时间里,我对庞大萍的好感也没有消退,而是渐渐加深,特别是,当我知道吴天已经是个已婚男人后,便萌生追求庞大萍的意思——我能感受到,庞大萍对我并不反感,她几次帮我打印稿子时,夸我文章写得好。还主动说起了那首诗,说她能在比赛中拿到第一名,多亏我提供的稿子。我当然知道,她能得第一名并不是因为反复录入我那首诗,也不是因为那首诗好,而是她本身的实力过硬。她之所以这样说,无非表达一种态度。在交流中,我知道庞大萍才十八岁,比我猜测的二十岁还小,她去年高考失败,就进入一家个体打印社,练就一手超乎常人的汉字五笔输入技能。吴天因为在印刷厂筹备时,需要打印各种材料,发现了庞大萍,就破格把她招进了厂里。庞大萍对他表示感激。吴天也把这种感激当成理所当然,承诺要重点培养她。这些都是庞大萍说的。吴天是已婚男人的话题也是她说的。我把她这句话理解成一种暗示,也即是对我示好的回应。有一天,她悄悄帮我打印一篇小说后,我要请她晚上吃饭,感谢她的同时,也准备向她明确表示我对她的爱。她在脸红之后,面露疑难之色地问我能不能改天。我答应了。但是,在当天一下班,我看到吴天开车把她接走了。第二天我再约她时,她拒绝了。不久,我从另外的途径知道,吴天离婚了,正热烈追求厂里的一个漂亮小女工。我知道这个小女工是谁。这个消息让我特别难过,同时也知道她为什么拒绝了我的邀约。我极度失望。我不年轻了,马上三十岁了,我知道在庞大萍面前,我和吴天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我不想再编报纸,不想再见到庞大萍,也不想再见到吴天。我的爱情才刚刚萌芽就被摧毁了,而且这是我初恋之后真正对一个女孩动心。恰巧厂里试行销售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广片区包干制。我决定竞争一个片区经理的职位。我如愿通过了面试,在三天培训之后,踏上了去贵州片区任职的旅程。这个片区经理我一干就是二十六年,一直在貴州深耕、拓展,多次被评为优秀经理。直到刚刚办理退休手续。而我个人问题,也因一直长期在外奔波,没有解决。虽然有过几次恋爱经历,甚至和贵阳一个女孩曾经同居过,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原本只想回故乡安度晚年,没想到会和庞大萍不期而遇。到这个年龄了,我并没有重叙旧情的意思,何况当时我们的关系还没有点破,形式上也只是熟人。但毕竟我们同住一个小区,能结识一个我曾暗恋过的熟人总比两眼一抹黑要好吧。更巧合的是,居然又在苍梧书斋茶社里见到了吴天。如果庞大萍和吴天终成一家,那吴天也和我同住一个小区了。
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家呢?好奇心害死狗。吴天和庞大萍的最终结局让我好奇,吴天和胡小妮之间发生了什么,同样让我好奇。
5
这确是一个小型茶艺培训班,除了我,只有三位90后女孩,她们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比一个认真——我们就坐在上午我参观过的“谷雨”茶室里,看胡小妮娴熟、优雅地表演,听她轻柔、温软地讲解。在胡小妮讲解和演示中,我喝着香茶,心思却不能集中,时不时地开小差,觉得胡小妮的情緒并没有受到吴天的影响,或者说,她消化不良情绪的能力太强,连带地,更想知道她和吴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的心猿意马、犹疑不定的神态没有逃过胡小妮的眼光,她每每用眼睛瞟我时,我就知道她在提醒我别开小差。等到两个小时的学习结束后(包括我们自己的冲泡实践),这堂课就算结束了。胡小妮提前预告了两天后的下一堂课的内容,就是品鉴号称“岁月的古董”的普洱茶,还要求大家来了就要专心和投入,别老走神——她后一句话是针对我。当三个学员陆续散去时,胡小妮主动跟我谈起了摄影。
“陈老师对摄影这么专业,我们就有得聊了。”胡小妮说。
“我那三脚猫的功夫,哪敢称摄影?”我立即谦虚地说。
“谦虚是美德。我听米医生说你办过厂报,写过诗,写过散文,很有才华,拍片子也是响当当的厉害。”
“米医生还说啥?她是我当年在开发区工作时一个朋友的女儿,在贵州医学院读书时她爸让我多多照应,我们又成了忘年交,她肯定只会说我好话的。”
“那当然,”胡小妮说,“不过也是实话,她还说,你的摄影作品得过贵阳市摄影家协会年度大奖,是不是?”
“就是一个三等奖。”
“三等奖也不得了。”胡小妮说,“陈老师现在对摄影还有兴趣吗?”
“当然有啦,正想跟你讨教呢,你这些作品才是艺术,我那些照片就不值一提了。”
“什么艺术啊,讨教更不敢了,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搞搞创作嘛。”
“那真是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