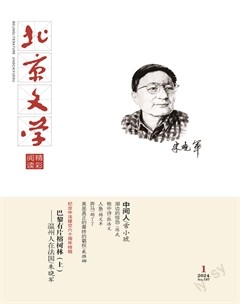上
父亲总是不在家。
在我们村里,男人不出门找点活计做,是件很可耻的事。所以情况经常是,在我睡醒时,父亲就已经不在了。他终日出门游荡在村子里,像一股风,在街巷中吹来吹去,哪里有动静,哪里就有他。哪里人多哪里肯定会有他。
小商贩叫卖的吆喝声,总是如同海浪一般,顺着村子中心的十字街,一波一波穿过胡同和院墙,传到村中的角角落落。妇女们坐在墙根,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支棱着耳朵听,酱油、醋、香油和豆瓣酱,头绳、袜子和裤头,哪样是自家需要添置的,哪样不需要,这都是过日子顶重要的。那吆喝声浑厚犹如鼓,激荡着下学后三心二意的娃娃们,各不甘人后地跑出去看热闹。而父亲,早已从那一声声诱人的吆喝声中回到了现实的家,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推开了破旧的屋门,在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上放上一些不花钱的小玩意儿,随后两袖一捋又走了。傍晚间,父亲又请来村东头那个神神道道的算命人,两个人喝酒吃菜,称兄道弟,屁股都不抬一下,既喝就喝到大半夜,杯盘狼藉,半夜到了人家告辞了,他却并不睡,又一甩袖子,吊儿郎当着跟客人的脚跟重新到村子里,在寂静的街上晃来晃去,就像村里一个没有家的魂。
这就是大我二十几岁的父亲。
他常去大槐树底下跟抽旱烟的老人打花牌,又总是呛得自己直咳嗽;和丈夫外出的婆娘们打麻将,发生口角后,都由母亲出面迎战那家的人。村里的红白事,父亲殷勤十分,从来没有落过一次,买菜待客,样样腿勤不含糊。逢年过节,人家杀猪了,他是第一个买到猪大肠的人。他没像其他在外忙碌的男人那样因提前招呼一声才买到,只是屠户住的离我家近,人家动刀的时候一喊他,他就热情地去帮一把手,刮猪毛,烧热水,提猪腿,递屠刀。自然呢,最后父亲买到的猪大肠,多得像屠户送给村主任家的礼。父亲把猪大肠捧回家里交给母亲又出门晃荡了。其他人家在置办年货准备团圆过年时,母亲就得在院子里一寸一寸、翻来覆去洗那猪肠子。那装肠子的盆,仿佛大得不着边。母亲在小板凳上坐了一下午,傍晚时候直了直腰,只见她“呸”一声,把一口浓痰吐进了卡在小腿下的不锈钢大盆里,又如梦初醒般,掬起手掌把痰舀起甩出去。
父亲如飘魂一样在外游荡着,在家的时间少得如一个手掌捧着一粒芝麻样,而在外的时间却多得仿佛一片戈壁捧着一个河滩的沙。我知道,是全村的街道把父亲的人生吃掉了,是全村的闲人把父亲的时间吃光了。
父亲总也不换衣服。一是他不爱换,二是他没有可换的。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在冬天裹着一件手工厚袄子,连罩衣也不穿;大夏天,他光着膀子,把一件黑色的圆领汗衫儿,捋成一股鞭,左肩一甩,右肩一甩,像牛尾巴似的忽闪忽闪地扬来扬去。父亲是眯眯眼,留着小平头,身子又瘦又单薄,下半身吊搭着半截裤,上半身随意地把汗衫搭在肩膀哪一端,走起路来却比谁都灵活而自如,活像一个老练的挑山工,挑着一个永远不会落地的俗世的担。可是这个担子又是很轻很空的,父亲挑着一晃一晃就无影无踪了。
父亲终于有了儿子了,可父亲还是那个人,一点也没变。反而圆润的母亲很快变得干瘦起来了。仿佛她是被一口气吹大后,又被一口一口吸瘪着。在她皴黑的脸颊上,长满了更黑的斑,像麻雀屎粘在脸蛋上。还是坐在那个小凳上,母亲抱着怀里的弟,把饱胀的乳头往弟的嘴里塞,一边说道:“我的儿啊,你快吃,吃了你好长大大。”然而这母子刚一对上眼,弟弟的嘴就咧到另一边。母亲耐着性子三番五次地将奶子朝着弟弟嘴里塞,她的奶水总如瞄不准的箭,最后都一滴滴射落在了土地这面靶子上。
有时候,母亲一边对我嘱咐着什么事,一边把她的奶头往衣服里装。她的奶水在抖动中滴滴答答,雀跃着从衬衣渗出来,然后晕开去,就像那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奶晕舍不得走。这时母亲会抬抬怀里的弟,突然右脚狠狠一跺说:
“快去把你爸那驴日的寻回来!”
我身子一颤,像掉了魂似的跑掉了。
我去找父亲。村东村西找,南岸子、北岸子,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可我还是找不到。可我这样找寻着,就把自己给找丢了。沿着寻找的路,我越走越远,直至出了村。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叔叔,叔叔认识爸,我就问他我爸在哪里。这个叔叔平时喜欢我,以前还跟我一起在十字街口新修好的水泥马路上玩过堵围墙游戏呢——他让我像猴子一样缠在他身上,背起我,把我架在他的脖子上,像抬着轿子一颠一颠的,从村子的东头晃到西头去。我得意极了,骑在他身上,就能看到每家每户的房顶子。风呼呼地吹,我看得那么远,远得好像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了。一路上,叔叔不停地问:“你爸叫啥?”我回答:“叫爸!”叔叔说:“不对不对,你再说。”我又说:“那叫我爸!”叔叔急起来:“不对不对,以后你要叫你爸——牛娃。”他教了我一路,等我学会了,便把我送回到我家的平房前。我用两只手抱紧叔叔的脖子,我喜欢被人架在脖子上的感觉,架在脖子上我就看到村子外面的世界了。到了我家门前,我被从脖子上卸下来,叔叔说喊你爸出来接你呀,我便扯着嗓子喊:“牛娃!牛娃!出来接你娃!”父亲被女儿叫了小名儿,却并不生恼火,只见他不慌不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把他肩膀上的汗衫换个肩,便从叔叔手里接过我,将我拉到他身边,然后教我道:
“快叫你利和大大(我们管叔叔叫大大)。”
父亲做什么事情都是半截子。他跟大伯分家时,把大大的老院子让给了大伯,自己却在老村旁边的新庄子里,购置了一块要填埋的狭巷宅基地。那块宅地原先是坑塘,满是野草和飞虫,村子发展起来后,又布满了垃圾和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