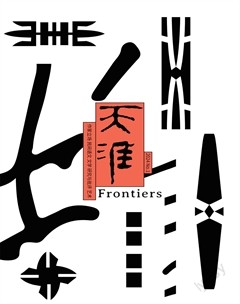一
白先生从未踏出鹿门书店一步,这间书店开张至今,也从未有顾客上门。书店前院的东北角,一架书柜,两张玻璃钢瘦腰椅,围着一个黑黝黝的火盆。火盆原是瓷白色的,书烧得多了,就成了黑色。这种黑色,是随时向人宣誓效忠的,是失去欲望的深夜狂潮退去之后,残留于日间的一抹堕落的灰烬。
白先生随手取出一本书,一页页地撕,残页再对折撕成两半,他陶醉于书页发出的悲鸣,更陶醉于烧书时那种介于生与死的灰烬味。老榕树里的鸟将鸣未鸣之际,他屏息聆听,黄昏的绿影千方百计地将鸟掩藏起来,鸣声依然流出了树心的欲望,犹如水晶雨点从翠绿云层中洒落。
白先生点燃了火盆里的书页,注意到身侧空空如也的座椅,就在火与鸟鸣的秋光里,他想起了鹿溪。
这座城市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人不如鸟,总喜欢用其他的东西替代他们的喉舌,鹿溪的舌头恐怕是被他的画咬掉了。白先生事后回想,如果鹿溪没有遇见国画,人生会是另一种光景,如果他没有遇见鹿溪,他还是原来的他。
在这样的城市,白先生的书店小得聊胜于无,他一时心血来潮,招聘了一名暑假工。无论是谁,都需要有人走进这间书店。鹿溪就读于深圳一所普普通通的高中,高高瘦瘦的,鲜嫩的胡须欲黑还灰,全身只有那件校服有一点可取之处。他来应聘时,白先生注意到他的衣服、头发凝结着清冷的白露,或许他来自一个秋风夕起的黄昏。后来,当白先生决定出门寻找他的时候,映入他眼帘的也是那片未响应的暮色。时间失去了它的进程,这令整座城市看起来都软趴趴的,摩天大楼、老村、古祠堂和他的书店,所有的建筑体内流淌的字符血液凝滞不动。
鹿溪在做自我介绍时说他喜欢国画,并向白先生展示他的新作:水墨舒散的云山,分不清性别与年龄的云寡欲无为,春色在树木的骨骼间晕开一团团心事重重的绿,苍老的山皱着眉头,细看之下又似摩天楼群,拥有三个影子的少年正在云烟飘渺处登天,脚下是无形的台阶,头顶是冷漠的月亮。鹿溪问,你认为他是要去摘月还是入月?白先生问,为什么画里的人会有三个影子?鹿溪的眼里浸透着一轮郁郁寡欢的月亮。这样的月色,就是答案。
白先生于是有了期待,國画里的书店是一种全新的解读,那是庄子遇见了孙悟空。他希望鹿溪将其画出来,让他拿到焚书角烧掉。这是鹿溪第一次遇到有焚书癖好的人,他注视着白先生,眼神发出淬炼艺术素材的笑意。
于是,焚书角多了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白先生是在鹿溪缺勤的一个星期后,才意识到焚书角的座椅重新空了起来。仔细回想,鹿溪并没有给书店带来多少幻想的热度,他自身甚至比书店更加缺乏冒险精神,仿佛他的生命在另一个时间进程里。
白先生得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另一个被世人遗弃的解剖标本。鹿溪也是被这座城市剥夺了想象力的局外人。他那愤慨的血肉可以点燃太阳,早衰的心却成了一颗白矮星。白先生知道那种感觉,身在人海之中,找不到一个愿意跟你视线交触的人。人海就是死海。
暮光碎了一地,无人光临的书店静得有些让人活不下去,白先生决定出门寻找鹿溪。
这座城的街道一直在疯长,现代楼宇犹如一层层凝固的巨浪。白先生内心深处有一个秘密:他对这座城市怀有难以言说的恐惧感。他曾做过一个梦:深邃的海底沉眠着一头没有头颅的古兽。这并非他的恐惧之源,他躲在书店内,只为了避免被门外的海洋溺死。他亲眼目睹这片海洋溺死了无数光阴的讲书人。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之心,他永远进化不出能在这样的海洋呼吸的鳃。
白先生以囚徒的姿势站在书店门槛上。鹿门书店的寂静同样浩瀚无边,深似海,他在里面活得太久了,早已忘记了不敢出门的缘由,但身体还一直记得。他的脚尖始终保持在门槛外缘内侧,连一毫米都不敢超越。他的灵与肉,成了临时的敌人。
出不出门,这是一个问题,他知道只有迈出去,外面的人才能进得来,他也知道外面的人正等着一层层地剥开他的果皮,企图唤醒果核内的十三名虐待狂,他什么都知道。他眼里的雾影渗入了心脑,本能占了上风,身体乖乖地走回书店。老榕树下的座椅披挂片片新与旧的落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落叶外,座椅已经找不到其他的饰品了。他坐下去,拿出手机翻看鹿溪的朋友圈。最近更新的信息是那幅山水画,鹿溪打上了画名——《三个影子的人》。
白先生给鹿溪发了一条信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手机悄无声息。他又发了一条语音。晚风翻起了层层的夜浪,他摁亮了书店里的灯。这一刻起,他的世界存在两种灯光:一种是书店的灯光,懒懒散散,透出一种秘密的温暖,宛若无头古兽的体温;另一种是除此以外的灯光,说谎的,虚假的,戏弄的,每一道光影都有一个癫狂的名字,每一道光影都纠缠着无数的趋光虫。
白先生打了一个冷颤。深海海底的无头古兽藏着一个痛苦难安的秘密。或许是它将自己藏在了这个秘密里面。白先生知道自己总有一日将会面对它。出于逃避这种命运的本能,白先生给鹿溪拨打了语音通话。第一通没人接。他非常有耐心地拨了第二通。一个急躁的烟嗓音在电话另一头叫了起来。白先生按住加快的心跳,抓起玻璃桌上的一片落叶,捏得手指关节发出紧张的声音。
你到底是谁?一个烟嗓音问。
白先生听到刀砍木砧板的声音,有种置身于一个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现场的恍惚感,凶手喊着下一个就是你。他慌慌张张地挂断了语音通话。秋夜漫漫,冷汗如露。白先生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的灵魂得了枯萎病,承受不起半点人间烟火的焦味。溺死时间的,不单是外面的人世之海,还有他自身的怪诞观。
这时,电话铃声追了过来。他本能地以为是快递或外卖,鹿溪的头像在手机屏里跳动。白先生的心跳转移到他的手指上,他恨铁不成钢地咬了咬手指,终于逼迫它以心平气和的姿态去按下接听键。
你是不是鹿溪的同学啊?
我……是他的朋友。
哦,原来是朋友,那你找我儿子有什么事?
就是……他之前不是在书店上班吗?这几天都没来了,想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上班?我没听他说过,那老板有没有给他发过工资?
白先生愣了一下,仿佛听到来自另一个人世的风声。他组织了一下语言,还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就是有了,那间书店在哪里?
白先生报上了地址。对方说了声“我收档后过去拿”就挂了电话。
“烟嗓音”站在书店门口时,书店吐出的光与街灯将他的身影渲染成一个扭曲的生命体。这名中年男子的头发黑的软,白的硬,这令他的眼神显露出矛盾性——妥协的漠然与生存本能的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