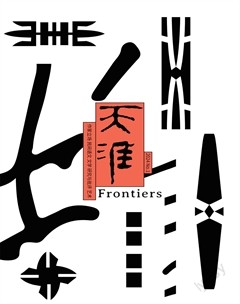资料提供者附言
2018年,我在构思并试图写作长篇小说《回响》。每天面对电脑,却写不出满意的情节和细节,于是删删改改,毫无进度更无惊喜,整天都泡在虚掷光阴的内疚里。为了对得起自己消耗掉的时间,便在写不下去时记录梦境,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还在写作,还能写作。但梦不是每天都有,而写却必须进行。非常神奇,自从我决定记梦后,梦就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仿佛自己在讨好自己抑或梦在讨好手指,以至于我每天都是先记梦再写小说。梦是现实的投射,没有无缘无故的梦。梦也是一份心理学样本,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出潜意识,而又从潜意识里看到环境?任何时代的浩瀚之梦都由无数个人的梦汇集而成,就像点滴以成江海。这是一次没有设计的记录,真实是它的唯一原则。到了2021年9月8日,我的记梦行动中止,原因是《回响》的写作顺畅了,而梦也越来越少了。当我专心于正业时,副业就慢慢淡出。
2018年1月6日,周日
昨晚梦见自己回到家乡,在我就读和工作过的天峨中学打篮球(我的脚踝因打篮球受伤,半个多月没摸篮球了),与杨秀高(当年的体育老师)在中学面向公安局那一方的坡上打球。球场是新开挖的泥地,临坡一面没有防护,我担心篮球会随时飞下坡去。杨说我们会把球护住。我把正装脱在地上,换上运动服,在篮下投球。梦中隐约感到脚踝疼痛,匆匆收工。
这两天往返于深圳,去书城“深圳晚八点”讲课,在车站走了太多的路,惊动了脚踝。
2018年1月10日,周四
昨晚梦见自己提着几个行李箱去飞机场,到了路上,看见一列车,很长,像地铁的车厢,但是停在马路上。室内装修是S型座位。我上车找到一位置,放下手中行李,转身欲下车再去提放在路边的行李。车忽然动了起来,我跳下车,原先在路边等我的一对作家夫妇不见了,我放在他们身边的行李也不见了。那列车开走了,我顾此失彼,两头的行李均失。焦急,寻找,但都没有结果。最焦急的是丢失了电脑包,里面有重要文件。正在悲催之际,醒了。就想,梦境中的难题可以用醒来解决,但现实中的难题却不能在梦中解决。
中午,趁坐南航飞机回南宁,在机上睡了一觉。梦见一位著名评论家带着几个朋友到我的家乡谷里。准备吃饭,我进屋找酒。屋内的陈设却是南宁的次卧室和铂宫工作室的陈设。翻遍所有纸箱,竟然不见一瓶茅台。我收藏的所有茅台都消失了。我非常内疚,先前说好要用茅台招待他们,现在连一瓶都找不到。只好找了一瓶别的牌子的老酒,结果大家一喝,都摇头。这是第一次在飞机上做梦。
连续两梦都是丢失,可见这几天的焦虑。一是焦虑小说创作的进度缓慢,甚至没有时间创作(时间被会议和各种活动占用);二是焦虑过几天又要到北京跟陈建斌导演修改剧本。
2019年1月11日,周五
午睡,梦。作家朱山坡告诉我,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了广西,准备去北海。我一路打听,他到了我家乡天峨县。于是,我赶到天峨。他正跟一桌人喝酒。他说这几天太紧张劳累,今天要喝醉,放松一下。我加入餐桌,一一敬酒,才知道,他是被一位女老板请来的。他喝得高兴,竟然跳起了街舞。我跟他商量到学校做讲座事宜。他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我忘了。他说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没看过,叫“肝什么”?这部电影讲的是建筑搬迁和平移的故事,他正讲着,我醒了。
这是一个与现实对应的梦。早上,学生论文预答辩,杨教授说了一个电影名,我没有看过,梦里出现了。午饭时,我去电联系北海文联主席,打听近期是不是要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过来?她说是的。不想这事提前出现在我梦里。
2019年1月12日,周日
昨晚有梦,记不住了,感觉是乱。正应和这几天的心情烦乱。上午去保养车子,午后回,补觉。梦见谁搬家,是个熟人,但忘了是谁。他说家里有50年前的柴火,要不要收藏?我一时冲动,脑海里闪过会不会有珍贵木柴?想去拿,但又想了想,50年的柴火,快变成灰了吧?于是没有出声。似乎还有杂乱的内容,但记不得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是个原因,梦痕太浅也是原因之一。
2019年1月14日,周一
记昨晚的梦。梦见谷里村的三嫂遇到冤案,跟着我进城找人主持正义。她像“秋菊”那样跟着我。具体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委屈,她边走边说村里的某某某欺负她,把她的一整箱物品拿走了,让我想办法帮她要回来。我忽然想起那个某某某,心有余悸,当年我似乎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随时受人欺凌。走着讲着,好像醒来。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贺先生的二十六楼,他让我品酒。我把六瓶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好的是巴马瑶鹰拿来的50年(杂牌)老酒。梦跳切到河北作家李浩来广西,李约热组织夜宵。我们带着刚才品过的酒到富安居附近文联宿舍楼下的小饭店点菜。这期间接到贺先生的电话,他叫大家过去,说已经订好了航洋大厦通宵营业的某饭店。于是大家又往航洋大厦赶去。
2019年1月26日,周六
开会,宿邕州饭店。醒来记住一个梦。梦见在河池师专,我还年轻,到某副校长家求婚,买的是二手玫瑰,很胆怯。进门发现夫人和岳母在房里。她们穿越了,竟然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副校长家里(这个副校长也穿帮了,他是我毕业以后才提拔的)。我生怕岳母反对,但因为她女儿同意,她也就默许了。
一个穿越的梦境。
2019年1月28日,周一
中午眯了一会儿,做梦。梦见自己从卧室出来,发现老人躺在铺在地板的被窝里。正要道歉,发现那人是L。L起床,上旋转楼梯,到一咖啡馆,找了一张长条桌坐上。我一直跟着,坐下后才发现旁边尽是孩童,Y坐在孩童中間,为他们讲故事。我滑到桌上休息。桌下几个孩子围观我。我离开,一痞子装扮的人追上来,要与我打架。我奇怪,问为什么?他指指我的脚。原来我的脚上缠满了纱布,我什么时候受的伤?他说从我的受伤情况来判断,我是好战之徒,故要找我打架。我赶紧溜走。
2019年1月31日,周四
开会,继续宿邕州饭店。凌晨做了一个梦。梦见几个人在我家聊天,其中有G先生,他像《安娜·卡列尼娜》(下卷)里维斯洛夫斯基挑逗吉娣那样挑逗L,眼睛直勾勾地毫不顾忌地看,让我像列文那样难受。这几天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梦在模仿小说。之后,在一楼客厅(仿佛联排别墅的客厅),有一个篮球架,大家在投球(这是不是近几天和正华先生说回天峨过春节,约好打球的原因)。我发现球是瘪的,于是去找另外一个好的篮球,找不到,拿着瘪球出门,到右边汽修厂打气。打气过程中,发现球快裂开了(旧球)。于是另外找一个新球。充满气,拿回家里客厅发现又瘪了,原来那个黑色的球不是球,而是我平时背的双肩包。L在看电视,“马大姐”在远处做着家务什么的。我想那个新球到哪儿去了呢?想了许久才想起在广西民大的家里。
梦里我已经搬到东边的新房了。
2019年2月2日,周六
梦里,在某地开会,在山上。饿了,下山去吃饭。一群人。下山路上碰上WHF,她说下面有食堂。到了海滩边的食堂,有好多人在吃饭。海边有沙滩,有横生在沙滩上的椰子树,还有一些茅棚(无法确认,这些景象是否与上个月下旬去三亚度假有关?)转过几个茅棚,看见C罗在沙滩上颠球。有几个人围着。怎么会请到C罗?有人说是他来做公益,收入全部捐给穷人的孩子。
上山,记得有作家凡一平和鬼子。鬼子与人撞了一个满怀,把那人撞倒在路上。那人好像是WHF。
2019年2月6日,周三
4号回天峨过春节,宿天峨五吉大酒店。晚上做梦。梦见我们在广西新闻中心的楼上找509房间,碰见常哥,说某部门领导召集开会。大家都很忙乱,很紧张(这是否与常哥正在被安排写一出彩调剧有关?我当然也被牵入其中)。
梦里有梦?在梦之前,我在停车场停车。下雨了,我忘了关车门。于是,走出宾馆(不是新闻中心),往停车场走去。宾馆门前有立交桥。在立交桥下面遇克参同学。他拉我跟他打牌。我输了,打开背包,抽钱给他。一小偷凑过来,看见我包里的钱。我很紧张,抽了五十元给他。让他走。他走了。我们继续打牌。
因为回乡过春节,背包里确定放了几万元现金。另外,回乡过春节之前,一位剧院领导一直在跟我商量开某剧的策划研讨会。这个梦是否与这两件事有关?不知。
2019年2月10日,周日
春节,还在天峨。住五吉酒店,调了闹钟,今天要回南宁。闹钟还没到时,被梦搅醒了。梦见自己在一个课堂上,好像是学员,被老师点名对课本提意见。好多同学。我说这个课本没有创新,没有感情。正说着,一位本地的联通老总走进来,夸夸其谈,扰乱课堂。我看过去,课堂的一侧,坐满了他们公司的职员,一个个打扮得像空姐。原来,他们公司的职工也来听课,本来要请一位比我名气更大的作家来讲课,但那位作家没空,叫我顶上。梦里,我的身份瞬间从学员变成了老师。我对这位老总的表现极为不满,宣布下课。我们一起走出来,老总走在前面。我跟上,对他说你没有教养,试想如果是你在讲课,我在下面高谈阔论,你会怎么想?他做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并不谦虚,问我是吗?我说,是的,你没有教养。他再也没说话,朝长长的台阶走上去。我在后面跟着,加快步伐想超越他,想抢在他的前面走到台阶顶部的平台。因为,在那里停着我的车。我认为我的这辆车能证明我也不是没有财富。你老总虽然有钱,但我也不缺。但是,我还没走到台阶顶部就醒了。
晚上8点回到南宁,补记此梦。
2019年2月15日,周五
昨晚梦见父亲住院,好像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实中,我父亲从来没到过南宁,我工作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从外地赶回,看见H在医院里。是个大病房,有十几张床排着。我没看见父亲,只看见病床上零乱的被窝。也没看见母亲。只看见H。我说了一些感谢H的话。然后,想到一院(梦里在二院的东边,连在一起,像宾馆)还住着一个朋友,就想去看看。但我走出二院往东,怎么也找不到那幢梦里的一院楼房,似乎一院不在这里,是我记错了。我急赤白脸地转了几圈,从东边楼道走到西边二院,中途看见林老师和师母。他们住在一间小房里,我和L招呼他们。岳母也好像在场,她做了开胃的菜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