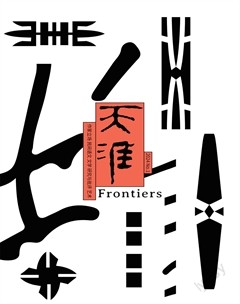2010年9月,具有杀伐之性情的西风,早晚如小股分散袭扰的贼寇,已开始在黎明和黄昏洗劫大地了。中午依旧很热。两个月前,我就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直觉,即我调离巴丹吉林沙漠的单位,到成都去工作的这件事,大致没有问题。《韩非子·说难》曰:“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凡尚未实现之事,最好缄口不言,知情者越少越好,若提前大张旗鼓,多会功亏一篑。
历史陈列馆收工,我又回到宣传科工作。那是一栋新建楼房,高大、气派,充满行政机关的威严。为了工作方便,同一部门占据一层或两层。我们对门是组织科、秘书科。干部科位于西边拐角处,这个职能科室总是充斥着神秘色彩。尽管只有几步之遥,从科长到干事也都认识,但关于我调职、调级等消息,都是我们科长通知我的。他们的办事程序是,先由部领导签批,呈报本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再把签批件拿给我们科长看。科长再把我叫到他个人办公室,一本正经通知到我本人。这一个流程,充斥着一种威严、无可置疑的程序与仪式感。
孔子《论语·尧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年少时,对这类宿命和违心的说法嗤之以鼻。到一定年纪,渐渐便有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的宿命感,也常因为某些事情心思缥缈,顿然恍兮惚兮。
这也算是我的人生大事,命运转折。正在此时,我打定主意,到下面最偏远的一个单位工作。这非一时兴起,而是我嗅到了一丝不好的气息。先前那位部领导和我同乡,不反对也不鼓励我业余写点小文章之类的个人爱好,素来相安无事。七月底,他和邻近单位一个职务相同的领导对调位置,此类大事,原本和我这样的一个小干事扯不上什么关系。没想到,新领导上任没多久,就让秘书科科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部领导办公室整洁、敞亮,我去过无数次,汇报工作,或者呈报文件等等,以至和先前领导平素说话办事,没有任何的隔膜。这位新领导,我只知道他原籍四川,姓叶,之前一直在邻近的一个同级单位任职,这一次主要领导互换,大致是为了落实上级关于干部工作的新要求进行的。进门,一个个子不高、脸色白皙、头发浓密但一律向后梳、眼睛明亮且神情有些莫测的中年男人,在巨大的办公桌后站着,似乎在整理某些个人物品。秘书科科长姓阳,也和我多年同事,个子矮,品性一直很好,我们私下关系还可以。
面对部领导,阳科长恭敬说,这就是杨献平,参与过单位历史陈列馆的建设,在某某基层任过职,在咱们机关先后当过文化、宣传、保卫干事等。部领导一边听一边嗯嗯回应,然后示意秘书科科长先出去,我留下。陽科长走出叶领导办公室,反手轻轻把门关上。按照一般情况,但凡主要领导找一个下属谈话,不是下属出了啥坏事儿,要被批评教育,就是天上掉馅饼,有了提职调级之类的大好事。看着叶领导光洁的额头,我的心七上八下,晃悠如秤砣。正在此时,叶领导干咳一声,端起茶杯,喝水时用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把我全身上下扫了一下,说:“听说你喜欢写点小散文、小诗歌之类的?”我不知道叶领导的真实意思,不由得支吾了一下,然后面红耳赤地答:“是。”
单位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上古时代,巴丹吉林沙漠被称为“流沙。”《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说:“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其中的“钟山”“昆仑之墟”“黑水之山”等地名确凿所指众说纷纭。《尚书·夏书·禹贡》中说:“(大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弱水”便是经由祁连山东麓发源至张掖、高台正义峡等地,转道巴丹吉林沙漠,最终流入居延海(额济纳河)的黑河,合黎山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北部,为天山余脉、河西走廊北山山系。《汉书·地理志》中说:“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
巴丹吉林这一名字的来源,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蒙古语当中的“绿色深渊”,还有人煞有介事说,“巴丹”初为“巴岱”,“吉林”则是六十个湖泊,合起来,就是一个名为巴岱的人,在这里发现六十面湖泊之意。历史地名流变,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我只是一个后来者与暂居者,对巴丹吉林的历史渊源,也仅限于历史典籍。《新唐书·地理志》载:“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至今,弱水河畔最有名的历史事件,一是老子由此“化胡”,虽然有荒诞之感,但两千多年来流传不衰。二是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之孙李陵带着他旗下五千“荆楚弟子,奇才剑客”由酒泉,沿着弱水河出塞,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军队,“苦战八昼夜”最终遭俘虏,终老于大漠,堪称千古第一伤心将军。三是瑞典人贝格曼与中国学者陈宗器等人于1930年在这一带发现了居延汉简。四是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由此发射成功。
在叶领导面前,我有些局促,从他颇为严肃的神色看,我平时喜欢写点小诗歌、小散文的行为,他肯定不满意。果不其然,我还想说点什么,他打断说:“你最好别再写那些了,我们单位这么多的先进事迹和人物,多写写我们身边人才是正事儿。”一听此言,我不知所措,脸色迅速涨红,自己都觉得烧到100摄氏度了。我局促地动了动趋于麻木的手脚。领导办公室尽管沙发林立,干净绵软,高大宽阔,但领导不表示让下属坐下来说话,下属自然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坐下。
在这个以科学技术研究、试验、训练为主的单位,舞文弄墨,一般都会被领导和同事们视作歪门邪道。这使我经常很羡慕岑参、高适等古代戍边者,写诗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送给各路统帅和地方官。因为自卑,我至今不愿意自称作家、诗人,一听到有人说我是一个诗人或作家,就想赶紧抓一把沙土,把自己涂成一个陌生人。很显然,这是一个崇尚知识和技能的时代,而作为人群、集体之根本和灵魂的文化,在很多人眼里,成了矫情、狂妄甚至不知羞耻,且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虚妄之物”。
站在叶领导宽大办公桌前,我谦卑地说:“您说得对,以后,我在这方面努力,争取有点儿成绩。”叶领导又喝了一口绿茶,整个脸扭向一堆待批的文件,我知道该告辞了,嗫嚅着说:“那我出去了啊!”叶领导嗯了一声,没抬头。我后退几步,打开门,出去,又反手轻轻拉上。这一连串动作,是礼貌,对领导,几乎每个下属都如此。
人在单位,必须和直接领导搞好关系,即使没有太多的交集,本人也没多少野心,但领导对某一个下属个人印象的好和坏,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某个下属在单位的现实际遇、心情,以及诸多现实利益的得与失。
秘书科在叶领导对面。我有一个预感,那就是赶紧逃离机关到基层去。这直觉迅疾,使得我没有犹豫,敲了秘书科科长的办公室,劈头对阳科长说:“我要下去,到最偏远的那个单位。”阳科长笑着说:“你想通了?这周部务会上,我提提,另外,你再给你们科长说下。”我说好。按照往常,一个机关的人到基层去,不是升职,也没有任何“好处”,总有些被“流放”的失落感,我却觉得一阵轻松,还暗暗对自己说:“杨献平,你小子是对的。”
夕阳残照,整个沙漠边缘的营区辉煌瑰丽,就连多数变黑了的杨树叶子,也有了金质之色。杨树黄叶曼妙,纷纷下落的姿势,像极了海市蜃楼中的精彩舞蹈,连千叶兰也如同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天了。我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奔驰。在沙漠绿洲的这个单位,多数人如此,只有少数领导,出于锻炼身体之故,坚持走路上下班,还有的车接车送。我只是一个小干事,还年轻,其实我更喜欢走路,之所以上下班骑自行车,是因为自卑。机关里面的人,不是科长就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再不然,就是手握财务、油、分房、人事等大权的办事人员,还有少数领导身边人和红人,相比之下,压力巨大。骑自行车上下班速度快,避免了与更多人正面接触。在一个单位,上下班遇到同事和领导打个招呼,是人之常情,也是职场礼貌。问题是,你主动打招呼、示好,人家就会给予回应或是表面上的接受,当自尊心被多次伤害之后,最好便是各行其是,遇到躲着走,绝不迎面直上。夕阳之下的戈壁,泛着无数的金银之色,一如海面上的万千反光,更远处的沙漠,金色的沙丘次第相连,风把它们塑造得犹如一只只美妙绝伦的乳房。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就想,那是大地在持续喂养天地万物、日月星光。
黄昏,除了在广场上嬉闹、玩耍的孩子,慢慢安静的万家灯火,万物都在静默,被黑夜带到一种模糊和空无的氛围当中。在家里,我喜欢一个人写点东西,或者上网浏览信息。有一段时间,因为保密,全单位没有连通互联网。人在大漠绝域,确实需要“外界”这个汹涌的现实现场来“通畅”与“加持”,可情况特殊,只能忍耐。当晚,我给家人说了自己的这个决定。当主管领导厌烦你的时候,选择到另一个单位,不失为明智之举。无论哪个单位,一个人毕竟渺小,而拥有决定权的人,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