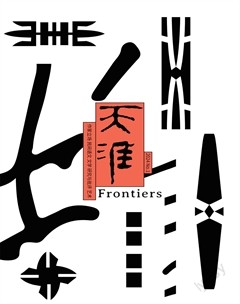祷河
大雨是在飞机即将降落呼伦贝尔机场时下起来的,夹杂着骇人的雷暴,机长果断掉头,直奔乌兰浩特机场。留着两撇八字小胡子的呼可夫安慰大伙儿说,等我们的海拉尔朋友来信了,是我们带来了雨,带来了雨就是带来了吉祥。
我们这趟五天四夜的呼伦贝尔之行由呼可夫带队,活动是他春天发起的,那时他正在筹备一个以儿童为主角的抗战题材电影拍摄,我们理所当然都叫他呼导——本来是导演的导,但此行他毛遂自荐,就变成了导游的导。呼可夫说,他每年都要去一趟呼伦贝尔。我们都知道,他早把呼伦贝尔当做自己的灵魂故乡了。
按计划,飞机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晚上八点三十分降落呼伦贝尔机场,谁知雷暴作梗,飞机只能暂时降落乌兰浩特,我们看到了舷窗外阴郁的夜色。人们不能出舱,乘务员用清晰的汉语和蹩脚的英语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似乎起了作用,大家都像绵羊一样安静地蜷坐着。好在过了一个多小时,呼伦贝尔的夜空上雷暴遁去,飞机又能飞行了,方才还萎靡不振的人们一下子欢呼起来。飞机在呼伦贝尔机场(海拉尔)落地时已近晚上十一点半,天还下着雨,但不大,空气很清爽,甚至有点微凉,我们几个无所谓,估计南方人会觉得有些凉。
开着一台别克商务车接我们的是呼可夫的一个朋友,全名敖其巴特尔,据说是个拥有百万级粉丝的大网红(搜索了一下抖音,果然如此),人既帅气也豪气。敖其巴特尔把我们接到一个小众文艺风格的餐吧,那里,早准备好了当地最著名的南屯牛肉,还有一柜子罐装的韩国啤酒。此地待客风俗有点奇特,事先告之,必须从天黑喝到天亮。那就是通宵酒喽!如果单纯灌一肚子酒,谁的胃也受不了,好在一众好友中有个前民族风乐队的歌手,叫乐乐,加上是个蒙古人或鄂温克人就会唱歌,所以这顿酒连喝带唱一直闹腾到了天光渐明时的凌晨四点。
我们回到宾馆后倒头便睡,浑身的疲倦只能靠深度睡眠才能逐出。但——此处我不得不提一下与我同屋的编剧老师苏俊杰,他的古怪而嘹亮的鼾声犹如呼伦贝尔机场上空的那场雷暴,又像他某部作品中某个明确的形象以及丰富的对白。
此行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是呼可夫重访大萨满斯仁其米格。大萨满的居住地在阿木古郎小镇上,离海拉尔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出发前已是中午时分,在敖其巴特尔的极力推荐下,到一条充满布里亚特美食风情的小街上吃了一顿布里亚特美食:加大块牛肉的罗宋汤,俄罗斯风味的大列巴和布里亚特包子,当然,加了奶油的香喷喷的奶茶是必不可少的。
在呼伦贝尔,除了城市就是草原,城市被草原包围着,一出城市就是草原。比如出了海拉尔城区的草原,眼界顿时阔大无边,风景美得乱套。我们来的时候正是雨季,目力所及除了草原还有几百万吨雪崩似的云堆满了天空,仿佛随时要落到地上,看得人有点胆战心惊。不过当地人说雨季还是来晚了,虽然今年的草颇茂盛,但比往年要矮了些。
草原上的公路笔直,没有尽头似的,一般人开起车来会疲劳,甚至生出绝望感。我们一行去往阿木古郎的途中,一直是苏俊杰在开车,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说第一次在大草原上开车,视野开阔,有新鲜感。愈往深处走,草愈密也愈高,草里夹杂着各种野花,我只认识一种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如果说辽阔的大草原上仅仅长着草那是不对的,草原上遍布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当然少不了牛群、羊群,更少不了马群。马群在水泡子边上互相嬉闹着,肚皮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蹄坑。草原上建有壮观的风电场,还有仪仗队列似的“护送”了我们一路的电线杆子;电线杆子太多了,路通向哪里它们就栽到哪里。我还在半途看到一只蹲在一个水泥桩子上的隼,被风吹着,但它像个伺机而出的黑衣刺客,始终一动不动。
车进入阿木古郎后,沿路的树多了起来,有的已连成一片。小镇风格看起来略有年代感,也有点异域风情感,也就是说,小镇显得旧了点。来之前呼可夫就给大萨满打了电話,大萨满也给他指了路,可是我们的车在呼可夫的指挥下两次误入歧途,他只好站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大土堆上再次给大萨满打电话,打通了,原来大萨满的家就在我们停车旁的一处旧院子里。
下午四点整,我们进了大萨满家的小院,小院里长满杂草,但不高,也就刚没过脚梁面而已,有个额吉模样的妇女站在一个小屋前迎着我们。小屋门口有几只小奶猫跑来跑去,非常可爱,与我们同行的两名南方女孩儿(我们电影剧组的助理)当时欢喜得不得了,抱起来好一通亲昵。
进了小屋,才发现屋里又连接着两三间小屋,其中一间是大萨满的。大萨满是个年轻的女子,穿一件半大身红袍子,头戴一顶传统式样的帽子,和蔼地端坐在一张小桌的后面。她面带微笑,仿佛邻家姐姐一般好看。屋里有金属画像、有木架子、有一套大萨满服装和一顶大萨满头饰;大萨满服装是蓝袍子,上面缀满了金属法器。在浓浓的檀香和艾草香味中,呼可夫对我说,这是我的师父大萨满斯仁其木格。
我们此行,主要是陪呼可夫向全科全能的大萨满问一些灵魂上的事。
我因好奇,就在屋子里外转了转,并没有发现什么太过讲究的装设,也没有发现什么太过稀奇的器物,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而已。呼可夫用蒙古语和大萨满聊了几句后,就招呼我们出行,出行前要到街上买一些祷祭的贡品,我知道,做法事时,神的荣耀会因没有贡品而暗淡。大萨满的专车是她的一个女助手开的,车上装了做法事用的服饰和器物,我们紧随其后,出了小镇,直奔一条叫乌尔逊的河流。
此时天空中的云越来越厚,也越来越多,像长了腿一般追逐着我们。天显得低了,仿佛魔幻世界,却更壮观了。我看着天上连绵不绝的云,突发奇想,云会不会死亡?它们跟着我们,一路上在变化,在前行,速度很快,我想它们会死亡的。云的死亡方式就是云死后又变成了云,只不过,原来的地方化作一片荒芜的墓园。
眼前的乌尔逊河不算宽,水缓缓地流着,目测最宽处也不过三十丈,但有多长就不知道了。水面上空不时有鸟飞过来叫着,我仿佛看见一条银灰色的鱼在水流中张大嘴巴打着哈欠。随行的一位当地朋友介绍说,乌尔逊河连接呼伦湖和贝尔湖,呼伦贝尔之名也由此而来,水很深,牛马皆不敢过;朋友又说,乌尔逊河也是新巴尔虎东、西两旗的边界线。呼伦湖和贝尔湖久负盛名,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去亲睹一遍。
大萨满站在绿草如茵的河边,凝望着河流,巴掌大的干牛粪片子在脚下随处可见。呼可夫和大萨满助手正从车上往下搬做法事用的服饰、法器和祭品。就在此时,石灰色的薄云布满了天空,而太阳的光晕有些模糊不清,太阳就像一个戴着浮雕面具的词语被阴云虚遮着。
不知何时呼可夫换上了一身宽大的蒙古袍,看上去像一句无人能懂的站着行走的戏剧台词,他说这样才能获得神的保佑。他和大萨满的助手在河边布置祭祀龙王的贡品,首先插起三根胫骨高的彩旗,其中两根的顶端是马头;然后依次摆放了水果罐头、蔬果、冰糖、馒头、饮料、葡萄酒、坚果、枣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