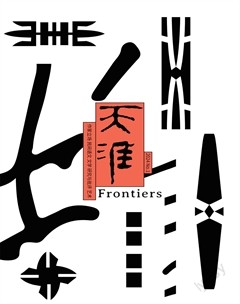一
人能变成蚕吗?
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变形记》,里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大家都知道那是小说,在神神叨叨的作家笔下,人变成啥都不稀奇。
可我遇到的事绝不是小说。
我妈问我:“你知道你变过蚕吗?”
我吃了一惊。
“就是那种上簇的蚕,”我妈解释说,“浑身圆鼓鼓的,透亮透亮的。”
她这么一说,我好像记起来了。我说“好像”,是因为我的记忆是模糊的。模糊既来自时间的久远——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也来自于我当时的昏迷状态——变蚕的过程我根本不知道。
但变蚕之前的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已经七岁了。那年夏天是我灾难的起点,一个蝉鸣如吼的午后时分,我姑姑和她的几个伙伴在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做针线,我在她们旁边玩耍,姑姑口渴了,叫我给她端一碗水来。我家装凉开水的瓦罐搁在灶台上,我站在地下够不着,就爬上灶台。这时候灶台上的大铁锅正熬着麦仁粥,我不小心踩到锅盖上,锅盖侧滑,我一脚踹进了滚烫的麦仁粥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被抱出来时整个脚丫子几乎烫熟了,那种疼痛几十年后我依然刻骨铭心。从脚掌脚背到脚踝,很快冒出一串串亮晶晶的水泡,小的像珍珠,大的像葡萄。
姑姑及家人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有邻居提议赶快降温,于是舀来一盆凉水,把我的脚浸在里面。又有人贡献出偏方,说可以敷上浆水菜,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无论是睡着还是清醒,脚总是被架起来,上面挂满一根根淡灰色的芹菜秆,好像我的腿是晾晒干菜的架杆。
这里不得不说说浆水菜。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小菜,做法很简单,把老芹菜、萝卜缨子、雪里蕻等在开水锅里煮熟,连菜带汁舀入瓦罐缸盆,再加入面汤,盖紧捂严,让其发酵,几天后菜叶变黄,汤汁变酸,便可食用。在今天,浆水菜只是特色美食,可在那个缺粮少菜的年代,它是老百姓的救命菜。因为新鲜菜没法久放,在收获季节把它们泡成浆水菜,可以在吃不上新鲜菜的时候调剂寡淡的饮食。浆水菜不光可以吃,泡菜的水也不能浪费,它可以煮面条,酸酸的味道节省了醋。更常见的是把浆水当成解暑降温的饮料,因为盛放浆水菜的坛罐为了防腐,一般都搁在阴凉处,特别是在幽深潮湿的窑洞里,所以滗出的浆水冰凉酸爽。夏天伏季,人们从火热的田野劳作回家,暑热难耐,喝上一碗浆水,那种沁入肺腑的清凉,一下子浇灭了从外到里的火气。
正因为浆水能降温,所以才会有浆水菜治疗烫伤的偏方。
我后来一直奇怪,为什么家人不送我去医院?要知道那时候我还小,烫伤很严重,可以想象我惊心动魄的哭闹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难道他们就不心疼吗?万幸的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脚上挂满芹菜叶,时刻都被闹哄哄的苍蝇包围着,但烫伤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皮肤没有留下疤痕。
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更糟心的还在后面。
二
烫伤好了之后,我莫名其妙地得了另外一种怪病:浮肿。刚开始时只是早晨起来手指肿胀,握拳不实,到中午就消退了。后来发展成十指肿胀不消,眼泡也肿起来了,再后来是下肢浮肿,用手指按一下小腿,就会陷下去一个深凹。最厉害的时候,脚肿得像砖头,鞋子都穿不进去。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袋大水囊,动一动都能听到水的晃荡声。
这时候我爷爷出场了。他是决定我生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同时还是一个半拉子医生。这两种身份结合起来,让他在如何对待我这个病患的问题上一言九鼎。我爷爷从小就在一家私营药铺里当店员,后来熬成了这家药铺的掌柜,公私合营后他作为资方代理人,成了国营药铺的副经理。他这个身份,不要说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数千人的村子里,也是极其显赫的。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为说错话,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在外面他变得谦卑内敛,但在我们家,他依然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他半拉子医生的身份,也与他的职业有关。他是药铺的配药员,数十年跟药材打交道,对药材的药理属性了如指掌,后来也自以为可以给人开方治病了。但他并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中医,不会把脉验舌,别人不相信他,他就在自家人身上练手。碰巧我这时得病了,在我爷爷看来,这算不得什么大病,他绝对可以给我治好。
我后来猜想我爷爷给我开的中药应该都是泄水利尿的,因为我喝了这些中药后,不停地撒尿,当然,身上的肿胀也很快消失了。可是这维持不了几天,一旦药效过去,旧态立即复萌。这种一消一胀的过程,就像孩子们玩的“吹胀捏塌”——猪尿脬。随着这种反复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的病越来越厉害了,我不但浑身浮肿,而且心急气短,渐渐地,行走都困难了。稍微活动一下,气喘吁吁,虚汗淋漓,身软腿颤,脆弱的腿干根本支撑不起沉重的身体。
这些感觉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到后来,我就没有记忆了,因为我昏迷过去了。在我昏迷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家里决定不救我了,放弃治疗。我推测这个决定是我爷爷做出的,我父母亲无奈,只得同意。假如不是发生第二件事的话,我绝对被扔进死娃沟。我们村子真的有这么一条沟,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很可能它原来是有其他名字的,由于村人常向沟里扔死孩子,渐渐地,它的原名就被死娃沟代替了。那时候儿童的夭折率很高,这其中有病死的,也有不明原因的死亡——多是女婴。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死娃沟是很阴森的地方,人们轻易不去那里,那里的常客是野狗,甚至传说有狼出没。
就在家里决定抛弃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一个人找上门来,是她救了我一命。我后来把这个对我有大恩大德的女人拜为干妈。
三
我变成蚕就在这个时候:我昏迷不醒,躺在炕上。由于肿胀,充满液体,我的身体膨大了一倍,加上小孩的皮肤又嫩又薄,在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照耀下,我真的很像一只圆鼓鼓、亮晶晶的即将上簇的大肥蚕。
我妈一直守在我的身旁,泪流不止,她知道她儿子就要被扔进死娃沟了,这是我们母子相处的最后时刻。可是我命不该绝,我干妈來了。
她是一个热心的异乡人。当然,所有嫁到我们村的女人都是异乡人,不过她不一样。别人的“异乡”只不过是异村——乡下结亲,择偶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十里路;而她却是真正的異乡,她娘家在百里之外的三桥,三桥是省会西安的郊区。郊区人也算是市民,相比我们这些农民,她在当时算是有高贵身份的,我不知道她为何远嫁到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变故,可惜她守口如瓶,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干妈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建议我家人立即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从发病到濒临死亡,我一直没有去过医院!这其中的原因,我后来猜测,无非两点:一是我爷爷相信他可以治好我;另一点是没钱,去不起医院。中药本来就不值钱,加上我爷爷一直在药铺工作,可以享受内部职工的成本价,所以我吃中药花不了几个钱。但进医院就不一样了,医院是要花大钱的,吃药打针对毫无收入或者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那都是天价。在乡下,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人多的是,我爷爷直到终老也没进过。
我家当时穷得叮当响,子女多,劳动力少,每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如果我爷爷当时有正常收入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偏偏他因为老问题,被监督改造,在单位,人家只管他吃饭,不给工资。这种家境,哪里有钱送我进医院。
我干妈的建议是,不但要送我进医院,而且要去大医院,因为我眼看就不行了,小医院救不了。
自然就卡在钱的问题上了。我干妈对我父亲说:“黑娃兄弟,你去借,向生产队借!”然后又对我爷爷说:“四叔,你也去借,到你单位去借,跟你同事借!”最后她说:“我好歹也能借给你们几个钱,咱们合力救下这个娃,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聪明得很,没上学就会背《三国》呢!”
能背《三国》,这是真事,也不是真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只会背诵《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那些片段。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一到节假日,如果恰好阴雨天,我爷爷不上班,也不能下地干活,他就会躺在炕上诵读《三国演义》,大概因为心境的缘故,他最爱的片段是“三顾茅庐”,最欣赏的是卧龙岗上散淡的诸葛亮。我爷爷念过私塾,从小养成诵读的习惯,他读书时总要把我搂在怀中,让我当他的忠实听众。学龄前儿童正是需要故事滋养的时候,于是我在他反复的诵读中记住了三顾茅庐的一字一句。
没想到这点小聪明打动了我干妈,生死关头对我施予援手。
我是怎么被送到省城的儿童医院的,昏迷中的我一无所知。后来是父亲告诉我的,他和我干妈护送我去医院。他们从我们村附近的绛帐车站扒上货车,注意,不是坐车,是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