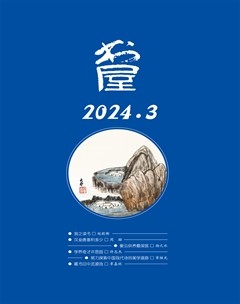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毅衡的叙述学事业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小说叙述的中西比较研究。赵毅衡基于叙述形式分析,初步建构了形式-文化论,代表论著为《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第二阶段是自二十一世纪后的广义叙述学。赵毅衡将形式-文化论推向一般的符号意义论,以符号意义论反哺叙述学,突破叙述学界至今依旧流行的小说中心局面,提出符号叙述学。研究任何符合叙述底线定义的叙述体裁——符号叙述学也因此被称为广义叙述学,代表论著包括作为理论基础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和《广义叙述学》(2013)。
形式-文化论也被称为“文化的意义形式论”或“意义形式论”,所涉及的三个关键概念是意义、形式和文化。在赵毅衡看来,是意义使意识和世界联系。具体而言,人类的意识具有寻找并获取意义的倾向,观照世间事物,在意识再现事物和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产生了意义。被再现的事物成为解释出意义的对象,而意识再现需要感知形式作为载体。可以充当这种感知形式的,包括物-事件、文本、他人之心-我之心等,这些“被解读出意义的感知”,即“符号”。所以,符号是承载意义的形式,符号活动就是意向观照对象和解释的活动,也即意义活动。所有的这些意义活动构成人类文化实践,文化是一个社会全部意义活动的集合。
形式-文化论构成了赵毅衡小说叙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在叙述中生成,这就意味着叙述者在叙述中显身,但是,叙述者又是叙述的生成和发送者,这就意味着叙述者在叙述前就存在——被生成的叙述包裹了生成它的叙述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赵毅衡称之为“叙述自指悖论”。这一悖论反映了叙述形式中存在着根本的龃龉,对它的解释需要上升到文化意识中去,将叙述理解为一个受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人工构筑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人文学界加强了对西方研究的引介,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模式的叙述学。彼时西方的叙述学,因为过于强调文本形式而忽略文化语境,正陷入低谷,而在引入国内时,因为中国叙述文化传统的不同,叙述学也面临着水土不服。